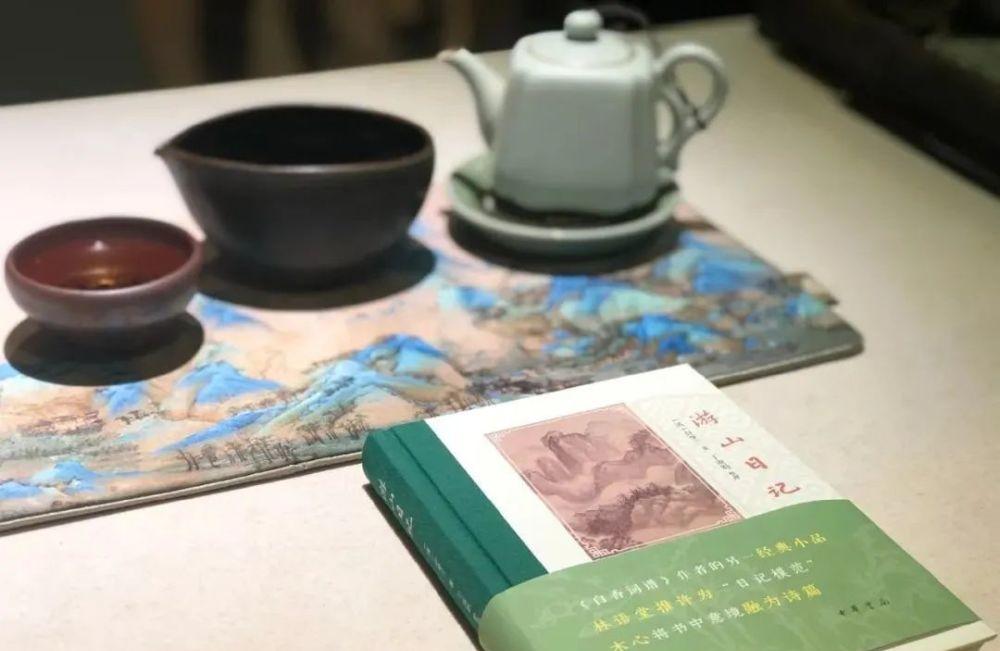
晚清有這麼一個文人:他一生未仕,但卻是親王大臣的座上賓;自幼家境不錯,但身無分文一箪食一瓢飲也頗能自得其樂。
在今天,他似乎不是那麼有名,不像納蘭容若、曹雪芹那樣人盡皆知;但在當時卻是書商追捧的對象,他編纂的《白香詞譜》被譽為“學詞入門第一書”。
他到廬山去住了100天,賞白雲清泉,聽虎嘯蟲鳴,有時給僧人講講佛法,有時和學生聊聊西方宗教與人口問題(周劭曾贊歎:“18世紀的中國文人,思想能及于社會人口問題……堪稱奇迹。”)他感慨遊客受知客僧熱情款待而欣喜,卻不知接下來就要面對化緣簿;但自己聽說一位招待過他的老僧患病,便傾囊相助,毫不吝惜。他遊覽廬山天池後,寫了一篇《天池賦》,然後笑呵呵地在日記裡記下:“又有數遊客……文人也,頃立四仙祠讀《天池賦》良久,贊曰:‘好長!’”
諸多名家的青睐
這個人就是舒夢蘭,字白香。這本書叫做《遊山日記》,一寫完就被清代書商搶去印了好幾版。民國時周作人在舊書店找到一版,大為欣喜,推薦給林語堂;林語堂拉了周劭來點校,推薦給宇宙風社出版,還專門寫了一篇《〈遊山日記〉讀法》,推許為“日記模範”。周作人為之作序,說:
白香的文章清麗,思想通達,在文人中不可多得,樂蓮裳跋語稱其彙儒釋于寸心,窮天人于尺素,雖稍有藻飾,卻亦可謂知言。
林語堂的《讀法》則更具體,贊許書中《庸人頌》一篇“此蓋古今來罵道學第一篇傑作,與袁子才《答楊笠湖書》媲美,真可謂盡嬉笑怒罵之能事”,又評《以寒熱談國脈盛衰》條“真所謂妙語解頤”,《以四時喻賢聖》條“罕譬而喻,文字活潑,是吾所謂好文章”。
後來,木心看到這本書,喜愛其中的清新甯靜,就寫了一首詩,叫《白香日注》。詩雲:
晴涼/天籁又作/此山不聞風聲日少/泉音雨霁便止
永晝蟬嘶松濤/遠林畫眉百啭/朝暮老僧梵呗/夜靜風定/秋蟲咠咠如禱
午明暖/晚來雲滿室/作焦油氣/以巨爆擊之勿散/煙雲異/不溷/雲過密則反無雨/人坐其中一物不見
阖扉,雲之入者不出/扉啟,雲之出者旋入/口鼻内無非雲者/窺書不見,昏欲睡/今日可謂雲醉
朝晴涼适/可着小棉/瓶中米尚支數日/菜已竭,所謂馑也
采南瓜葉、野苋/煮食甚甘/予仍飯兩碗
冷/雨竟日/試以荞麥葉作羹/柔美過瓠葉/微苦
苟非入山既深/安知此風味
埋豆池旁/際雨而芽/晨食烹之嘗試/入齒香脆/頌不容口
日注就是日記,詩中幾乎所有的句子都摘自《遊山日記》,以詩人的眼光遴選、重新排列,将《日記》中清幽出塵的生活集中展現了出來。
中華書局本出版
時光荏苒,後來的很長時間内,這本書都沒有再版,似乎有些被遺忘了。直到2021年,中華書局簡體橫排本出版。
這個選題最初是時任中華書局上海公司總編輯的李保民先生策劃的,他找來上海圖書館藏的嘉慶十年刻本《遊山日記》,邀請之前點校過《白香詞譜》的于淑娟教授整理并撰寫了完整介紹舒夢蘭其人其書的導讀。但是,工作尚未完成,保民老師就退休離開了中華書局,于是将這本書托付給我。
坦率地說,最開始接手書稿時,我也不過當成前輩交待的一個任務——畢竟在市場碼洋為主要考核名額的當下,一本清朝人的日記,實在很難讓人抱以太大的期待。但這樣的想法很快發生了改變,原因很簡單:舒夢蘭此人,實在太有魅力了!審稿時,經常忍不住為那些看穿世事、說到人心裡去的話擊節贊歎,為那些隐藏在溫柔敦厚下的犀利笑話拍案叫絕,而那支生花妙筆下描繪的廬山清景,又往往能讓人忘記滾滾紅塵,仿佛置身于山中清涼世界。我一邊審讀,一邊摘抄了自己喜歡的句子,試舉一二如下:
飯後果大雨,檐聲如瀑。徐察天池,得雨水反有濁意,是雲自地起,賦氣未能極其清,故天池不樂受耶?下士謂韓、樊之封爵等耳,乃不屑與哙等伍,是以取禍,殊不知信即終窮,亦羞與哙為友也。此志惟蕭何知之,故亦惟蕭何惜之而已。
一般人以為韓信和樊哙的爵位一樣,卻看不起後者,是以自取其禍;卻不知道韓信哪怕一輩子不封侯,也是看不上樊哙的。
大雨終日,昨所謂涼者,變而寒矣。……不免避熱來,複避寒歸,歸仍大熱,則又複追慕天池。人生亦安有兩面便宜之境?可深思也。
入山太冷,人世間太熱,但人生又哪來那麼多兩全其美、“不負如來不負卿”的好事呢?
聞曉鐘梵唱而起,徑詣文殊崖看雲。意方适而剃發人至,不直為此舍妙雲歸也,遂呼使剃沐崖上,和雲栉發,黑白分明,香光則一,可謂與雲為徒矣。
舒夢蘭最愛廬山的雲,日記中反複詠歎,有時白雲入室,有時“飲雲”“雲醉”,更多的則是到山間看雲。而連理發也在雲中,“和雲栉發,黑白分明”,真是令人羨慕了!
成書時,我便為每個章節都選了一段類似的文字,放在目錄中,希望借此讓讀者一開卷就能感受到白香文字的精彩。事實上,書中妙處實在太多,俯拾皆是,摘不勝摘,目錄隻是一個引導,入門後才是真正的美不勝收。
書後設有附錄,除了嘉慶刻本原來的序跋題詞,還收了民國版周作人的序、林語堂的《遊山日記讀法》和周劭的跋。其中文字我有意保留了民國版原貌,與正文偶有差別,蓋當年校勘、出版條件不如現在,多魯魚亥豕之誤,标點習慣亦間有異同。這也正是如今精擇善本、重新整理的意義所在。
《遊山日記》篇幅不大,内容又輕快可讀,是以開本上選擇了130×184mm的标準32開,在大32開已成慣例的當下,這個開本尤顯小巧可愛,且非常便于攜帶。
《遊山日記》
[清]舒夢蘭 著
于淑娟 整理
中華書局 2021年11月出版
封面則又是花工夫的地方。美編設計了好幾套方案,底色有灰的、黃的、白的、橙的、紅綠撞色的,好像都還行,但又始終覺得缺了些什麼。最後,我從季羨林先生的《登廬山》中獲得了靈感,季先生說:“所到之處,總是綠,綠,綠……綠是廬山的精神,綠是廬山的靈魂”,他還改寫了蘇東坡的廬山詩,開頭一句改為“近濃遠淡綠重重”。由此,我們把封面設計為深深淺淺的綠:墨綠、淺綠、翠綠……封面主圖采用清代著名畫家王翚的《廬山白雲圖卷》,旁邊配以古典格子窗棂,就好像舒夢蘭在《日記》中再三詠歎的風景。
前幾天的票選中,《遊山日記》被評為中華書局2021年度“最受讀者喜愛的雙十佳圖書”之一。希望我們的努力,能讓更多讀者走近這本名字普普通通、内容卻精彩紛呈的小書,和舒夢蘭一起享受山中風味,為這滾滾紅塵、碌碌勞生增添一份安甯與清涼。
(本文原載于《藏書報》2021年12月27日11版)
【贈箋紙】《遊山日記》(贈整理者于淑娟簽名箋紙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