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生到北京來,我都是問他們,房子買的還是租的,我建議他們買下來,我會非常具體問多大面積,在我印象中底線是120平米。120平米在北京可能1200萬,而且還不見得特别好,但他們(在省會城市)都能達到。我覺得這才是人生。”
著名作家梁曉聲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談到他對一個學生生活是否幸福的判斷,在于其住什麼樣的房子,并直言人生的其他方面都是在這個物質基礎上展開。
随即他又問:“這是不是有一點被認為很俗,不浪漫,不激情?”
2022年3月,梁曉聲的又一部長篇小說《中文桃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該書以80一代為主角,以現實主義的筆法描寫了某高校中文系幾位學生求學、戀愛、工作、北漂及最後傳回原籍,在家鄉紮根、建立家庭的故事。小說涉及諸多備受時下讀者關注的社會議題,如北漂、房價、官二代、中文系的沒落等等,較為真實地反映了80一代的人生經曆和生存境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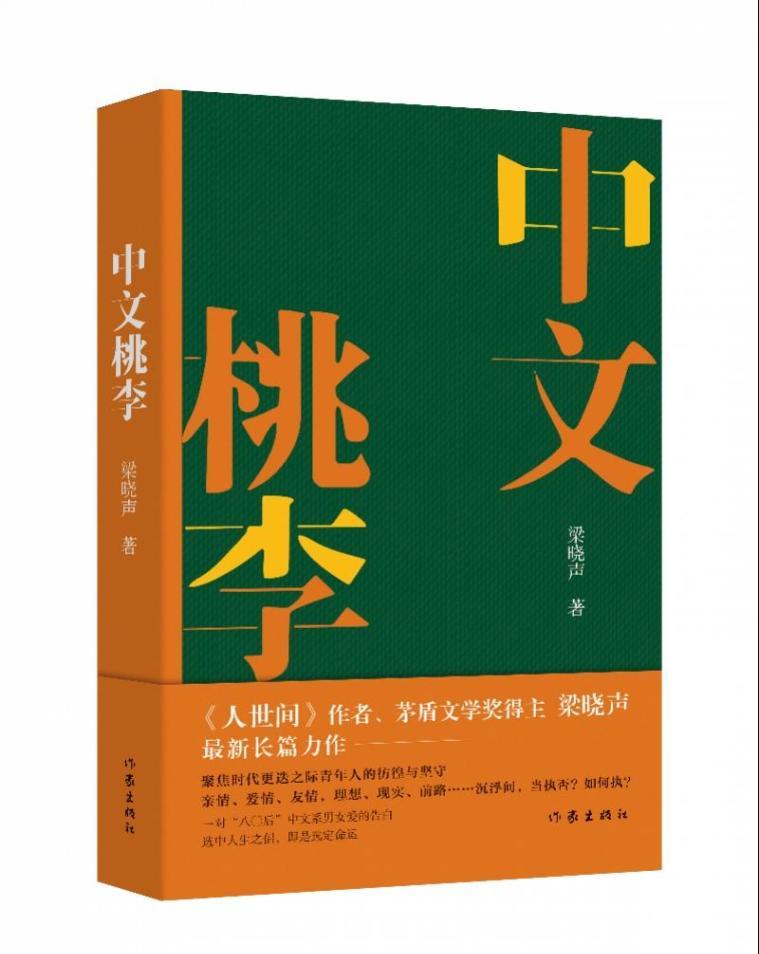
為教過的學生寫一本書
“實際上我為80後學子,就是為我教過的學生們寫一本書始終是一個心念。”70出頭的梁曉聲精神抖擻地出現在作家出版社的會議室裡。他坦言,寫作《中文桃李》就是為了完成這個心念,他在叙事上很有親近感,因為可以站在人物的角度“換位思考”。
自2002年開始,梁曉聲在北京語言大學擔任中文系教授。他談到中文系的招生狀況,顯得有一些憂心忡忡。“2002年的時候,我們班裡有将近10名男生或者還要多。他們都是沖着‘中文’兩個字來的,你擋不住他們那種激情,要辦刊物。當年北語的刊物辦得還不錯,還吸納了周邊高校的同學們來投稿……我們有時候上二百多人的大課,周邊的同學也來。”
可是大約從六七年前開始,中文系的男生越來越少,最少的時候一個班裡隻有兩三個男生。“男生少到這樣程度,如果又很内向,不發言,那實際上你聽到的讨論之聲都是同一性别的人的觀點,這對讨論本身是一種遺憾。”
一方面男生愈來愈稀少,另一方面女生又“身在曹營心在漢”。在梁曉聲看來,中文系的女生皆是由于“在理科方面不能夠與男生們競争取得優勢”,出于無奈才考入中文的。她們在考研的時候恨不得“搖身一變”,趕緊跳脫出去。
“我和同行們在一起經常地苦笑說,也不能使中文專業變成一個‘筐’,什麼都能往裡裝。”梁曉聲感慨道。他強調,文學不僅陶冶我們的靈魂,中文的認知能力也是一種從業能力。有了這種從業能力,到了社會上怎麼檢驗、應用這種能力,在這個過程裡中文系畢業生所面臨的困惑以及他們的思考,這是《中文桃李》試圖探讨的話題。
在哪裡生活沒有對錯,隻有利弊
中文系畢業生工資收入普遍較低也是一個現實問題。就像在小說裡一樣,梁曉聲特别能代入男生的角度,他說:“女生選擇不選擇我們,即使人家不說,心裡也會想他掙多少錢,這樣想也有道理,因為你要養家糊口。”
在小說中,男主李曉東中文系畢業後,輾轉于省電視台、廣告公司、地方電視台等工作機關,為了省城戶口還當過一陣清潔工。女主徐冉研究所學生畢業後到北京也隻是做了一份短暫的明星經濟助理的工作,傳回臨泉後考上公務員,成了離退休老幹部服務處的上司。
當年在北京闖蕩時,兩人在回龍觀社群租了一處三十幾平米的半地下室,每個月房租1500塊。當時北京的房間正是起飛階段,學區房的房價已是兩萬多一平米,普通工薪層已是難以企及。
在小說裡,主人公李曉東的父親曾說:“人是追求幸福的動物,但首先得明白幸福的要義是什麼。在哪裡生活的愉快指數高一點兒,哪裡才是我們普通人的福地。”對于主人公最終選擇離開北京,放棄省城,回到家鄉臨泉去生活,梁曉聲認為“不一定有對錯,它隻是一種利弊,一種權衡。”
梁曉聲說,他的學生中凡是回到了自己原籍的,現在生活都相對滋潤。在當地可以用較少的錢買到很大的房子,工作上也很快成為骨幹。留在北京的反而更難,”那麼優秀的女生,她們本來是可以不在北京,換一個地方,身上其他方面的優勢都會被呈現出來。”
在梁曉聲看來,此心安處是吾鄉。人生需要規劃,但“人生規劃裡邊一定把北京放在那兒,北京就是我的規劃之一,這規劃太要命了。”
小說的一大看點是李曉東和徐冉兩個年輕人相識、相戀、走入婚姻殿堂并攜手一生的故事。“我是不太願意靠愛情線索和愛情内容來撐起一部書的,但是我有時也會沾沾自喜,雖然70多歲了,寫年輕人的愛情也還可以寫到信手拈來。”梁曉聲說。
範偉能演出中文系教授的“宅心仁厚”
小說裡的官二代、幹部子弟王文琪是梁曉聲很喜歡的一個角色。此人頭腦靈活、手眼通天、仗義疏财,許多讓寒門子弟一籌莫展的難題,在他那裡幾乎迎刃而解。
談到王文琪和主人公李曉東的關系,梁曉聲說:“兩個男人之間,如果他們是發小又是初高中同學,上大學又在一起,還是同一個專業,愛好、諧趣相投的話,能好到什麼程度?女生有閨蜜,男生我們叫‘把子’,從前的年輕男人為了這份交情是可以豁出命來的。”
他也坦言,像王文琪這樣的幹部子弟,不乏酒肉朋友、玩樂朋友,但像李曉東這樣的内心的朋友卻彌足珍貴。事實上,随着人年歲漸長,“社會關系之和越來越大”,卻會突然發現“在乎自己,或者自己也在乎的人越來越少。”
無論是小說前半段的中文系往事,還是後半段寫北漂經曆、返鄉紮根和徐冉在離退休老幹部處“轉移于生死二場”的體制内工作,梁曉聲的叙事中都有一股輕松诙諧乃至荒誕的調子。在小說最後,他自己也粉墨登場“打醬油”,寫道作家梁曉聲到臨泉辦講座,講座票送不出去,徐冉更對此不屑一顧:“如果由我來講文學與人生,肯定比那個梁曉聲講得好。”
“寫完《人世間》的時候,相對放松一些,就寫一部寫起來不那麼沉重的,可以放松一下的書,否則人家以為我就是一個不知道有多憂患、多沉重的人,”梁曉聲說。小小的幽默藏在字裡行間,這是生活中他比較喜歡的狀态。
據他透露,書中的中文系教授汪爾淼正是以自己為原型,書裡汪爾淼在中文系講的課程也是自己在北語上課的内容。和《人世間》一樣,《中文桃李》目前也有影視改編的計劃。
“演汪先生的人我都物色好了。”梁曉聲興緻勃勃地說。“我喜歡範偉,我沒見過他,但我比較欣賞他的表演。他的整個面部表情,尤其在他眯起眼睛微微一笑的時候,似乎有着一種宅心仁厚的狀态,而這個狀态我認為是汪先生應該有的宅心仁厚。”
南都記者 黃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