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殺進文學界:“讓寫作像呼吸一樣簡單”?
學生們忙着用AI寫論文,程式員們忙着用AI寫代碼,畫家們忙着用AI繪畫,寂寞的普通人忙着和AI聊天……
這不是科幻小說中才存在的故事,而是發生在2023年的常見場景:不知疲倦的AI正試圖進入一個又一個領域,取代該領域原本的工作者。也有人對此感到激動,一位AI行業從業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元年到來了。
這些AI工具宣傳語承諾要“讓寫作像呼吸一樣簡單”“故事不會寫?給我一個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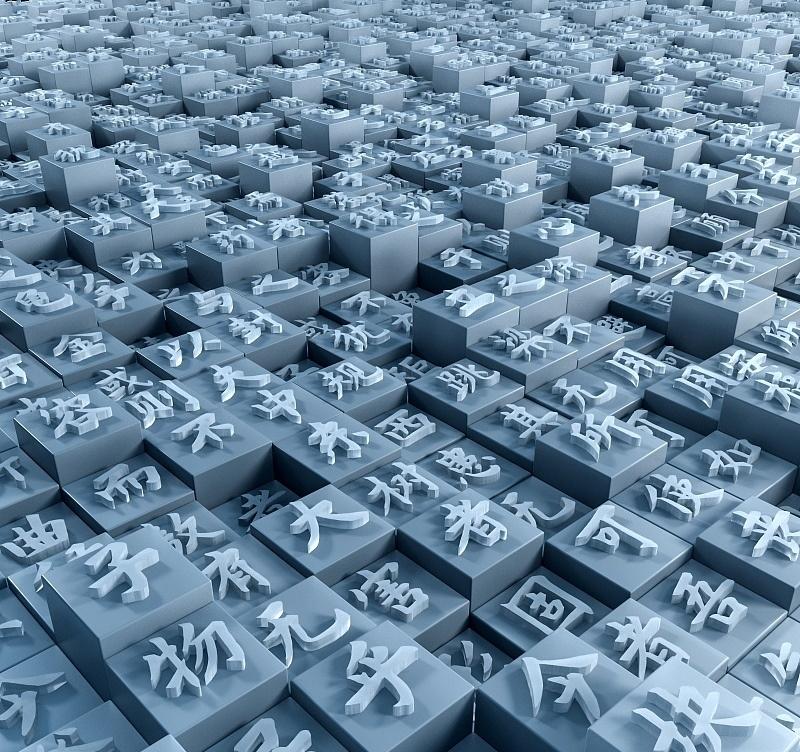
AI曆經疊代學習,如今正成為大衆化寫作工具。圖為創意圖。(視覺中國/圖)
如今,市面上至少有70款AI寫作軟體:它們是寫作模闆,撰寫方案、報告、公文、演講稿和總結;它們是創意導師,提供寫作的想法和創意,幫你修改、續寫和擴充,調整文章情緒;它們是編輯,潤色和批改拼寫、文法、翻譯,檢查原創度;它們是市場經理,總結爆款類型,優化關鍵詞和内容,增加在搜尋引擎的曝光度。
2023年2月,有人在知乎上提問:“AI文學家會獲得諾貝爾獎嗎?”盡管回複者寥寥,但答案幾乎一緻:“不能。”
文學仍然被認為是寫作的最後一塊堡壘。2023年美國福克納文學獎現場,作家們再次提到這個話題,主持人還使用了AI來撰寫演講稿:你認為AI能夠勝任作家和講故事的人的工作嗎?一位作家這樣回答:“我不認為任何人的工作是安全的。”
“文學,不存在了”,AI重新讓“絕望”的作家們齊聚。
在2023年同濟青年人文論壇第八場上,浙江師範大學教授吳翔宇講起1990年代末的一件往事。當時電腦尚未成為創作工具,詩人阿紅請朋友為其做了一個超前的作詩軟體,隻需敲一下Enter鍵,便可以自由組合出一首現代新詩。阿紅曾向許多雜志投遞作品但被拒稿,作詩軟體的這首作品反而受到雜志編輯的青睐。
編輯們回信稱贊“你的時代到來了”。阿紅一時無語,陷入技術迷思。
人工智能已是一支當代的“神筆”。“神筆馬良”故事中,一個叫馬良的孩子獲得一支神筆,從此有了畫物成真的本事。過去,筆常被認為是個人才華的象征。而在新的故事裡,神筆是外在于馬良,具有主導性的力量。
“這樣的工具在不斷地改造,AI創作各種文體(的作品),”吳翔宇說,“給文學本身帶來了翻天覆地的影響。”
每個人都能使用和觸及的工具
多年來,科幻作家陳楸帆以一種十分“科幻”的方式進行創作。
2017年,陳楸帆開始參與語言模型的工作。谷歌的同僚、科幻作家王詠剛主要完成技術性的工作,陳楸帆則為模型提供語料。那時,參數規模有限的語言模型距離真正的寫作仍然很遠。
六年過去,陳楸帆感歎,曆經疊代學習、回報和自我強化,AI已經成為“每個人都能去使用和觸及的(工具)”。
用AI寫小說的視訊教程如今比比皆是。(資料圖/圖)
複旦大學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員戰玉冰說,在AI影響文學的一個讨論中,科幻小說、偵探小說等類型文學的讨論更容易陷入兩極化。一方面,支援者認為,類型文學最容易被AI取代,“這種模式化的書寫是可以進行模仿跟學習的”;另一方面,反對者、偵探小說的粉絲們又堅信,“密室詭計、不可能犯罪等等,是人類的智慧之光,是人工智能所不能取代的奇思妙想”。
AI寫作工具能夠為陳楸帆的類型文學創作充當強大的輔助。比如Sudowrite,這個“故事引擎”服務于科幻、奇幻、偵探、言情等類型小說創作,能在世界觀、人物、技術、情節、故事轉折等方面提供幫助。Sudowrite有浪漫、驚悚、神秘、恐怖、科技等七種風格,它能夠幫助作家創作内容、頭腦風暴、建構角色和情節等。
“它可以幫你發現一些角色,劇情按照什麼樣的套路。比如說‘英雄之旅’,好萊塢的劇本格式,有幾個模闆供你選擇,能夠很快地給你生成一個大概的類型故事。”陳楸帆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你肯定不能完全照着它去做,但這個過程中會有很多啟發。”
陳楸帆曾經暢想,AI在學習某位曆史上的大師的所有文本之後,可以用大師的思維方式去與人溝通。比如,他想與AI版阿瑟·克拉克(編者按,一位已故著名科幻作家)聊一個創意,聽從這位大師的建議。
他還提到Midjourney(著名AI繪畫工具)的幫助。當他把角色的設定輸入進去,AI的作品為他帶來視覺上的參考,“寫到這個角色的時候,我腦子裡出現的就是(AI)肖像,可能很多互動就會變得特别生動起來。”
陳楸帆多次向南方周末記者提到AI生成的内容的“啟發性”,“很快地給你看到很多可能性,挑選你最喜歡的。人類作家其實也一樣,但是我們可能想得沒那麼快那麼全面。”
與AI協同寫作後,陳楸帆感覺到,遣詞造句、劇情走向、人物塑造等一些寫作慣性被逐漸打破了。有時候,AI去描述一個場景,會以想象不到的方式呈現。陳楸帆享受與機器的互動過程,“跳出套路”。
陳楸帆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人機協作還會帶來“心理上的激勵”。過去,他常常苦于走出創作的第一步,那些腦中繁雜的知識,需要一點點整合出來。AI改變了這種狀況,即使要對AI生成的提綱或者模闆改寫、推翻、重寫,“心理障礙”也會小很多。
人機協同創作的過程,往往需要反複嘗試才能得到結果。陳楸帆的編劇朋友給予AI的設定,會具體到劇本格式、人物設定,并令其了解上下文關系。這時候,AI可能帶來驚喜。比如寫到第六集的時候,AI突然給出一個線索,能對接到第四集的某個情節,“他(編劇)自己沒有想到”。
“人的主觀能動性、創造性和想象力,還是在這(AI寫作)裡面起到非常核心的一個作用。”陳楸帆覺得,寫作者本身需要對創作有清晰的預期,“以一個什麼樣的身份,什麼樣的風格,什麼樣的方式去生成一段什麼樣的對話”,指導越詳細,産出的效果越好。
盡管積極擁抱AI,但陳楸帆對目前AI生産的内容評價有限,“比較容易預測劇情的走向,不會有一些特别個人化、旁逸斜出的東西”。過去六年,AI為他的創作帶來了啟發,但是他現階段承認,“大部分的參與可能是讓AI幫我搜集一些資料,做一些總結或者分析,具體到寫,從文字上來講,離得還是比較遠”。
純文學的“防線”
一篇由普林斯頓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紐約大學的學者們撰寫的論文中提及,在AI對774個工作崗位的潛在影響中,作家排名第138位。
“你認為在本世紀,人工智能會寫出一本暢銷書嗎?”南方周末記者詢問ChatGPT。
“盡管未來可能會有更進階别的人工智能文本生成,但要寫出真正引人入勝的暢銷書,可能還需要結合人類的創造力、情感和獨特的人類體驗。”ChatGPT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多位作家、學者相信,“純文學”是AI暫時無法征服的領域。(視覺中國/圖)
關于AI寫作,作家三三提到了《格列佛遊記》中的故事。
拉格多大科學院中的空想設計家,研究如何運用機械操作方法來改變人的思辨知識。通過他的方法,即使是最無知的人,隻要付出學費和體力便可以寫出書來——學徒們轉動巨大機器的把手,語言中所有的單詞及其不同的語态、時态等重新組合,産生新的句子,這些支離破碎的句子最終被拼湊在一起。
目前,AI獨自創作作品的結果,正像這些被機器拼湊起來的句子。
2017年,作家走走辭去《收獲》雜志社職務,之後參與開發了一款數字人文——大資料文本分析軟體。文本裡的事件、節奏、情緒變化等轉化為程式語言,軟體可以畫出沖突曲線模型。據說,曲線模型靈感來自美國作家馮内古特。“他曾提出一個問題,我能不能用一條線畫出一個故事來,從開始到結束有一根線。”
創作者可以借助軟體,進行學術化的研究和寫作。靠着AI這樣“全面的、天眼一般的閱讀者”,戰玉冰曾用12.5小時“讀”完了749部中國網絡小說,總字數七億兩千九百多萬字。
但是寫作者能否借助AI分析軟體進一步學習并掌握某種寫作規律?走走向南方周末記者坦承,無法做到。
“我們現在最大的訓練語料庫幾乎全部是網絡文學,因為網絡文學有明确的分類,有大量的可訓練的語言庫,有大量的非常直白的計算機可識别可打标簽的對話。”走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目前,AI對套路化的“強情節”有強大的沖擊力,卻始終無法沖破純文學的“防線”。
青年作家、《收獲》雜志編輯餘靜如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純文學領域,故事架構沒有十分重要,它可能是一個基礎,但不是決定小說好壞的标準。”餘靜如認為,與純文學不同,也許類型文學中更強調“點子”和“創意”,這更容易得到AI的幫助。此外,創造“神轉折”也是AI的強項。
不過,如果好的點子沒有足夠的叙事細節支撐,“神轉折”不能表達個體經驗和情感記憶,也稱不上成功的創作。走走提到,AI寫作出現後,實際上考驗的是每個寫作者對關鍵資訊的連結能力。人類在文字中投入的感受、追問、反思、自我等主體性的部分,正是純文學的獨特性所在。盡管上述AI分析軟體已經能夠解析人類作品的内容和情緒,卻始終無法輸出這些意涵,寫出文學中那些迷人的、令人驚歎的部分。
走走最近在看契科夫的十卷本,其中有一個短篇故事,寫到了一個女人内心的愧疚感和罪惡感,“你不會用那個時候的‘老天爺’那樣的語言了,我們要模仿的是那種嚴肅的思想。”走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所有的(AI)語料庫隻能給你語言,不能給你後面的東西。”
走走想起畢飛宇的小說新作《歡迎來到人間》,小說男主角一開始是個非常冷漠的人,母親的手切出血來了,他連看都不看,會覺得這跟自己沒關系。“這麼一個冷漠的人是什麼時候覺得要拯救衆生的?一個活下來的患者向他下跪了。文中,他看到夜裡的那些建築物,就感覺這些建築都在向他下跪。作者是根據這個人物發展到現在,才有這麼一筆,這句話AI是寫不出來的。”
走走向南方周末記者展示了小說中的一段話,“傅睿的恐懼就開始痙攣了……像分枝菌絲”。
“寫的是醫生,是以關于恐懼的比喻用到了菌絲(AI分類還真很難那麼細),”走走說,“整段心理描寫,從破折号開始的,也不是傳統AI能提取的。‘要談。要談的’這句話,内心情緒變化由氣憤到緩和一點就差在這一個‘的’字上。這種回環也形成畢飛宇獨有叙事風格。後面破折号引出這段夫妻的故事,過渡句設計AI也是做不到的。”
好的文學是需要“字裡行間”的,需要隐喻,需要“轉譯”日常生活。走走提到自己個人獨有的寫作經驗,這些龐雜、私密的個人經驗如何喂給電腦?她為創作思考本身而感到悸動,幾條線索如何彙合,如何分流,力量何時迸發?這些,AI顯然做不到。
“真正意義上的作家、創造性工作,沒有辦法使用AI。”走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挑戰文學評委、文學編輯
2019年的一天,走走打電話給陳楸帆。走走問,他2018年發表過的一篇小說《出神狀态》,據說使用了AI工具?陳楸帆回答,是的。當時,走走注意到小說後的一段話:“帶*号楷體字部分為AI程式通過深度學習作者風格創作而成,未經人工修改。”
走走說,AI評委在“閱讀”了2018年中20本文學雜志刊發的全部771部短篇小說後,《出神狀态》的得分是最高的。
所謂得分,是AI通過資料分析評判文學作品,包括判斷情節之間節奏變化規律、結構的流暢程度等,得出的系數。也就是說,AI在衆多人類作品中,準确甄别出另一個AI的痕迹,這是人工智能界的高山流水覓知音。
陳楸帆覺得,“這是一件非常科幻的事情”。
《思南文學選刊》也是這份AI榜單的合作者,主編黃德海表達了對結果的興趣。除了AI在文學方面的可能性。另一個理由是,文學排行榜,不管評選結果如何,總有人質疑評委的專業度,抑或認為評選結果依賴的是人情——“那麼,一個相對中立的選擇标準,會是比較好玩的吧?”
論壇上,詩人木葉說,當文學獎不再依賴于某某著名評論家、某某雜志主編等,現在來看,結果仍然是難以預料的,因為會産生一系列問題——“審美是什麼,文學是什麼,才華是什麼,有沒有公平?”
走走深知AI評委目前的局限性,它能識别節奏感、叙述強弱、結構工整等,卻無法辨識語言的好壞。
前段時間,餘靜如和AI玩了一次寫作接龍遊戲,得到了一個略感失望的遊戲結果:“它沒有給我帶來那種能夠寫小說的快感,或是跟人互動那樣的感覺。”
餘靜如設定的是一個荒誕故事的架構,情節以一個小孩在前往村莊的路上,撿到了一隻豬腿開始,之後小孩每走一段距離,都會撿起豬的不同部分,最後這些部分可以拼在一起組成新的生命。
這種奇怪的設定令AI感到困惑,它總是在尋找一個現實邏輯并試圖将故事推向現實的方向。“在這個過程中,這個故事被弄得亂七八糟,”餘靜如對南方周末記者說,“AI沒有辦法自圓其說,而且總是很倉促地要去結尾。”
雜志社中的一些插圖開始使用AI繪畫技術。餘靜如發現,同AI創作的文字的回報結果相似,一旦稍微涉及人類的精神世界或者違反現實邏輯的内容,AI便無能為力,甚至做出奇怪的、并無美感的東西。
總之,現階段的AI似乎對餘靜如這樣的編輯幾乎沒有什麼幫助。餘靜如形容,如果把AI比作一個人,那會是“一個功利性很強、目的性很強、知識面很廣,但沒有什麼想象力、沒有什麼創作天賦的人”。
從目前專業編輯對故事模式、語言等多方面鑒定來看,AI作品很容易和人類作品差別開來。往往在第一句話,資深編輯便會看出“錯亂”。
但是,編輯們的憂慮已經開始了。美國的科幻雜志編輯們已經開始收到大量由AI創作的小說作品,并加重了其工作負擔。2023年2月,一位美國雜志的主編尼爾·克拉克在部落格中提到一個令人擔憂的創作趨勢:“AI故事”投稿明顯激增。2月份,有七百份人類投稿和五百份AI投稿。
“技術隻會變得更好,是以檢測将變得更具挑戰性。”克拉克提到,第三方用以鑒别機器寫作的工具價格高昂,短篇小說市場難以負擔其重,“它不會自行消失,我也沒有解決方案。我正在修補一些,但這不是一個任何人都可以赢的‘打鼹鼠’遊戲。”
《上海文學》編輯、書評人吳昊說,作為一線編輯,他已經察覺到,這兩年的自由來稿中,AI元素越來越流行。在《上海文學》收錄的一篇小說中,作者創造了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人都可以寫出一首令人稱贊的詩,每個人都是李白,“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借助AI,借助雲儲存,随時随地調用這個世界曆史上存在的任何文學流派。”吳昊說,他能感受到小說家内心的危機感。
吳昊相信AI的參與未來能創作出更好的文學作品,但是“現在的問題是,我覺得能夠比對現在AI熱度的,(AI創作的)真實的、優秀的文學作品還相對比較稀少。”
“人類的創作過程跟AI沒有本質差別”
關于AI創作能力,早在2017年就曾引發讨論。AI“小冰”出版了第一本人工智能中文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出版詩集之前,小冰曾用27個化名在各大平台發表作品,從未被人發覺真實身份。
小冰學習了1920年以來519位中國現代詩人的詩作,經過一萬次疊代學習後,終于獲得了現代詩的創造力。語言模型的内容生産結果,往往由調教者根據自己的審美品位進行微調。小冰式的詩歌,與調教小冰的工程師的品位和詩歌偏好有關。
AI創作漢語新詩的結果,令人想到那些關于現代詩的批評。“很多新詩寫作被大家譏諷為‘敲一敲Enter鍵的工作’。”青年詩人、複旦大學博士曹僧認為,AI可以當作一種語言環境檢測器,據“吐出的東西”,可以“幫助我們發現語言本身的情況”。
未來的一種趨勢,AI有望成為作家日常工具的一部分,陳楸帆形容,就像日常使用的word那樣簡單。陳楸帆嘗試AI協同創作了一系列的作品,他會有意識标出哪部分是人創作的,哪部分是機器創作的,最後給予署名,以表達對知識産權的尊重。
陳楸帆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國外使用AI進行創作的作者比較多,他認識美國幾位雜志社主編會收到這樣的作品——懶惰的、直接大段使用、格式都未改過的AI作品。
吳昊認為,作品永遠是文學刊物和文學編輯最關注的東西,“AI所帶來的挑戰是人類編輯如何在未來去建立一個作品的AI系數。”吳昊說,在不久的将來,也許純文學期刊會和作者簽訂協定,杜絕AI參與協作的可能,或者需要标注AI的參與程度。
吳昊設想,對于一本純文學雜志而言,AI已經可以取代大部分人類編輯的工作,如基礎修改工作,“一個資深編輯可能有一個很成熟的作者群,你對這個人的了解可能會幫助你對他的作品修改。但是對于自由來稿,是不是将來AI崛起後,直接把自由來稿放進AI,它就可以告訴你大緻上你能不能用。”
在六年的協同工作裡,陳楸帆其實一開始糾結于AI對主體性、原創性造成的破壞,但是最後卻得出結論“人類的創作過程其實跟AI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人們通過界面擷取更多模态更高次元的資料。
他讀過科幻小說《降臨》作者特德·姜的文章《ChatGPT是網上所有文本的模糊圖像》,“ChatGPT是一個模糊的被壓縮過的對真實世界的JPG圖像,人類何嘗不是?人類對外部世界的感覺,同樣也是經過了各個感官的壓縮,一個變形的扭曲,甚至刻意的遺忘,它的這種壓縮的比率甚至比 AI還要更嚴重。”
2016年,日本一篇由人工智能創作的小說,在“星新一微型小說文學獎”的比賽中通過了初審,不過并未獲得最後的獎項。這篇名為《電腦寫小說一天》的小說寫道:“我高興地扭動着,這是我第一次體驗到的,并興奮地繼續寫作。電腦寫小說的那一天。計算機優先考慮追求自己的快樂,不再為人類工作。”
南方周末記者 張銳
責編 劉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