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釋出于“新京報小童書”。新京報小童書(xjbkids)是書評周刊的童書分舵,已聯合衆多出版品牌,為讀者精選童書,解答教育困惑。
——
童書市場有大量的引進版圖書,目前大家讨論得比較多的依然是以圖畫為主的繪本,對于以文字為主的兒童文學作品,主要依靠作品自帶的光環來吸引注意力,比如作品在海外獲得的獎項、作者的知名度和某些機構的推薦。至于作品本身為何能得獎,作者為何要這樣寫作,作品是否沿襲了某種曆史,取得了哪些創新,最重要的是,這些對于兒童和青少年的意義又是什麼,常常不為大衆所知。再加上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對作品的了解。造成的一個直接結果便是,一些童書買回家,卻依然不了解宣傳語為什麼稱它為經典。
是以,從本期開始,我們将推出一個新的專欄,名為“兒童文學通識課”,先從經典作品較多的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兒童文學入手,提取多個主題,包括“二戰時期的兒童文學”“童話故事裡的人和動物”“童話的改編與流傳”“兒童文學如何在電影中呈現”等,探究作品背後的文化因素和它們真正想表達的意義。
這個專欄的兩位作者是桑霓和子葭,專業是比較文學,桑霓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子葭畢業于布林茅爾學院,這些主題來自他們在牛津大學做通路學生時上的兒童文學課。每一篇文章都是與教授一對一進行一個多小時的讨論後完成的,經曆了大量的資料查閱、找思路和列提綱的過程。有一些觀點可能頗為大膽,也歡迎你與我們探讨。
兒童文學雖是一門學科,但相關的圖書卻是由老師、家長等大人為孩子挑選,大人的教育目的和孩子的興趣點常常難以達成一緻,兒童文學的定義也在不斷被讨論。今天推送的第一期是桑霓的文章,原标題為“大問題:兒童文學是什麼?”從作家與作品的關系看作家隐藏在兒童文學中的觀念表達。黃曉丹的文章《至今為止,我對世界的了解從未超出童年時讀過的那些書》也能從讀者的角度印證這種表達。
需要強調的是,廣義上的兒童文學包括了繪本等一切給兒童閱讀的書籍(Children‘s Books),但在童書的閱聽人市場,兒童文學一般是指以文字為主的小說,下文中采用的是這個狹義上的定義。
撰文 | 桑霓
01
我們需要探讨
兒童文學作者和他們作品之間的關系
許多知名文學批評家和學者,比如加拿大學者佩裡·諾德曼(Perry Nodelman,代表作《兒童文學的樂趣》)、英國卡迪夫大學兒童文學榮譽教授彼得·亨特( Peter Hunt,代表作《批評、理論與兒童文學》)、英國雷丁大學國際童年研究中心主任卡琳·萊斯尼克-奧伯斯坦(Karin Lesnik-Oberstein,代表作《權力與兒童書籍:講授神話、童話、民間故事和傳說》)等,都曾嘗試為“兒童文學”建立可行的讨論範圍及架構(framework)。
在此過程中,他們要麼嘗試理論性定義“兒童文學”這一 “類别(genre)”,要麼尋找其與讀者、發行商和文學傳統之間的關系和對他們的影響。這些學者的讨論有同一個先行假設,那就是“兒童文學(Children’s Literature)”或者是“給兒童寫的書 (Children’s Books)”都在優先考慮一個特定的讀者群體 ——兒童,盡管兒童文學的創作、出版和發行其實是一個屬于成年人的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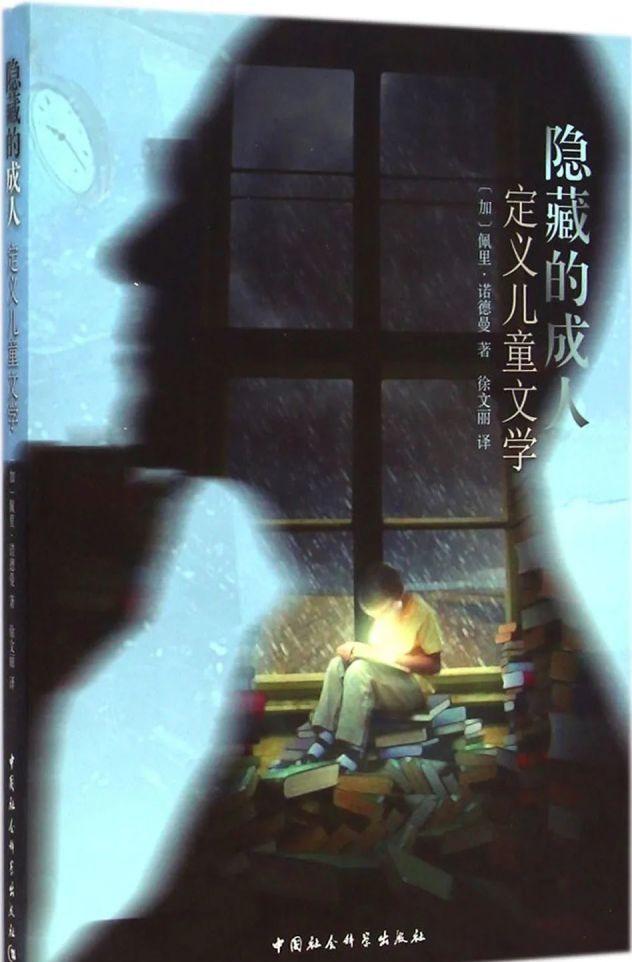
《隐藏的成人:定義兒童文學》,[加拿大] 佩裡·諾德曼 著,徐文麗 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11月版。
就如佩裡·諾德曼在他的著作《隐藏的成人:定義兒童文學》(The Hidden Adult: Defin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中提到的,“兒童文學是出版商希望孩子們閱讀的作品,而不是孩子們自己想讀的。”這些“孩子們的書”不僅由成人作家創作,也主要面對着成人購買者,包括父母、圖書管理者和老師,而這些成人購買兒童讀物的标準則是基于他們對“什麼樣的書适合兒童閱讀”的了解。由此看來,兒童文學這一“類别”在很大程度上被成人控制和塑造。在被成人定義、操控、創造和想象的過程中,“兒童”以及“兒童讀者”也常常成為被動的客體。
雖然許多學者基于“兒童”和成人之間的權力關系進行了深入的讨論,但他們的理論分析還是更着重于從讀者的角度看待“兒童文學”如何影響讀者,以及這些作品在傳達什麼樣的資訊,并沒有探讨兒童文學作者和他們作品之間的關系。
值得關注的是,當一部“寫給兒童的書”被創作并投入市場後,是讀者和批評家在決定着它是否适合“兒童”閱讀。這些書籍的作者在他們的作品究竟是不是應該被特定的文學類型标簽定義這一問題上缺乏話語權,很有名的例子是小說《歡樂滿人間》(Marry Poppins,同名電影獲得第37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提名,講述的是一位仙女化身為保姆來到兩個孩子身邊,幫助他們重新感受到親情和友情)一直被看作是兒童文學的經典作品,但是它的作者帕梅拉·特拉弗斯(Pamela Travers)曾直接否定這本書是“為兒童創作的文學”。
電影《歡樂滿人間》(1964)劇照。
02
被分類為“兒童文學”的作品
很可能并不是為兒童所寫
在許多論述中,有關作者和創作本身最為重要的問題沒有被讨論和解答:這些作者究竟在為誰寫作?是什麼推動他們在作品中創作一個童年?在 “兒童的世界”背後隐藏着怎樣的心理欲望?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将有助于了解“兒童文學”的誕生機制,進而幫助我們更深入地了解 “兒童文學”作為文學類别所隐含的共通性。在接下來的讨論中,筆者将去探讨為什麼我們應該重視從作者的角度看待兒童文學的創作,以及他們和書中“被創作的童年”之間的關系。
在探索中筆者發現許多作家都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放入“兒童文學”這一類别中。作家司各特·奧台爾(Scott O’Dell,代表作《藍色的海豚島》) 曾提到,“那些被分類為'為兒童所做的書'的作品其實不是為兒童所寫的”, 而J.K.羅琳也說過,“如果一本書有吸引力,那應該是對所有人都産生了吸引力”。
《藍色的海豚島》, [美] 司各特·奧台爾 著,傅定邦 譯,新蕾出版社2017年5月版。
一方面,他們的觀點表示他們的作品應和“嚴肅文學”同樣受重視,并且是海納百川的,而非被類型拘束和限制。同時,他們也在直指兒童文學讨論中“房間裡隐形的大象” ——兒童文學所使用的某些元素,比如純真性、幻想世界以及相對直覺的故事線,讓它們本質上比成人文學更加淺薄。如此,對于兒童文學的偏見建立在一個武斷的類别分界線上,忽視了“為兒童創作”這一概念中 “兒童”不僅僅指代着生理年齡上年輕的兒童,也可以指代那些“已經長大了”的兒童。
當然,不可忽視的是,許多被看作“兒童文學”的作品确實使用了相對更直覺的文學手法以及技巧。那麼,是什麼讓這些作家如此自信地說他們的作品包含了“足夠的深度和複雜性”,以至于可以比肩狄更斯或是莎士比亞的作品呢?
著名奇幻作家菲力普·普爾曼(Phillip Pullman,代表作《黑暗物質三部曲》)曾在1996年的演講中解釋這一争議:“有一些主題,核心對于成人作品來說過于宏大;它們隻能在兒童的書籍裡被足夠好地展現”。基于普爾曼的言論,彼得·亨特作出了更加深入詳盡的解讀:“成人的大腦……相比兒童的大腦更加不可能接受圖像,氛圍以及未經引導的隐射” 。
他或許暗示着當讀者有着“孩子一般的眼光”時,他們更容易跳脫出成人社會生活所附加的意識形态、定義、思維慣性等元素,并且容易從文本中了解出更多的可能性以及深刻的意義(此時我想到了道家學說中的無名)。這也許從側面解釋了為什麼衆多兒童文學作品中的主角一定都是孩子,因為孩童般純粹的眼光是這些作品的核心之處。
英劇《黑暗物質三部曲》第一季(2019)劇照。
03
從成人的世界退後一步,
再用孩子的視角去審視、挑戰成人
跳脫出意識形态束縛的自由能帶來許多好處。當作者摒棄許多社會上的規則與教條時,也在為自己尋求更自由的創作空間。這一自由的創作空間可以讓他們的角色更加深入地探索自我,甚至問出不符合常理的“幼稚問題”來展現角色的内在思考,而這些思考也展現着主角們對自我、個體以及和外界建立關系的覺知過程。
以《愛麗絲漫遊仙境》為例,它的主要角色時常問出看起來不可思議的荒謬問題,又同時尋找着看起來無厘頭(nonsense)的答案,而正是這一充滿思維探索的旅途讓愛麗絲真正成為“自己”。
比如,在《愛麗絲漫遊仙境》第二本《鏡中奇遇記》裡,彈彈丁(Tweedledee)問愛麗絲紅國王(Red King)在夢中見到了什麼,他說:“如果他不再夢到你了,你認為你會在哪裡呢……你哪裡都不在。為什麼呢,因為你就隻是他夢裡的一個東西。”彈彈丁的一系列問題和解答正是存在主義哲學的核心思考之一。愛麗絲的故事在不斷地挑戰角色對于外界和自我的既定認知,比如紅皇後就不斷鼓勵愛麗絲去相信不可能的事情,也表現着作者卡羅爾對于“個體”的了解——主角正在成為一個擁抱變化、直覺和随性,又在不斷思考自我和外界關系(有時甚至形而上)的人。
同時,這樣的創作為作家們創造了一個相對安全的空間,讓他們從成人的世界退後一步,用孩子的視角去審視、挑戰并且批判它。
J.K.羅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創造了一個真實世界複制版的巫師世界,其中存在着種族、階級等元素之間的沖突。故事發生在青少年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身上,他們在冒險以及對抗伏地魔的過程中不斷揭露和反抗着人性中“黑暗”的一面。當然,他們的三人組也在不斷地打破各式各樣的規則,并展現着珍貴的勇氣、義氣和善良,與成人角色的行為進行對照和呼應。
文學批評家卡琳·韋斯特曼(Karin E. Westman)曾寫道:“通過融合一種重視讓讀者與哈利共情的叙事方法以及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這一文學類别,羅琳鼓勵她的讀者同時用懷疑和共情的眼光看待成人世界,羅琳也更加關注奇幻文學怎樣提供一個看待每天生活經驗和個體在社會中位置的視角”。可見,選擇用兒童的視角去講述有社會批判意義的故事也可以反映出深刻的思想與主題。
電影《愛麗絲漫遊仙境》(2010)劇照。
04
重新創作童年的過程,
也是一個探索與自我關系的機會
在創作故事線和角色的基礎之上,重新創作童年的過程也許為作家們提供了一個主動或是在潛意識中探索與自我關系的機會,并進行存在主義式的思考。如同批評家卡琳·萊斯尼克-奧伯斯坦所寫:“精神分析的一種理論支援我提出的 ‘兒童’是被建構和創造出來的概念,也提供了與利用起這一被建造的‘個體’(‘兒童’和‘成人’)的想法的不同方法”。這一關于自我探索的議題和方向可以被許多作者的觀點印證,他們不約而同地強調着是在為自己寫作。兒童文學作家威廉·梅斯(Wliam Mayes)直接寫道, “我為自己寫作,但是一個很久以前的我”,而J.K.羅琳也曾說過“我主要是為了自己寫作”。
但是當他們說“我在為自己寫作”的時候到底在表達什麼意思?他們的“自我”和他們的作品之間的關系究竟是什麼?我發現,作者們表達了幾種不同層次的動力和覺知:
(1)他們對于回到童年并且再次成為孩子充滿渴望。作家伊萬·索薩爾(Ivan Southall)曾寫道:“我全身心地與兒童同在,我成為一個兒童,在一本書的紙張裡我的心和孩子的心一同跳動着,我成為一個孩子……這個孩子應該成為你的一部分”。這位作家在表達着一種重新回歸童年,成為孩子的欲望和懷舊感,也表示着人的“兒童”時期對于自我認知的重要性。
有許多人和作家都将無憂無慮的童年視為自己的“黃金時代”,并将兒時觀察到的許多元素應用在自己的作品之中(包括喬治·奧威爾,也曾直白地表達過對童年時期的懷念和熱愛,沈從文的作品中也常常有童年相關的元素)。
(2)如弗洛伊德所提出一個人的兒童時期是建立“自我”的關鍵點,這些作者也通過寫作在更深層次地進入并探索着塑造了自我認知的潛意識。理論學家弗朗西斯·斯帕福德(Francis Spufford)曾在成人閱讀兒童文學的好處上提出非常有力的觀點,他說:“這些書成為了我們自我認知過程的一部分。那些對我們意義最為重大的故事融入了我們真正成為自己的過程。”
許多作家都曾直白地表達在寫童書時重新成為孩子的快樂,比如羅爾德·達爾曾說:“我和孩子們因為同樣的玩笑哈哈大笑……而是以總是有着最棒的靈感。”而劉易斯·卡羅爾也說過,“當我們在為孩子寫作的時候,我們在使用着我們和孩子們的想象力中相同的元素”。彼得·亨特也曾将《愛麗絲漫遊仙境》中的無厘頭元素當成“有趣的無厘頭”。雖然以上提到的作家來自不同的曆史時期,但他們的觀點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以孩子的角度思考的重要性、愉悅性,以及給他們創作帶來的關鍵切入點。
羅爾德·達爾作品《女巫》中的插圖。
05
描繪想象的世界時,
也将對童年快樂的向往融入了寫作
在此基礎之上,筆者将提出有關這些作家寫作原動力的第三個觀點:這些作家在重塑童年和描繪想象中的世界的時候,也将自己對于童年純粹快樂的向往融入了寫作。
他們的寫作也許是一種反抗成人世界中意識形态、政治、社會習俗等對所有鮮活的個體壓迫的方式。在他們創作的世界中,他們可以操控一切“現實元素”,使用自己的想象力将這些元素重組,并在完全由他們創造的世界裡享受着充滿童趣的玩笑、有意思的冒險,并且塑造出那些無拘無束、打破傳統的主角們。
同時,他們也許是在通過寫作補償自己不滿意的童年生活,包括自我所經受的童年創傷及痛苦,并通過他們的想象力去塑造一個更理想的自我,在寫作的過程中讓孩童時期的自我重生。當我們以精神分析的角度繼續深入“潛意識的兔子洞”,可以發現童書的創作也許隐含着更多的欲望表達。
當我們在談論“兒童文學”的時候,也要避免就這一有争議的“文學類别”去總結出代表性的籠統定義,因為“兒童文學”的天花闆下總蘊藏着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不過作為讀者和批評者,我們需要承認“兒童文學”對于兒童和成人的吸引力常常來自于這些書籍對于童年時期的塑造,以及這些故事與我們個體的經曆、期待和想象的呼應。畢竟對于許多人來說,童年是他們一生都在不斷回味和懷念的時期。基于以上的所有讨論,我想提出一個有關“Universal Child”,即一個包含所有人共性的孩子形象的設想。當我們去閱讀兒童文學的時候,是否有一個人類共通的審美意識在引導着我們?
批評家美狄揚(Mei de Jong)對于重返童年的概念曾如此解釋:“穿過你自發潛意識中的所有深厚、神秘的層面,回到你的童年。如果你探索的足夠深,看到的足夠本真,并且重新成為童年的自己,你很可能已經通過你的潛意識成為了那個Universal Child。”對于兒童文學的研究不僅和文學研究的各個理論方向息息相關,也在幫助所有讀者和作家探尋着我們内心深處的那個自我。
參考資料:
1.James Kincaid, The Hidden Adult: Defin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0
2.James Kincaid, The Hidden Adult: Defin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140
3.Julia Mickenberg and Lynn Vallo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Julia Mickenberg and Lynn Vallo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106
5.Julia Mickenberg and Lynn Vallo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197
6.Julia Mickenberg and Lynn Vallo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97
7.Karin Lesnik-Oberstein, Children’s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 Fictional Child (Oxford: Oxford UP, 1994)168
8.James Kincaid, The Hidden Adult: Defin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168
9.Julia Mickenberg and Lynn Vallo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103
10.Julia Mickenberg and Lynn Vallo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191
11.Spufford, Francis. The Child That Books Built: A Life in Reading.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1.
12. Roald Dahl Website
13.James Kincaid, The Hidden Adult: Defin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191
14.Julia Mickenberg and Lynn Vallo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43
15.James Kincaid, The Hidden Adult: Defin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