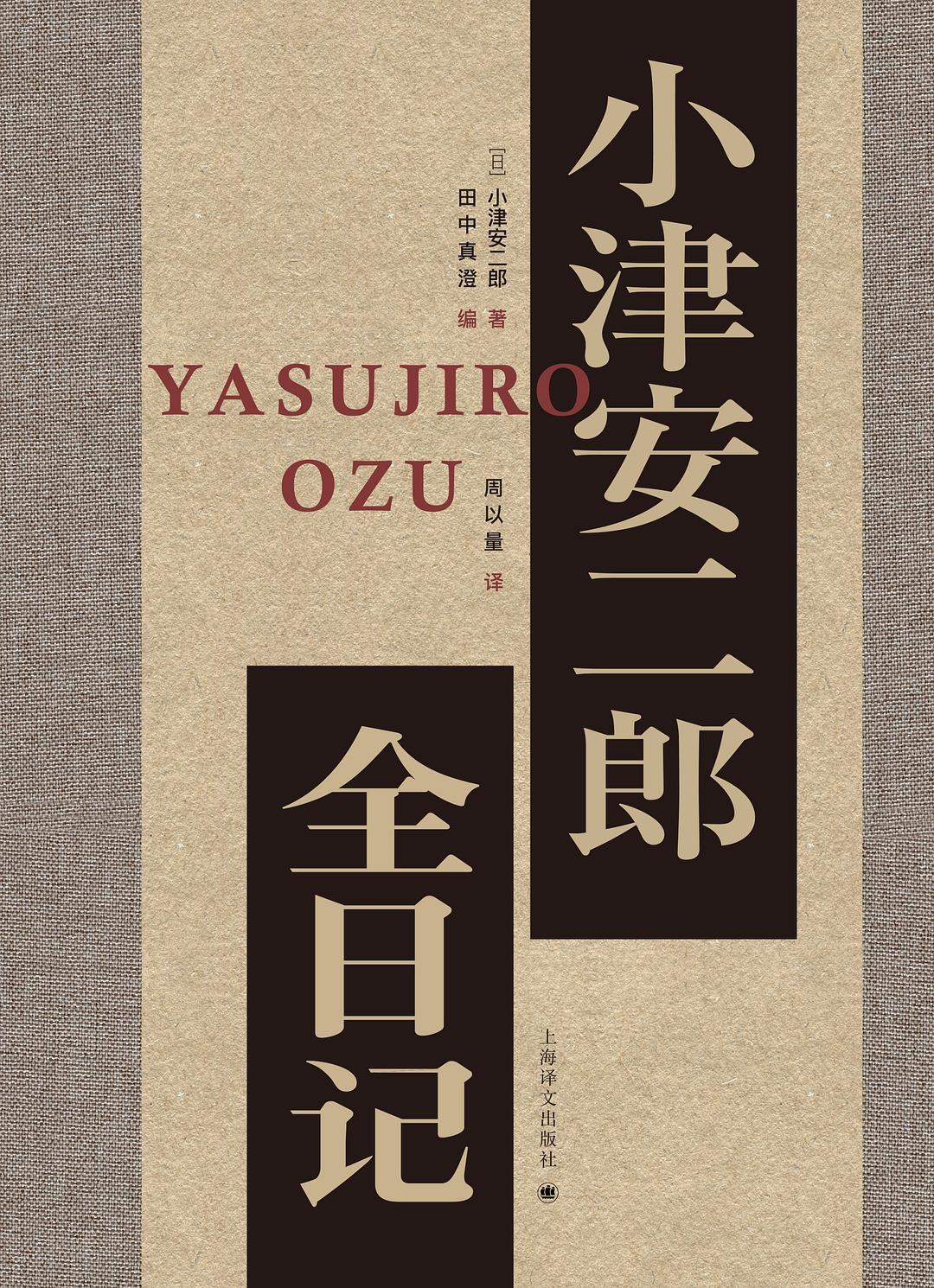
名人日記裡有許多内容是很诙諧的。胡适每天賭咒發誓不打牌,結果每天都疏于學業忙于打牌。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是個“低俗小說”深度讀者,每天掙紮在正經做學術和讀閑書之間。小津安二郎的日記也可以歸到這一類,從1933年到1963年,他斷斷續續寫30年日記,大多數時候是個吃貨事無巨細地記下“喝紅茶”“吃俄羅斯點心”“吃雞肉火鍋”“吃豬肉豆腐”“吃紅豆飯”,不出意外地間雜着“喝酒”,很多次地“喝醉了”。
這不意外,小津的電影裡,同樣有許多的食物和酒。他的電影裡,有兩部直接以食物命名,分别是《茶泡飯之味》和《秋刀魚之味》,他沒能完成的劇本遺作叫《蘿蔔胡蘿蔔》。
在婚喪嫁娶的日常故事裡,飲食飲酒負擔了衆人的悲歡。
《晚春》的結尾含悲,紀子嫁了,父親枯坐在空曠下來的家裡,獨自削着蘋果,孤單的身形定格在仿佛永恒的死寂裡。《茶泡飯之味》是諧谑的輕喜劇,鳳凰男高攀白富美,身家背景差别太大的小兩口過不到一起,時常怄氣,男主總是加班很晚歸家,偷偷摸摸地吃剩茶泡冷飯,這竟成了他生活中最輕松快意的時刻。
《秋日和》的色彩明豔濃烈,上了年紀的長輩們讨論“吃胡蘿蔔,豆腐,香菇……”,當場有人異議:“也想吃牛排和炸豬排呢。”《秋刀魚之味》裡并沒有出現秋刀魚,這種魚在初冬寂寥的季節出現于海岸,吃秋刀魚的季節難免有生命凋零的傷懷感,恰似片中的老家夥們在酒局中讨論起壯陽藥。戰後進入消費社會的日本,《麥秋》裡那種傳統大家族逐漸解體,代際的疏遠和撕裂滲透到衣食住行的細節裡,《秋刀魚之味》的老父親平山日常去居酒屋喝一杯,而他的大兒子喜歡的高爾夫球,他和媳婦新組的小家庭裡,家常的食物是漢堡、煎蛋和火腿。
食物之外,小津日記裡落筆最多的是天氣。
“雨夾雪,沼津旅館裡,蚬湯鮮。”
“雪積了起來。喝啤酒。”
“要下雨了。櫻花還沒有完全綻放,今年春天看不到櫻花盛開。”
“雨下了一整夜。牡丹花都凋謝了。桔梗長得很高。”
緻力于研究日本電影研究的學者唐納德·裡奇曾總結過,小津電影裡的角色異常關心天氣,常常在氣氛緊張微妙的時刻,他們開始談論天氣。《東京物語》裡,母親去世後,父親在衆人面前突然說出:“今天會很熱。”《早安》裡,一對雙向暗戀的年輕人在車站遇上,沒話找話地說着:
“好天氣可遇不可求。”
“那片雲彩的樣子真是生動有趣。”
食物構成了恒久日常的堅實質地,天氣是戲劇性被過濾之後仍然旁逸而出的尋常生活的詩性。人物可以不響,雨雪仍有表意。小津在電影裡警惕天氣的“詩性”語言,克制着不許晨昏交替和風雨如晦的畫面出現,隻留下白晝和晴天。日本學者蓮石重彥曾總結過,小津的電影片名雖有強烈直白的季節感,如《晚春》《麥秋》《秋日和》,但季節的痕迹在他的電影裡是模糊的,他的畫面總是明亮幹淨。
黑澤明的電影裡有雨,溝口健二的電影裡霧氣彌漫,小津的電影卻似乎停駐在無休無止無邊無界的白日豔陽天。在他成功的、受歡迎的電影裡,“晴朗”是他創造的修辭。這種修辭,如他偏愛的巴赫音樂,創造了嚴謹的節奏和結構之美。
而“風雨”是他克制的真實感受,他的最後一部黑白電影《東京暮色》裡有罕見的黃昏暮色和細雪,彩色版的《浮草》裡有滂沱的雨,這兩部被認為“不成功”的小津電影,偏偏是他放棄情感管理後偶然的真情流露。
《麥秋》緊随《晚春》,都是大齡姑娘找對象的故事,小津說,他想在相似的情節裡表達“人受到自然與人事的不同情境觸發的感動”。拍完《麥秋》,他覺得“結果不夠理想”。直到9年後拍《秋日和》,他說:“這次做出來了,但不夠徹底。”
或許小津沒想到,他最頑固的藝術觀念是在日記中得到“徹底”實作的:時間怎樣在一個人的生命中落下印記。
1923年,19歲的小津成為松竹片廠的攝影助理,田中真澄在《小津安二郎周遊》寫到了“少年阿津”:“筋骨強壯的少年穿藏青地碎白花紋的衣服,腳穿厚木屐,出現在片廠……輕巧把沉重的攝影機扛到穿着汗背心的肩上,靈活地跑着。”
《小津安二郎全日記》收錄的第一篇時間是1933年1月1日,這時他開始做導演,表達欲旺盛,在日記裡寫詩寫俳句,“日暖光燦燦,春野花香難尋覓。春淺霞光重,麥苗漸露色青翠。”詞句裡有敞亮的樂觀。到了1963年,相依為命的母親去世後,獨居的小津進入枯井般寂寥的生活,他的日記不是寫給“不存在的讀者”,也不是和自己的交流,片言隻語隻是時間不停歇流逝的痕迹:“整天在家。”“終日睡覺。”“無所事事。”“安靜地送走一年。”
默片與有聲片時期的小津對比,風格差異甚大,這種變化的痕迹和戰争帶來的職業中斷是重合的。從《晚春》《東京物語》這些名作進入小津世界的觀衆,初看1934年的《浮草物語》很可能會感到意外。那年小津32歲,翻看他當年的日記,關于《浮草物語》拍攝的内容不多,7月末寫完劇本,8月初勘景,10月初開拍時,他想盡快拍完,搬家去鐮倉。11月17日,電影拍完最後一個鏡頭,5天後就完成剪輯、公映了。短暫的拍攝周期裡,最有趣的一筆記錄是“夢見與田中絹代喝茶,是個有禮節的夢。”小津在《浮草物語》裡,拍着江湖戲班的混亂和流浪藝人的悲歡,30出頭的他,對藝術和藝人的“浮浪”有着清醒仍不乏溫存的認知,他用肆意的、不克制的影像拍出了一段充滿意外和失控的人生——外部世界和命運都是無法控制的,但他既不怨,也不懼。
三年後,戰争中止了小津安二郎的導演生涯。他入伍,在南京的古城牆上,他見識過理性和秩序崩塌後的世界。待他幾經沉浮、經曆了一段國外旅居的時光回到松竹片廠後,戰後的日本天翻地覆,而他從“藝術家的廣闊世界”退回到“父與女”的家庭中。小津的嫁女故事是無關現實主義的,他借用“家庭”的概念創造了父母與子女自洽的小世界,那個世界原本可以是封閉完整的,卻一次次迫于倫理和社會秩序的壓力,因為女兒的出嫁而面臨解體。
1959年,小津為了兌現和友人的諾言,把《浮草物語》翻拍成彩色版《浮草》,他對新版的重視遠甚于25年前“無意草就”的原版,這一年有大半年的時間,他在日記裡談論《浮草》的籌備和拍攝。内心如此在意,現實卻與願違,大部分時候他在日記裡寫下的是“很不順利”。這是苦澀的認知,以事後之明來看,這位老成的導演用《晚春》以後積澱的精确如數學的視聽方案和節奏,其實無法再現年輕時那份生動的、充斥着不确定感的浮浪。或者,他已無法從容坦然地面對命運的不可測和不可控。
那時日本新浪潮已經開始,小津的學生今村昌平将叛出師門,年輕一輩的創作者激進地在全新的表達中尋找世界碎片化的真實。而小津頑固地在電影的修辭中捍衛世界四分五裂前脆弱的“完整”。《秋刀魚之味》裡,盛年盛裝的女兒回眸,那是燦爛又傷感的道别,笠智衆扮演的父親在女兒離開後,孤身醉倒于小酒館,凄涼的軍歌循環播放着,他的時代過去了,他的世界翻篇了——他是小津的代言,這是小津的自況和自哀。
1955年元旦,小津在日記裡記道,“川喜多夫人送青魚籽,意思是‘雖然味道足,但不谙世事。’”其實他未必不谙世事,隻是拒絕而已。
劇照均為資料圖檔,書影為出版方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