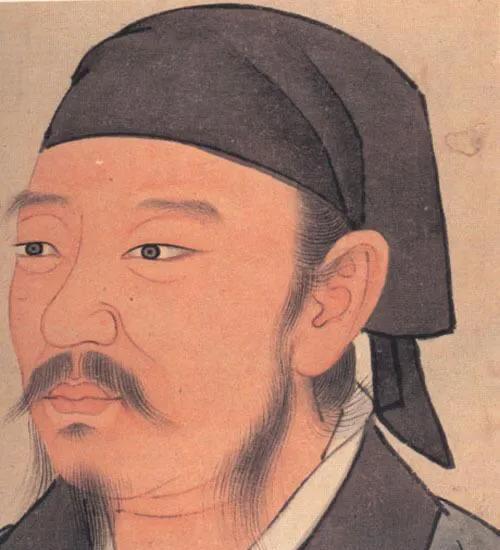譯注:方勇 李波
出版:中華書局
王制
一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鄭而化。分未定也則有照缪。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于禮義,則歸于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故奸言、奸說、奸事、奸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
譯文:請問如何治理國家?回答說:賢能的人不必按照等級次序進行提拔,軟弱無能的人可立即罷免,罪魁禍首不需要教育就可以殺掉,普通百姓不需行政力量就可以教化。名分未定時就應像昭穆那樣确定上下等級。即使王公士大夫的子孫,不能遵守禮義,也要歸入平民百姓。即使平民百姓的子孫,隻要積累了知識,行為端正,能遵守禮義,就歸入卿相士大夫。是以那些傳播邪惡的言論、鼓吹邪惡的學說、做邪惡的事情、有奸邪的才能、逃跑流竄和反複無常的人,就要強制他們工作并進行教育,耐心地等待他們轉變,用獎賞勉勵他們,用刑罰懲治他們,安心工作就留下,不安心工作就抛棄。對有殘疾的五種人,國家收留并養活他們,根據能力安排工作,官府任用他們并提供衣食,要全面照顧沒有遺漏。對那些用才能和行為與時事對抗的人要堅決殺掉不能赦免。這就叫做天德,是聖王所采取的政治措施。
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别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凡聽,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則奸言并至,嘗試之說鋒起,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故法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必隊。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隐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譯文:處理政事的要領是:對懷着善意而來的要以禮相待,對不懷善意而來的要以刑相待,把兩者區分開,賢能的人和不賢能的人不摻雜在一起,那麼英雄豪傑就會到來;是與非不混亂,那麼國家就會治理好。像這樣,名聲就會一天天顯赫,天下人就會仰慕,就會有令行,有禁必止,王者的事業就完成了。凡是處理政事,如果過分威嚴猛厲而不喜歡寬容引導,那麼下面的人就會畏懼害怕而不親近,就會隐瞞實情而不全講出來。像這樣,那麼大事就會廢弛,小事就會落空。如果凡事随和,喜歡寬容而沒有節制,那麼邪惡的言論就會一塊到來,嘗試性的學說就會蜂擁而起,像這樣,聽到得太多,事情就會煩瑣,這對事情有損害。是以制定了法令而不加以讨論,那麼法令所涉及不到的地方一定會廢止;規定了職權而不互相溝通,那麼職權所達不到的地方一定會出現漏洞。是以制定了法令而加以讨論,規定了職權而互相溝通,沒有隐瞞的計謀,沒有遺漏的善行,就會什麼事情也不會犯錯誤,這隻有君子才能辦到。是以公平是職權的尺度,中和是處理政事的準繩。有法令規定的就依法行使,沒有法令規定的就用類推的方法處理,這是處理政事的最好方法;偏袒同黨而沒有準則,這是處理政事的邪路。是以有好的法令而發生動亂的國家是有的;有君子而國家混亂的,從古到今,卻沒有聽說過。古書上說:“國家安定産生于君子,國家混亂産生于小人。”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分均則不偏,勢齊則不一,衆齊則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争,争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譯文:名分相同就不能有所偏重,權勢相同就不能統一,衆人平等就不能互相役使。有天有地就有上下的差别,聖明的君王一開始當政,處理國事就有了一定的等級制度。兩個同樣富貴的人不能互相侍奉,兩個一樣卑賤的人不能互相役使,這是自然的道理。權勢地位相同了,喜好和厭惡也相同,财物不能滿足就互相争鬥,争鬥就會混亂,混亂就一定會窮困。先王厭惡這種混亂,是以制定禮義來區分,使人們有貧富貴賤的差别,足以全面進行統治,這是養育天下的根本。《尚書》中說:“要想齊就必須不齊。”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笃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子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馀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馀雖曲當,猶将無益也。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馀矣。”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産,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則,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箧,實府庫。筐箧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故我聚之者以亡,敵得之者以強。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譯文:馬拉車受驚,那麼君子就不能安坐在車子上;百姓被政治吓怕,那麼君子就不能安坐在他們的職位上。馬拉車受驚了,那就沒有比讓它安靜下來更好的了;百姓被政治吓怕了,那就沒有比給他們恩惠更好的了。選用賢良的人,提拔忠厚老實的人,提倡孝悌,收養孤兒寡婦,救濟貧窮的人,像這樣,那麼百姓就安于政治了。百姓安于政治,然後君子就安于職位了。古書上說:“君主,就像船;百姓,就像水。水能浮起船,水也能傾覆船。”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是以處在君位上的人要想安定沒有比政治平和、愛護人民更好的了,要想榮耀沒有比遵循禮義、尊敬士人更好的了,要想建立功名沒有比崇尚賢良任用能人更好的了,這是做好君主的重要方面。這三個方面做得恰當,那麼其馀方面沒有不恰當的了;這三個方面做得不恰當,那麼其馀方面即使做得都很恰當,也還是沒有用處。孔子說:“大方面對,小方面也對,這是上等的君主。大方面對,小方面有時對有時不對,這是中等的君主。大方面不對,小節即使對,我也不用看其他方面了。”成侯、嗣公,是聚斂錢财、精打細算的君王,沒有能夠得到民心;子産,得到民心了,但沒能處理好政事;管仲,善于處理政事,但沒有能夠實行禮義。是以實行禮義的國家就能統一天下,善理政事的國家就強大,得到民心的國家就安定,聚斂錢财的國家就滅亡。是以行王道的君主使百姓富裕,行霸道的君主使士人富裕,勉強生存的國家使大夫富裕,即将滅亡的國家富了國君的箱子,充實了府庫。箱子塞滿了,府庫充實了,而百姓貧窮了,這就叫做上面溢出下面漏空。這樣的國家對内不可以防守,對外不可以戰鬥,那麼傾覆滅亡立刻就會到了。是以我聚斂這些錢财就會滅亡,敵人得到這些錢财就會強大。聚斂錢财,是招來敵寇、養肥敵人、滅亡國家、危害自身的道路,是以聖明的君主是不走這條路的。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強奪之地。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強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者,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我鬥。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鬥。人之民日欲與我鬥,吾民日不欲為我鬥,是強者之是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雖守者益,是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是以反削也。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伺強大之間,承強大之敝,此強大之殆時也。知強大者不務強也,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強道者也。
譯文:王者争奪人心,霸者争奪盟國,強者争奪土地。争奪人心的使諸侯臣服,争奪盟國的與諸侯為友,争奪土地的與諸侯為敵。使諸侯臣服的稱王,與諸侯為友的稱霸,與諸侯為敵的危險。使用武力争奪土地的,人家的城池守得很牢固,人家的士兵拼命戰鬥,而我以武力戰勝他們,那麼傷害人家的群眾必然很厲害。傷害人家的群眾很厲害,那麼人家的群眾怨我也一定很厲害;人家的群眾怨我很厲害,就會天天想與我戰鬥。人家的城池守得很牢固,人家的士兵拼命戰鬥,那麼傷害自己的群眾也一定很厲害。傷害自己的群眾很厲害,那麼自己的群眾也一定十分怨恨我;自己的群眾十分怨恨我,就會天天不想為我戰鬥。人家的群眾天天想與我戰鬥,自己的群眾天天不想為我戰鬥,這就是強國變成弱國的原因。土地奪來了而人心失去了,負擔多了而功效少了,雖然守衛的土地增加了,而守衛土地的群眾減少了,這是大國反而削弱的原因。諸侯國沒有不心懷怨恨表面與它結交而不忘記他的敵人的,時刻窺伺強國的可乘之機,趁強國疲敝之時來攻擊,這就是強國危險的時候了。知道強大之道的君主是不追求武力的,而是考慮利用王命來保全他的力量,積累自己的德行。力量保全了那麼諸侯就不能使它衰弱了,德行積累了那麼諸侯就不能将它削弱了,如果天下沒有王者或霸主那麼他就會常常取勝了。這是知道強大之道的君主。
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廪,便備用,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然後漸慶賞以先之,嚴刑罰以糾之。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則諸侯親之矣;修友敵之道以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是以親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疏矣;是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道,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闵王毀于五國,桓公劫于魯莊,無它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而強矣。
譯文:那些行霸道的人不這樣,開辟田野,充實糧倉,改進器具,謹慎地招募、選拔武藝高強的人,然後用重賞來引導他們,用嚴刑來糾正他們,使将要滅亡的國家得以儲存,使将要斷絕的後代得以延續,保衛弱小,禁止強暴,卻沒有兼并他國的野心,那麼諸侯就會親近他;以友好平等的态度同諸侯交往,諸侯就會喜歡他。之是以親近他,是因為他不兼并别國,如果兼并的意圖顯現出來,諸侯就會疏遠他;之是以喜歡他,是因為他态度友好平等,如果臣服他國之心顯現出來,諸侯就會離開他。是以表明自己不會有兼并他國的行為,信守友好平等的原則,如果天下沒有稱王的君主,就會常常勝利了。這就是知道稱霸之道的君主。齊闵王被五國毀滅,齊桓公被魯莊公之臣劫持,沒有其他原因,就是因為沒有實行正确的道路卻想稱王天下。那些行王道的人卻不這樣,仁愛高于天下,道義高于天下,威望高于天下。仁愛高于天下,是以天下人沒有不親近他的;道義高于天下,是以天下人沒有不尊重他的;威望高于天下,天下人沒有敢與他為敵的。用無敵的威望,輔助仁義之道,是以不用戰争就可以勝利,不用進攻就可以達到目的,不動用一兵一卒天下就臣服了。這是知道稱王之道的君主。知道這三種治國之道的君主,想稱王就稱王,想稱霸就稱霸,想強大就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