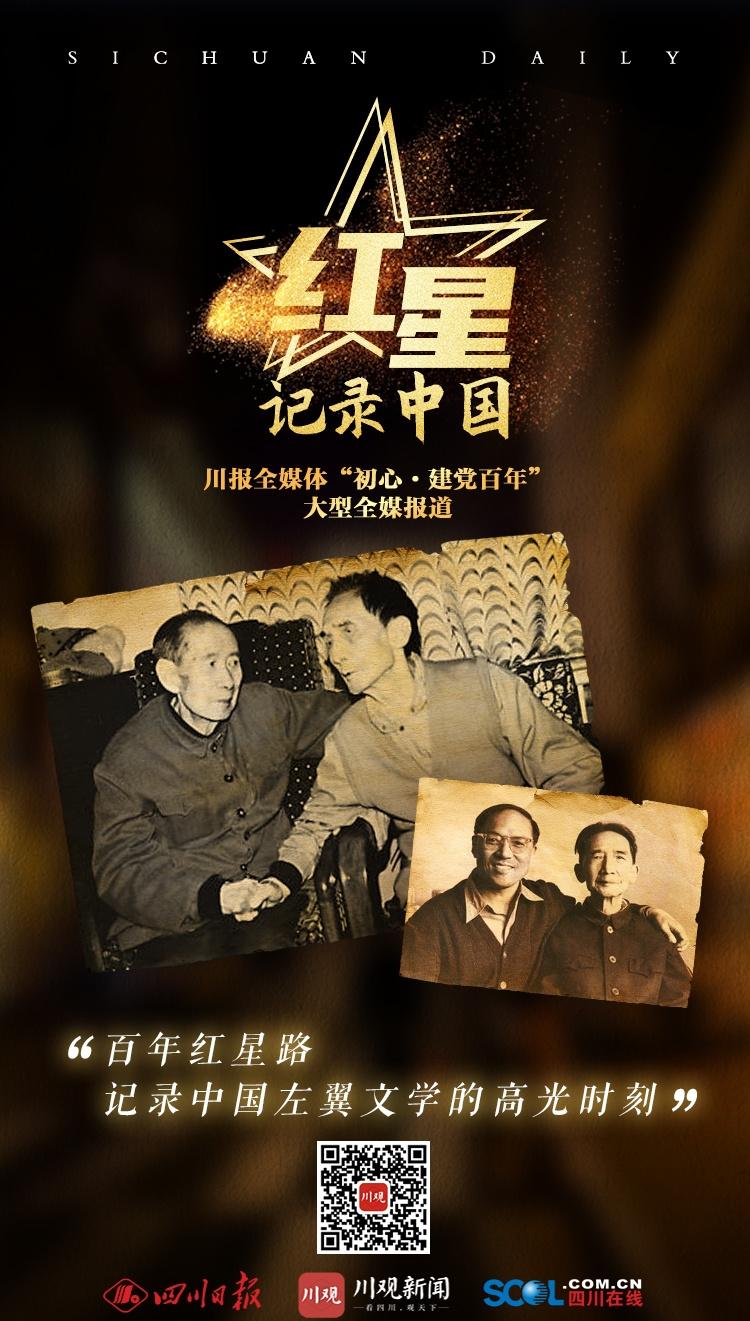
四川線上記者 肖姗姗 成博
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運動興盛,川籍作家沙汀和艾蕪先後揚名。由于創作上的互相促進、生活中的持久友誼,沙汀和艾蕪被譽為中國左翼文學的“雙子星”。加之雖未加入左翼作家聯盟、但卻用作品喚醒國人掙脫枷鎖的巴金,川籍作家在時代的轉折中,親身參與到描畫未來世界藍圖的左翼文學運動中。
新中國成立後,沙汀擔任全國和四川省文學界的上司工作,并親身參與川西文聯和西南文聯的籌建,1955年回川後又擔任四川文聯主席兼任《草地》主編。艾蕪則曆任四川省文聯臨時黨組成員、省作協籌備組組長。兩位文壇巨匠,都生于1904年,逝于1992年;他們從四川出發,享譽全國;最終又回歸故鄉,同居一座古雅小院,安度晚年。
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巴金、沙汀、艾蕪三人結下深厚友誼。他們創作上互相促進,在生活中互相照顧的事迹,深深烙印在紅星路二段新巷子十九号的宅院裡。三位作家,用他們的作品與友誼書寫了不朽的佳話,成為中國左翼文學浩瀚星空中最燦爛的星辰,至今仍閃耀在紅星路和中國當代文學史上。
“雙子星”回歸紅星路
再出手震驚文壇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1930年代興起的左翼作家創作中保持着“苦難書寫”的傳統。受到國際共産主義運動與國内社會現狀及革命思潮的深刻影響,左翼文學一開始便表明了自己鮮明的底層立場與政治态度。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段從學表示,左翼是時代的方向,是當時文人的選擇。而最終留下名字的,他列出了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蕪……段從學直言:“新中國成立後,那些沖出夔門、走向延安的青年學生,在經過戰争與革命的鍛煉後,又有相當一部分人回到了四川。”而紅星路,正是他們回歸的終點。“以省文聯的組建為契機,包括沙汀、艾蕪等左翼作家在紅星路上彙聚。”
艾蕪
當時的沙汀,不僅是紅星路上創作力旺盛和文學觀成熟的中堅力量,他還在中國作協擔任着上司工作。四川作家進京,紅星路與首都的交相呼應,彰顯着四川當時在全國的文壇地位和影響力。一邊工作,一邊創作。沙汀寫出了大批真正反映新生活,歌頌新型農民的作品,《摸魚》《盧家秀》《過渡》……回顧這段創作曆程,沙汀曾說:“一晃眼六十年過去,我寫的作品不算太多,其中也有一些自己喜愛的,如《在其香居茶館裡》《呼喚》《闖關》等等。”即使在紅星路上工作,長期限于行政工作,但沙汀的創作從未中斷,他自謙:“僅寫了二十多個短篇小說和散文報道,是以客觀上給人一種創作難以為繼的印象。”而事實上呢?沙汀筆耕不辍,陸續創作《青岡坡》《木魚山》和《紅石灘》三部中篇小說。前兩部是寫社會主義農業化的,《紅石灘》是寫土豪劣紳如何抗拒時代潮流的,沙汀回憶言:“師陀去世前還來信說他很欣賞這部小說,覺得比《淘金記》還好。”
同沙汀一樣,艾蕪的創作之路也從未停步。歌頌新生活的多篇短篇小說先後出爐,《新的家》《夜歸》……1961年到雲南舊地重遊,完成了《南行記續篇》。1981年以後,艾蕪再度深入大小涼山,重返雲南邊疆,創作短篇小說集《南行記新篇》。四川大學教授張放回憶起當年再次于《四川文藝》上看到艾蕪的《南行記續篇》時,仍然激動不已,“同學們争相傳閱,艾蕪先生又回來了!而且,這篇作品簡勁明麗、清新氣息撲面而來,裡邊的女性與流浪者的情懷,絲絲入扣。刻畫人性,惟妙惟肖!而其‘南行’詩意,無疑達到了老人一生文學追求的最高境界!”
那時,張放正在鄰近紅星路的川大求學,他一直渴求能與艾蕪見上一面。這個夢,之後在紅星路上得以圓滿,不僅見過艾蕪多次,在一次座談會上,甚至肩挨着艾蕪坐過。“紅星路二段新巷子十九号,《四川文藝》(先後更名《四川文學》《現代作家》等)二進四合院小門裡,裡進半廂是編輯部(進去左側),半廂是艾蕪先生的家(進去右側)。我們在編輯部院子亭子間開座談會,艾蕪先生就在對面家門前走廊上散步,包括做些輕微勞動,面容清癯,身着舊布中山裝,常現思考的樣子,與我們距離應該不到十來步。”後來有人招呼艾蕪來指點一下,“艾老聽到就微微一笑,擱下手中活計,抱個茶缸,笑盈盈踱步過來,在長條凳一端坐下與我們慢慢談文學,談生活。”張放感歎,艾蕪十分樸實,讷于言,不善辯,非常低調。
沙汀在小院兒凝視文壇
艾蕪跨出院門兒走出“艾蕪路線”
張放所提到的紅星路二段新巷子十九号,正是紅星路上最耐人尋味的地方。在作家雁甯的記憶中,那是一座小巧玲珑古色古香的老公館,“上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這裡曾是《四川文學》雜志社的駐地,同時還住着四川人為之驕傲的著名作家沙汀、艾蕪兩家人。在我和許多文學青年的心目中,這座時常開着白色丁香和粉紅月季,總是那麼安靜那麼祥和的小院,宛若一冊打開的線裝書卷,散發着淡淡書香,令人神往。”
彼時的沙汀,已是70多歲的老人,“這位個子不高幹瘦清癯看似沒多少精神,談起話來尤其是談起文學話題就目光炯炯的老作家,笑起來常有一種孩子般的單純和天真。沙汀一家住在小院最裡邊的幾個房間裡,他時常帶着思考的樣子,挪動輕緩的步子,慢慢走出來,路過編輯部都要用目光給我們幾個年輕人打招呼。”曾擔任過四川作協主席的沙汀,那時已是中國作協創委會負責人了,不但關注全國的文學創作,對四川新人新作也十分關心,作家周克芹和女作家包川,提起沙汀就心懷敬意由衷感謝。雁甯回憶,晚年的沙汀對四川作家的創作非常關注,當時周克芹發表了長篇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每每來找沙汀聊天,談到激動處,沙汀都會禁不住手舞足蹈,又突然靜止下來眼睛微閉仰向天空久久不動,如一尊雕像。
同在紅星路這座小院兒的,還有艾蕪。在這裡安度晚年的一代文豪,将這條路寫進了日記,寫進了生命。除了小說創作,艾蕪還始終堅持寫日記。從四川文藝出版社推出的《艾蕪全集》中可見,寫日記是艾蕪數十年如一日的必修課,基本上每天動筆,内容包含每日見聞、所思所想、文事文稿、旅行遊曆、起居飲食、書信來往、親友走動、書賬等,還有采訪筆錄、讀書劄記等等,單篇最長的達數千字。這些日記從未被披露,仔細翻來,逐年逐月逐日穿越在先生的生命時态中,細察一代漂泊文豪天南海北的行走、江湖廟堂的舉止、待人行事的斟酌、居家過日子的雞毛蒜皮……實在是一種極為特殊的閱讀體驗。而也是在這些字裡行間,艾蕪與紅星路的漫時光,彌足珍貴——晚年居成都,艾蕪天天散步,形成了一條“艾蕪路線”,自紅星路二段的新巷子19号出發,“從猛追灣一直沿着新修的大馬路走,轉彎到水碾河,向西而走,直到紅星路,然後回家。”邊走邊看街頭風景,順便買豆腐、蔬菜、面包之類。忽然想起一些故事,便提前趕回家記下……
學者張效民著有《艾蕪傳》,他第一次見到艾蕪,也是在紅星路上的新巷子十九号小院兒。“1981年1月10日,我和一位同學在紅星路的新巷子十九号院子敲響了艾蕪老人的門。開門的是一位高高瘦瘦的和藹老人,正是艾老。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艾蕪這位名聲遠播的老作家,這是一位非常平易、安詳、睿智的老人。”
巴金執着的遙望
成就紅星路最真摯的念想
1992年,沙汀和艾蕪相繼去世。紅星路上最悲恸的友人,他的名字,叫巴金。不得不說,他們三人之間的神仙情誼,不僅成就了三人在文壇上的成就,更讓紅星路上的文心熠熠生輝。據了解,在為人處世中,沙汀都是自覺将巴金的言行作為參照,他崇敬巴金、欣賞巴金,直接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近幾個月來,我倒的确有很多改變,不大肯同人争論了,也不愛提意見了。而且,對于從前可能吵起來、跳起來的一些事情,我也能夠像老巴那樣,說一句:‘沒關系!’或者:‘不要緊’就拉倒了。”不僅是為人處世影響了沙汀,巴金還慧眼識珠,出版了很多沙汀的優秀作品。巴金欣賞沙汀,沙汀的小說集《土餅》《航線》《苦難》《淘金記》《還鄉記》都是經巴金之手出版的。巴金甚至給沙汀寫信,直言:“望你常來信,有什麼新作品,不要忘記寄給我一本,我喜歡你寫的東西。”除了文學上的惺惺相惜,巴金對沙汀的物質和精神方面也十分關愛。他為沙汀催促版稅,緩解生活窘境;沙汀夫人患病,巴金來信安慰,并郵寄來相關珍貴藥品,當沙汀希望能夠求購日本的一種新藥“絲裂黴素”時,巴金立刻遍找日本友人相助,委托他們将藥空運到上海,再寄給身在四川的沙汀。
于艾蕪而言,巴金是朋友,更是伯樂。1935年,巴金所在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為艾蕪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南行記》,艾蕪是以一舉成名。巴金與艾蕪也就開始了交往幾十年的友誼。第二年,巴金着手編艾蕪的短篇小說集《逃荒》,還專門為這本集子寫了《後記》。此後的幾十年間,巴金與艾蕪分居兩地,相聚的機會不多,但彼此的心是相通的。1950年代初期,艾蕪深入鞍鋼體驗生活,創作了長篇小說《百煉成鋼》。出于與巴金的友誼,他将這部小說交給巴金主編的《收獲》首發。1980年4月,由巴金擔任團長的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日本,艾蕪作為代表團的成員,在出訪期間,他們有機會相處了兩周的時間。對于這對老朋友來說是極為珍貴的一段時間,為他們的友誼史冊更增加了難忘的一頁。
1980年以後,從沙汀家裡、從紅星路上寄出去的信,直接給巴金的少了。沙汀把信寫給了巴金弟弟李濟生,但在每封信中問候巴金。兩人若在北京的作協大會上有幸碰頭,那必然是相談甚歡,聊至深夜。1987年,巴金專門從上海傳回成都,不參加任何會議和座談,也不接受記者采訪,隻見老朋友。于是,巴金、張秀熟、艾蕪、沙汀、馬識途,“蜀中五老”喜相聚。那一次,巴金還特意到艾蕪的老家新都去賞了桂花。
1992年12月,艾蕪去世。巴金立即讓女兒給四川發了唁電,這是艾蕪家屬收到的第一份唁電;沙汀聞訊後,第一時間發話,提到了自己,提到了艾蕪,提到了巴金。“你怎麼忍心松開我們握了大半個世紀的手,先我而去呢?你,我,巴金三人同庚,我們曾經約定,明年在成都共慶九十生日,可你卻等不及了,這叫我怎麼不倍感痛苦和悲傷呢!”同月,沙汀也去世了。
兩人的相繼離世,讓巴金悲痛不已。1992年12月18日,巴金曾給自己的侄兒李緻寫信,他說:“這個月我心情不好,艾蕪、沙汀相繼逝世,尤其是沙汀的突然死亡,使我十分難過,他還能寫,也準備寫不少作品,就這樣離開人世,太可惜了!你不在成都,他們的最後時刻,我也無法知道。”
那之後,巴金再也不能遙望紅星路,因為這路上已經不再有他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