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裡,獨自彷徨在街頭,無所依歸的孩子們”。
這是白先勇在自己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孽子》中的開篇之語。《孽子》描寫的是一個獨特的群體,一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生活在台北市前路新公園中的同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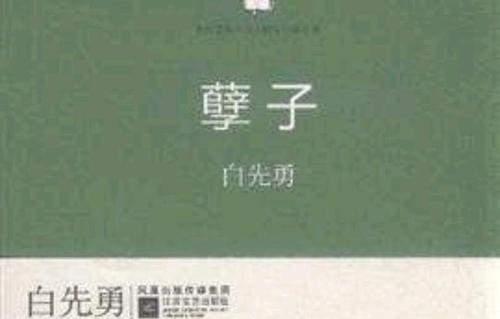
白先勇可謂是出身名門,他的父親是大名鼎鼎的“小諸葛”白崇禧,乃民國時期最頂尖的桂系軍閥領袖之一。
隻是即便自己的父親位高權重,但出生在戰亂年代的白先勇依然承受了戰争所帶來的流亡之苦,他多次跟随家人輾轉搬家,似乎一生都是在漂泊之中度過......
如此豐富的人生閱曆,再加上後來又親曆了父親的逝去和家道中落,使得白先勇對社會、對人生有了更深層次的感悟,他用文字慢慢記錄下自己内心中的所思所想,成長為了一位著名的旅美作家。
白先勇創作的《孽子》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第一部以同志為題材的小說。會選擇觸碰這樣的題材,白先勇無疑是既大膽而又感性的。
當然也隻有他本身是這一群體的一員,才能深刻描寫這一群體的心理和生活狀況。那他到底經曆過什麼?對于兒子特殊的取向,他的父親白崇禧是否是知曉的?父親又是對此持一種怎樣的态度呢?
一、早年的孤寂生活
“七七事變”的幾天之後,也就是1937年7月11日,白先勇出生。
對于這個兒子的出生,白崇禧并沒有太多的激動,畢竟在此之前他已經有七個孩子了。白先勇在家中排行第八,自幼體質就不太好。
父親的教育對于孩子的成長是至關重要的,但在白先勇小時候,白崇禧由于身居要職,軍務纏身,常常不能顧及到家人,是以對白先勇來說,父親這個角色常常是缺位的。
不過,白崇禧對子女的要求卻非常嚴格,白先勇曾提到父親白崇禧在家中逼孩子們讀書是從不松手的,而他的哥哥、姐姐們在後來回憶起父親在飯桌上考校算術時也仍然是心有餘悸。
白先勇出生在桂林白公館,在七歲之前,他都生活在桂林,這也是他童年時代難得快樂的一段時光。這段時期的美好在他後來的作品中有所展現,而這種家庭情懷也是白先勇内心中最為真實的寫照。
1983年,白先勇在美國寫了散文《第六隻手》,在文中回憶了自己小時候的桂林生活,那是他在得重病之前在家鄉桂林的最後一年的時光,對于家鄉的鐵佛寺、風洞山和東鎮路等都記憶猶新。
多年以後,白先勇重回故鄉,還能用一口道地的桂林話對前來接他的人道謝說:“辛苦你們了”,引得衆人紛紛感慨他鄉音未改,實屬難得。
2012年,白先勇在回國接受記者采訪時還說道:“桂林的确是山水甲天下,這種山清水秀在全世界都是沒有的。我回去的心情也悲歡交集,悲的是自己的父母都已故去,物是人非,另外又會覺得江山依舊,還是那麼美,這是一個叫人欣慰的地方。”
然而,美好時光猶如白駒過隙,快樂的日子也總是短暫的。當年随着戰争的不斷蔓延,長沙和桂林等地相繼淪陷,白先勇一家不得不跟随白崇禧從桂林搬到了重慶。
白崇禧雖然經常不着家,但就像我們前文有提到過那樣,他特别重視子女的教育,每一次從前線打電話回來都一定會詢問孩子們的成績,孩子們在家中的地位甚至都是以他們學習成績的優劣來決定的。
當時在重慶安穩下來後,到了讀書年紀的白先勇被安排到西溫泉國小讀書,這在當時是一所非常不錯的學校。白先勇曾回憶說:“父親雖然是軍人出身,但極為重視教育,每到一個地方,都會想辦法把我們送到最好的學校去念書。”
而白先勇自己從小也很熱衷于讀書,喜歡聽各式各樣的老故事。不過令人感到有些許意外的是,他的文學啟蒙卻是家中的一位廚子。
他在《蓦然回首》中便提到過此事:家中的廚子老央是桂林人,做過火頭軍,又能說會道,還有一些見聞,也喜歡講故事,他給白先勇講的第一個故事就是《薛仁貴征東》。
後來接受采訪時,白先勇也說過一嘴:“老央可以做一流的說書人了,他講的故事很傳神,講到我都不願意睡覺,他對我也有影響,稱得上是我文學的啟蒙老師。”
實際上,白先勇正是在這樣一種孤寂、落寞的時代背景下喜歡上老央故事的,而這對他後來的人生經曆也有一定的影響。
為何這樣說呢?原因在于重慶上學後不久,白先勇便被查出了肺結核二期,這個病在當時幾乎算是“不治之症”,俗稱肺痨,極具傳染性。
為了治病,同時也為避免将病情傳染給家中其他人,白先勇被隔離在山坡上一棟小房子裡,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毫無疑問,這種生活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創傷,有時候他甚至感覺自己像是一個被遺棄的孩子。
很多時候,白崇禧在家中宴客之際,屋裡都是燈火通明,賓朋滿座,但熱鬧都是屬于旁人,與他無關。他站在山坡上看着不遠處喧鬧的場景,還是一個孩子的白先勇不禁落淚大哭。
童年對一個人的塑造是深遠持久的,是以這樣的經曆也使得白先勇自幼便形成了一種多疑、敏感、又缺少安全感的性格,他在孤寂的氛圍中化悲痛為想象力,将自己的思想和情緒都傾注到文字裡,而這或許就是他以後在取向上與常人不同的内因所在。
在那段最為孤寂的日子裡,老央的陪伴和故事講述成了他最大的慰藉,也成為了他的一種習慣。是以當病愈之後,白先勇便如饑似渴地投入到學習讀書中去,不但将每門功課都學好,還抽時間閱讀了大量書籍。
二、影響一生的相遇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白先勇的人生注定會與父親的政治生涯緊密相連,而當國民政府在大陸潰敗之際,白先勇也跟随家人再一次地颠沛流離。
白先勇先是來到了香港,不久之後,他的母親帶着一部分孩子前往台北與父親白崇禧彙合,還有一些孩子則去了美國念書,隻是白先勇繼續留在了香港。直到1952年,白先勇才從香港去往台北與父母團聚。
白先勇功課很優異,在台北依然能考入當地最好的建國中學。十七歲時,還在建國中學上高二的白先勇為了能夠考上一個好大學報名了一個補習班。
在一次上課期間,他因為快要遲到而一路狂奔,卻不小心與另外一個名叫王國詳的同學撞在了一起,而這一撞便是驚天的緣分。
“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這句詩雖然描寫的是愛情的美好,但對于超越了傳統愛情的白先勇來說,這樣的意外相逢更具有故事性。
正所謂不打不相識,兩個青年逐漸成為了最要好的朋友。在《樹猶如此——紀念亡友王國祥君》一文中,白先勇說到兩人一開始就有一種異姓手足,禍福同當的默契。
鳳凰衛視的花旦許戈輝曾主持了一檔訪談節目《名人面對面》,對話了十五位台灣文化界名人,其中就有白先勇。
許戈輝說:“您懷念一生自有王國祥的文章令人非常感動,你們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八年,我一直在想那是一種怎樣的情感。我也在文章中讀到了你們相遇的情形,是一個充滿了童趣的過程,兩個人都恰好遲到了,就這樣相遇了。”
白先勇沉默了片刻後回答說:“是以啊,我後來越來越覺得緣分是一個非常神奇的事情,人與人的相遇完全是憑着緣分。不然為什麼天下那麼大,有那麼多的人,而兩個人還會相遇、相識,還會成為最好的朋友呢?或許冥冥中有一種命運的力量。”
白先勇與王國祥在成為好朋友後,越走越近,兩人甚至還商量好了考同一所大學。
其實白先勇當時本來有機會保送台灣大學的,但因為有一個水利夢,還想日後能去長江三峽修大壩,就申請了保送成功大學的水利系。
而王國祥則非常支援摯友白先勇的決定,也轉而考上了成功大學。他本身就是高材生,考台灣大學沒有問題,但還是去了成功大學的機電系。
兩人進入大學後就在學校附近租房住了下來,過了一年比較惬意自由的大學生活。但随着課程和學業的深入,白先勇發現自己的興趣已經不在水利方面了,學習起來非常吃力,就果斷選擇退學,又重新考了台灣大學外文系。
但沒想到的是,此時王國祥也覺得所學的專業不合自己胃口,他認為自己不擅長工程,同時這也不是他的愛好所在,真正想學的是理論科學。
有了白先勇的鼓勵,王國祥也邁出了轉校的這一步。他報考了台灣大學的轉學考試,想轉到該校的實體系去。
要知道在那個年代,别說轉校了,就是在校内轉系都是非常難的一件事,而王國祥是又要轉校,還要轉學院加轉專業,簡直是難如登天。但他确實是在學業上過于優秀,竟然考上了,而且也隻錄取了他一個人,可見此事當時有多艱難。
白先勇和王國祥兩人先是一同考了同一所大學,後來又都因為不滿意所學的專業,重新做了一次選擇,又都考取了自己喜歡的專業,還都在同一個學校,這又是一種怎樣的緣分呢?
白先勇後來寫了《孽子》這本書,1977年剛發表時與當時時代是格格不入的,因為這本講述的是一群特殊性取向的台灣年輕人悲歡離合的故事。是以,這本書一開始并不被主流關注,而是被沉寂,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才慢慢多了一些評論和注意。
而之是以會寫這樣一本書,本就是因為白先勇自己也是一個有特殊戀情和特殊取向的人。對于白先勇來說,這種特殊取向的愛也是他生命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
王國祥始終在他的生命裡,即使後來病故,離開他很久了,但這段感情似乎還是沒有結束。
三、陪伴與懷念
當時就在二人都慶幸自己考中了心儀的專業,以及二人又能夠去同一所大學讀書之時,厄運卻悄悄降臨了——王國祥患上了極為罕見的血液病。
白先勇在采訪中對許戈輝說道:“王國祥在大學時期得了血液病,那一次幸運地通過中藥治好了。”
那一次得病的一年多時間裡,王國祥用西醫方法治療,病情沒有任何起色,還幾乎耗光了家中積蓄,處境十分艱難。
好在他的一個親戚聽說江南名醫奚複一大夫醫治好了一個情況比他還要糟糕的南韓僑生,才重新燃起了希望,最終痊愈,不需要依靠輸血了。
然而,當兩人後來都來到美國學習、生活後,王國祥的病情卻在二十年後又複發了,而且這一次更加兇險,一直不叫好轉,最終其不幸因病去世。
雖然悲劇是在美國發生的,但白先勇和王國祥在美國的絕大部分日子都是很幸福的,在這裡兩人也有着一段美好的回憶。
當時他們到了美國後,很快就安頓了下來。1973年,白先勇搬到了“隐谷”,那時候他在加州大學的芭芭拉分校擔任教師,看中了一處房子,但房子裡的常春藤等一些植物都不是他喜歡的,于是他決定對其進行改造。
這種改造工程是非常費時費力的,他一個人有些勉為其難,好在王國祥在暑假時過來給他幫忙,二人合力改造了房子。
當時的王國祥正在賓夕法尼亞州州立大學做博士後,隻有一個半月的假期,但兩人卻齊心協力,足足做了三十天的園藝工作。
後來,兩人還買了三株意大利柏樹的幼苗,一起在院中種了下去。王國祥當時還說這三棵樹長大後一定會超過園子裡的其他樹,後來這三棵樹果然長得格外好,俨然成了白先勇園子裡的地标。
在後來的日子裡,王國祥曾輾轉換了好幾份工作,還去過加拿大和德州。後來他放棄了實體學,轉行到了高科技産業,但不管怎麼忙,隻要一有假期,王國祥都會到白先勇的芭芭拉家中小住上一段日子。
而每一次去芭芭拉後,王國祥第一件事就是看他們當年一起種的植物,那三棵樹已經十分茁壯了,尤其是中間那一棵樹,比兩邊的都還要高上許多。
或許樹也是有“靈性”的。
1989年,白先勇發現中間的那棵意大利柏樹葉子開始變得焦黃,沒過幾天,這棵樹就像被雷擊了一樣通體枝焦而亡。奇怪的是,這三棵樹隻有中間這一棵樹死亡了,旁邊兩棵倒是長勢依然良好。
柏樹無故死亡令白先勇很傷感,而同時他也有一些不好的預感,果然沒過多久就收到了王國祥再度重病的消息。
王國祥給白先勇打電話說自己舊病複發,是再生不良性貧血,雖然多年前王國祥曾憑借中醫治好了此病,但這一次卻沒有了之前的幸運。
在患病的那段日子裡,白先勇一直陪伴在他身邊,一次次開車帶他去醫院看病,陪他在醫院與病魔做鬥争。為了給他治病,白先勇還跑了很多地方,從美國到台灣,再從台灣到大陸,尋找各種可能的治病方法。
在人生中最後的時光裡,白先勇顯然也成為了王國祥最後的依靠和慰藉。
盡管病魔可怕,但兩人還是想盡一切辦法樂觀的生活,他們在可以被允許的範圍内吃美食、看電影、甚至還買了桂花種在王國祥家中院子裡,細心照料。
1992年1月,白先勇陪王國祥過完了他生命裡的最後一個生日,當年夏天,王國祥病逝,在他生命的最後一程,白先勇一直緊緊的握着他的手......
從上文我們不難看出,二人的感情是彌足真摯的,無論外人到底是如何評價,至少他們兩人相濡以沫過了如此長的歲月,足以令人感動。
四、父親白崇禧的态度
隻是對于兒子白先勇這樣的複雜情感與特殊取向,父親白崇禧是否知道?還有他對此又是持什麼樣的态度?
在很多人看來,白崇禧這樣戎馬一生的國民黨官僚軍閥,在對待子女上肯定猶如處理軍事決策那般跋扈專斷,但實際上他在對待孩子方面卻并不像外人認為的那般。
白先勇曾說過,父親喜歡看自己寫的書,對于自己的特殊取向是知道的,但并沒有粗暴的幹涉,也沒有覺得這樣的兒子給他帶來了恥辱,而是非常了解,也非常尊重兒子的選擇。
其實這對于一個從傳統和戰亂年代走出來的身居高位者來說,實屬不易。
白先勇曾寫過一篇叫《月夢》的文章,在文中他第一次提到了自己特殊取向的感情,白崇禧認真翻看過兒子的文章,自然也是了解孩子在這方面的與他人的不同之處,畢竟文章往往反映的就是作者的個人思想。
難能可貴的是,白崇禧并沒有是以暴跳如雷,甚至也沒有主動與兒子提過此事,父子之間有一種彼此盡在不言中的默契,雖然不言語,但雙方卻都心知肚明。
而這種沉默和溫和的相處方式,也令白先勇非常感動。
或許對于白崇禧而言,他縱橫疆場數十年,一生經曆了無數大場面,見證了太多的悲歡離合與人生無常,也就看淡了許多。
兒孫自有兒孫福,隻要孩子過得幸福,能夠以自己的能力實作人生的價值,除此之外又何必有過多的強求呢?
其實這一點在白先勇當年退學重考大學上也有展現,白崇禧是希望兒子能夠學理,不願意他學文,盡管白先勇忤逆了父親,重新聯考并換了專業,但白崇禧也沒有粗暴的阻止兒子,等到後來看到兒子寫出了一篇篇優秀的文章後,他也就釋然了。
孩子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路,可以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并有所收獲,這不就是身為家長最期望看見的嗎?
在《孽子》這篇小說中,白先勇刻畫了因為父親不了解兒子的特殊取向,導緻兒子自殺或者因為被父親逐出家門,而流浪美國的角色,這種悲劇角色與他們父親的不了解和強硬幹涉有莫大的關系。
與小說中的人物比起來,白先勇無疑是極其幸運的,因為他遇到的是一個相對開明,也能夠了解自己的父親,這是何其的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