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巴掌、打屁股、擰耳朵、打手心……這些看了就讓人感覺火辣辣地疼的詞,在許多家庭裡卻是家長用來管教孩子的方式。除了肢體暴力之外,還有許多孩子在家裡承受着語言暴力和情感上的“冷暴力”。創傷性的童年經曆會對人産生長久的影響,以至于“有的人要用一生來治愈童年”。
事實上,《未成年人保護》《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法規都明确規定禁止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暴力。2021年《家庭教育促進法》出台時,網友們也紛紛感慨“家長終于要‘持證上崗’了”。
然而,法律和現實之間仍有很大的差距。很多人認為,管教孩子是家務事,家長有權決定怎麼管教自己的孩子。是以,雖然一些惡性的虐待兒童案件已經引起了社會的關注,但在“棍棒之下出孝子”“打是親罵是愛”的文化規範下,非暴力的教養方式仍然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可。
“上次是用木棍打我,把棍子都給打折了。”
一項發表于2015年的研究估計,中國0-17歲兒童中,遭受肢體虐待的發生率為26.6%、情感虐待的發生率為19.6%、性虐待的發生率為8.7%、忽視的發生率為26.0%。[1]目前,大陸仍然沒有關于針對兒童的暴力事件的全國性統計資料。
2014年,救助兒童會提出了“消滅針對兒童的體罰和羞辱”這一全球行動。同時,我們啟動了“正向教養”項目,聚焦于家庭中對兒童的體罰和羞辱。
為了解中國家庭中打罵兒童的現狀和原因,我們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的童小軍副教授合作,進行了文獻回顧和訪談。在對初、高中生的訪談中,許多學生都能回想起在家中被暴力管教的經曆,其中既有肢體暴力,也有語言和情感暴力:
“國小之前還是國小那一陣,我媽老是打我,打屁股或者用手拍後背……有按在那兒打過。”
“上次是用木棍打我,把棍子都給打折了。”
“爸爸就讓我在櫃子那裡罰站,站了一下午。”
“用晾衣竿打。”
“我爸到院子裡把遊戲機放在地上,用我的手握着錘子把遊戲機砸碎了。”
“我爸就會先選擇不說話。他就在那坐着,也不讓我走,就讓我在那呆着,他也什麼都不說。”
“(媽媽)對我會冷眼相待,寡言少語,沒句話,就是不帶任何感情的感覺。”
“我幹什麼事笨了,比如找東西找不到,她帶着我去找,找到了就會罵我,說我笨,‘這麼簡單還用教嗎?’”
雖然學生們對這些經曆記憶猶新,但他們往往不認為這是兒童虐待,反而會用“爸爸媽媽都是為了我好”來解釋父母的行為。這使我們意識到,在打和罵的話題上,父母和孩子的體驗都是沖突的,在理論上很容易定性為“正确/錯誤”“好/壞”的問題,從情感和關系上,卻是很複雜的。
在調研的基礎上,我們引入了救助兒童會(瑞典)與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瓊恩·E·杜朗特博士共同開發的《正面管教》家長課程手冊,綜合參考國内外的其他書籍和教材,嘗試開發适合中國國情的家庭教育教育訓練教材。
這個時候,我們将“正向教養”定義為“專注于養育者雙方平等及共同的參與,積極為孩子創造一個沒有身體和情感傷害、尊重他們權利的教養環境,繼而培育親子之間親密而鞏固的關系,并實作兒童潛力的最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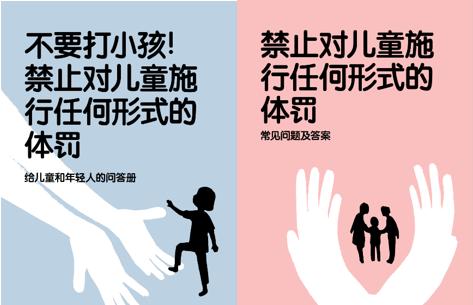
救助兒童會開發的兩本禁止針對兒童的體罰的手冊,分别面向兒童和家長
家長為什麼會打孩子?
從2015年開始,我們在廣州、眉山、昆明、烏魯木齊等城市,和社會組織合作,面向家長開展正向教養學習小組。在小組中,我們接觸到了形形色色的家長,也了解到他們在家庭中遇到的各種挑戰。
有媽媽說,她的丈夫常常用打的方式來教育一歲多的孩子,在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到被衣架打過的痕迹。有一次,她看到孩子也拿着晾衣架在抽打一個凳子。
有爸爸說,他希望能學到一些直接、有效的方法,讓孩子乖乖聽話。
有媽媽說,自己從小被家長打罵,婚後又常被丈夫責罵,自己難受時,常通過兩個孩子洩憤,有次甚至把孩子打得都進了醫院。
在和來自不同地區、文化、階層、職業、受教育水準的家長交流的過程中,我看到了暴力管教的代際傳遞——很多家長是在打罵中長大的,當他們為人父母的時候,就認為打罵是一種有效的管教方式,以此來教育自己的孩子。
同時,我們也看到了許多“被困住”了的家長:家長很愛孩子,卻在教育的過程中打罵了孩子。冷靜下來後,她/他會充滿愧疚,決心下次要改變。但是,當沖突再次發生的時候,又會忍不住使用暴力。這樣的循環不斷侵蝕着家長的信心,内疚、無力和自我懷疑不斷地告訴她/他:你不是一個好家長。
是以,在正向教養的家長小組活動中,我們并不先和家長讨論他們的孩子,而是讨論家長自身。
在一開始,我們會邀請家長分享他們的家庭夢想——我希望成為什麼樣的家長?我希望孩子、鄰居/朋友怎麼評價我?在家庭教育方面,誰是我的榜樣,他/她是怎麼做到的?
進而,我們引導家長看到維持生計、教養孩子等等給她/他帶來的壓力,以及壓力産生的影響——什麼事情會讓我感到有壓力?在有壓力的時候,我的身體有什麼反應,我的情緒有什麼變化?處于壓力下時,我容易對别人說什麼或做什麼?有壓力時,孩子的什麼行為會讓我容易爆發?在壓力情境下,我對待男孩和女孩的方式有不同嗎?男性和女性在壓力下對待孩子的方式有差別嗎?
在我看來,一個人要照顧好孩子、家人,前提是要先照顧好自己。我們并不是劈頭蓋臉地怪罪家長“你打孩子是錯的”,而是幫助家長有意識地觀察自己的壓力值、情緒變化,學會自我照顧,尋找适合自己的纾解壓力的方法。很多家長告訴我們,當自己成為了情緒的主人,而不是被情緒所左右時,她/他能夠更心平氣和地和孩子交流,很少會無意識或控制不住就打罵孩子了。
正向教養導師互相練習非暴力的溝通方式
我們不告訴家長“怎麼教孩子才是對的”
雖然很多家長都說希望在教養孩子上得到指導,但在項目開展過程中,招募家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時間有限之外,家長對于“學習”的緊張是更主要的阻礙。
在我們的成長經曆中,學習通常被認為是一件“苦事”——老師會在課堂上指出學生的錯誤,學習之後要考試,不允許抄襲,考得不好還要被批評。是以,說到要學習家庭教育的方法,很多家長會自然而然地産生畏難情緒,害怕自己學不好、做錯了。
事實上,和正常的教育不同,家庭教育沒有标準答案,而是基于經驗不斷發展的。相比于告訴家長“怎麼教孩子才是正确的”,我們更願意和家長一起發現和總結“我用過哪些好的經驗和方法”,并鼓勵大家互相參考,模仿别人用過的有效的、非暴力的教育兒童的方式方法。
在我們看來,不隻是孩子,家長也需要被肯定和鼓勵。當家長看到自己的高光時刻的時候,她/他會變得更加自信,更願意去學習别人的成功經驗,更有動力去嘗試新的方法;遇到挫折的時候,也更容易走出來,與人讨論,總結經驗,繼續嘗試。
這便形成了對于“賦能”的新的了解——不隻是賦予技術和方法,更需要賦予使用技術和方法的信心。基于新的了解,我們在2019年更新了“正向教養”的定義,更強調鼓勵和認可,提高家長的信心和能力,使家長願意控制打罵孩子的行為,嘗試非暴力的教養方式。
很多家長會說:“學了正向教養之後,我知道不能打孩子,但情緒上來的時候,還是控制不住自己就下手了。”這時候,我們會肯定家長的自我覺察和檢討,引導他們允許自己的失敗,接納自己的焦慮,重建立立起和孩子之間的信任關系,慢慢地将非暴力變為一種習慣,實作“國際不打小孩日”所提倡的“請來試試看,至少在今天不要打小孩,或許你将會發現,今天過後的每一天,你都不需要打小孩了”。我們也相信,家長坦誠地面對挫折,在尊重的基礎上和孩子進行溝通,也會進一步影響孩子,使孩子從中學會尊重和自立,同時使親子關系更加親密而穩定。
李東是正向教養家長導師,也是仁壽縣心時代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技術顧問。在一個家長小組上,一位父親和李東說,今天的課程讓他有了改變對孩子的教育方法、和孩子改善關系的想法,請李東幫忙出主意。李東對他的想法表示了贊賞,并請他回家後,就過去給孩子帶來的傷害向孩子真誠道地歉。這位父親問:“道歉有用嗎?”李東說:“試試吧,慢慢來,不急。”
當天晚上12點左右,這位父親激動地給李東打電話,說他給孩子道了歉,孩子回到房間大哭了一場,等了一陣才出來。他給孩子遞了一盒牛奶,孩子看了看父親,用拳頭捶了他一下,然後緊緊地抱住了父親。在這位父親的記憶中,這是孩子懂事以來,他們倆的第一次擁抱。
家長在正向教養小組活動上進行小組讨論
眉山有一群草根媽媽
從2015年到2021年,救助兒童會和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合作,在四川、雲南和貴州等西部地區的農村和鄉鎮開展了400多場家庭保護服務活動,40,000多名家長和兒童受益。六年裡,我們培養了200多名正向教養家長導師、兒童引導師,他們将持續在鄉村開展家庭保護服務活動。
在四川省眉山市仁壽縣,有一群媽媽通過正向教養服務,成為了家喻戶曉的“草根媽媽”。
王佳秋是仁壽縣文缜國小的一名國小老師。2014年,她參加了救助兒童會在仁壽舉辦的正向教養家長導師教育訓練。有一天,在陪孩子玩的時候,她想到可以把幾個家庭聚在一起,孩子們一起玩,家長們互相交流育兒的方法。于是,她問孩子:“你在班上有沒有玩得好的小朋友呀?我們可以邀請他們家一起玩。”
最初聚在一起的5個家庭,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大多是全職媽媽、單親媽媽、爺爺奶奶、外公外婆。2016年下半年,家庭數量增長到了10個,王佳秋就建了個微信群,買了投影和其他裝置,每個星期天下午在自家客廳裡組織親子活動。
随着家長們的互相介紹,群裡的人數在半年内就增長到了500人。于是,王佳秋和幾位夥伴一起成立了“草根媽媽成長教育協會”,定期組織周四親子朗讀、周五草根媽媽講故事、周日親子玩等等活動,開始和婦聯、民政部門進行長期合作。
每周五的草根媽媽講故事,是微信群裡最熱鬧的時候。參加過正向教養小組的媽媽會分享自己學到了什麼;有些媽媽沒有學過正向教養,就分享自己帶孩子的故事;也有媽媽會講講自己和孩子之間的問題,向群友們尋求意見。
一開始,有的媽媽、外婆、奶奶因為國語有四川口音,不敢發語音說話,擔心在幾百個人的群裡,自己說得不好。王佳秋就不斷安慰她們:“沒關系,這個群裡大家互相尊重,講話和分享是安全的。你要是擔心,可以先聽聽别人是怎麼分享的,再說說你想說的。”
草根媽媽協會的志願者會把群裡的故事整理成文章,發在微信公衆号上。對于很多媽媽來說,自己的分享被寫成文章,既能給孩子起到榜樣作用,也能讓孩子看到自己在親子關系上的用心。
作為志願者之一的張海蘭是一位單親媽媽,2017年,她帶着2歲的女兒從成都回到仁壽。在新環境裡,她想給自己和孩子找到新的朋友,就開始參加草根媽媽協會的活動。
張海蘭說,她以前脾氣比較暴躁,一個人又要上班又要帶孩子,壓力很大。女兒隻要一調皮、不聽話,她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常常打、罵女兒,也覺得這是很正常的教養方式。
參加了5節正向教養小組活動後,張海蘭意識到自己應該轉變對待孩子的态度和方法。從那以後,每當孩子發脾氣時,她會先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女兒為什麼生氣?是不是因為有什麼需要沒有被滿足,有什麼我沒有了解到的?”接着,張海蘭會再引導女兒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在雙方彼此了解的基礎上進行溝通。
慢慢地,張海蘭開始和其他家長分享正向教養給自己和女兒帶來的變化,吸引他們參加草根媽媽協會的活動,而她自己也從參與者轉變成了志願者。“我和草根媽媽團隊一起組織過很多線下活動,縣裡頭好多家長、孩子都參加過我們的活動。有時候我出去逛街、買菜,都可能遇到認識我的家長和孩子,他們離得很遠就跟我打招呼,我就覺得很開心,很自豪。”在一次訪談裡,張海蘭和我們分享了她作為志願者的成就感。
現在,正向教養的活動、草根媽媽們的故事都在仁壽縣的官方宣傳平台“大美仁壽”上得到了長期推廣。草根媽媽和孩子共讀故事的聲音,也通過仁壽縣人民廣播電台,傳遍了整個仁壽。
草根媽媽們在一起交流教養孩子的經驗
外來務工家長如何更好地和孩子“在一起”?
在西部鄉村開展正向教養服務的時候,我們接觸到了許多留守兒童,他們雖然很少被打罵,卻普遍缺少家長的陪伴和支援。在談論到家庭教育時,外出務工的家長也隻能很無奈地說:“我怎麼教她/他啊,我一年就回家一兩次。”
雖然大多數家長都會盡可能多地和孩子打電話、視訊,但因為不懂得如何溝通,隻能問一問“最近成績怎麼樣”、“吃的好不好”,久而久之,孩子也不願意和家長聊心裡話。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後,由于封城、交通管控等疫情防控措施,家長更難返鄉,和孩子也就見得更少了。
除了留守兒童之外,還有一部分孩子跟父母一起搬到了城市。根據教育部的統計資料,2020年義務教育階段随遷子女人數達到了1429.7萬人[2],占流動人口子女的52.58%[3]。
新冠疫情也同樣給這些家庭帶來了更大的挑戰。疫情使得外來務工的家長面臨更大的經濟壓力,精神壓力增加,打罵孩子的可能性也是以提高。居家隔離時,家長和孩子不得不在有限的空間裡長期相處,更有可能産生沖突和沖突。而在風險增加的情況下,社群對于家庭暴力的識别和幹預能力卻反而減弱。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20年,大陸有約2.86億農民工,其中有配偶的占79.9%[4]。是以,在2022年,我們從農村轉移到城市,進入以流動人口為主的“城中村”,并嘗試和雇傭了大量外來務勞工員的企業合作,使正向教養服務進入到流動人口家庭中。
我們希望提高外來務工家長對親子關系的重視程度,鼓勵他們在努力賺錢養家以外,也關注家人之間的情感聯系。事實上,許多家長并非故意不重視親子關系,而是受限于“時間貧困”——每天的工作時間長,少有時間好好地陪伴孩子,更難以抽出時間學習家庭教育的方法。
是以,我們重新梳理正向教養的核心資訊點,結合外來務工家長在家庭教育上最感興趣的話題,設計成1.5小時的線上、線下講座,開發短視訊等學習材料,以期覆寫盡可能多的外來務工家長,為他們提供基礎、有效的知識和技巧,并吸引其中一部分家長參加更長周期的工作坊。對于工作坊,我們也設定了6小時、12小時、20小時三種不同時長的課程,探索最适合外來務工家長的學習模式。
如果家長一周隻有一天,或是一天隻有一小時能夠和孩子相處、給孩子打電話,那麼,在短短的時間裡,給孩子提供高品質的陪伴,或許正是流動人口家庭所需要的。
家長和孩子共同參加正向教養親子活動
引用文獻:
[1]
XFang,DAFry,KJi,DFinkelhor,JChen,&PLannen等.(2015).Theburdenofchildmaltreatmentinchina:asystematicreview.BulletinoftheWorldHealthOrganization.
作者和機構簡介:
馮浩殷,救助兒童會家庭保護項目經理。從2007年開始,緻力于倡導家庭中的兒童權利與兒童保護。目前是救助兒童會正向教養家長教育核心導師,也是救助兒童會(瑞典)正面紀律認證導師。過去8年間,他帶領團隊開發了一系列正向教養、兒童權利、健康教育相關的教育訓練課程,并與政府部門、社會組織等合作,在廣東、四川、雲南、新疆等地開展了430多場家庭保護服務活動,服務了43,000多名家長和兒童。
救助兒童會是全球領先的、獨立的兒童慈善組織,1919年成立于英國。20世紀80年代起,救助兒童會進入中國,開始在安徽、雲南、西藏開展項目。2017年,依據《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内活動管理法》,注冊成為境外非政府組織代表機構——國際救助兒童會(英國)北京代表處,依法在中國境内開展兒童福利和保護、救災、教育、健康、兒童權益等項目。目前已在中國12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實施項目。我們的願景是所有兒童都能享有生存、健康、受教育、被保護以及參與世界的權利。
(郭悅萍對本文亦有貢獻)
馮浩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