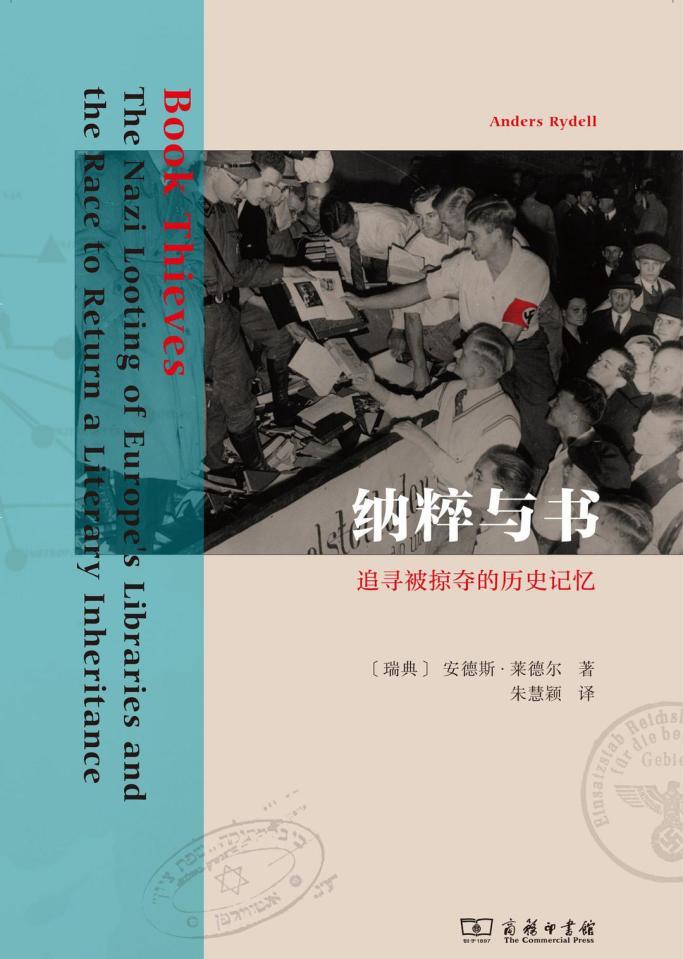
《納粹與書:追尋被掠奪的曆史記憶》,[瑞典]安德斯·萊德爾著,朱慧穎譯,商務印書館,2021年8月版,328頁,66.00元
與我以前讀過的以納粹與書為主題的著作相比,瑞典記者、非虛構作家安德斯·萊德爾(Anders Rydell)的《納粹與書:追尋被掠奪的曆史記憶》(原書名 The Book Thieves: The Nazi Looting of Europe's Libraries and the Race to Return a Literary Inheritance,2015;朱慧穎譯,商務印書館,2021年8月)有兩個新的叙事視角,一是關注納粹帝國在歐洲掠奪圖書的目的、過程和細節,以及戰後仍然存在的同樣屬于劫掠圖書的行為以及歸還原主之難的問題;二是分析納粹黨人對圖書的重視與使用,從納粹帝國對圖書的有目的的劫掠和使用中揭露納粹法西斯的邪惡本質。該書原書名直譯是“偷書賊:納粹對歐洲圖書館的掠奪和歸還圖書遺産的經過”,很直白地講述了該書的主要内容。2018年的台版譯作“偷書賊:建構統治者神話的文化洗劫與記憶消滅》(王約譯,馬可孛羅文化出版);而現在商務版這個書名沒有把“偷書”直譯出來,“納粹與書”似乎更能概括全書的核心内容。但是兩個中譯本的副标題離原書副标題所要表達的書的内容有點遠了,或許譯者是更希望把叙事内容中的深層含義表述出來。
上述兩個叙事視角均可延伸和挖掘出納粹帝國史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議題,比如從圖書的命運看二戰前後歐洲的圖書史、閱讀史、精神文化史,以及納粹帝國的興起與文化暴行又是如何改變和摧毀了這幅文化版圖;從納粹黨人對所劫掠圖書的使用,更是與研究納粹帝國的意識形态、教育、學術有的直接聯系,是研究納粹政治中的知識生産與思想戰争的重要議題。在納粹史研究中這些議題并不新,但是從劫掠圖書的角度切入可能就不多了。雖然“納粹與書”這個主題隻是納粹帝國史研究中的小題目,但是深入挖掘進去,還是可以發現不少新問題值得研究。從這個角度來看這部面向公衆的普及讀物,我覺得有其重要的學術價值。
全書開頭和結尾講的是同一件事。作者于2015年前往伯明翰,背包裡放着一本橄榄綠封面的小書。在穿越了七十多年的時光之後,這本書将回到它曾經的主人理查德·科布拉克(Richard Kobrak)的孫女埃爾斯手裡。扉頁上貼着藏書票,書名頁寫着科布拉克的名字。1944年底,科布拉克和妻子一起被送上開往奧斯維辛的列車,然後被趕進毒氣室。理查德·科布拉克唯一留存在世上的東西就是這本小書。封面隐約燙金凸印着一幅圖案:一把鐮刀放在一束小麥的前面,書名是《法律、國家與社會》(Recht,Staat und Gesellschaft),作者是保守派政治家格奧爾格·馮·赫特林(Georg von Hertling)。作者知道這本書在今天并不特别值錢,在柏林的舊書店裡,它的售價很可能也就幾歐元;但是更知道它價抵萬金,因為它對于其主人的後代太寶貴、太重要了。另外,它是還在等待被整理、等待被尋找前主人的數百萬本書籍中的一本。大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它們被人忘卻,或被那些知道它們來曆的人撕掉有标記的書頁,劃去個人贈言,僞造圖書館目錄,在目錄裡把蓋世太保或納粹黨贈送的“禮物”寫成來自匿名捐贈人。
這是一段悲傷的圖書聚散史,更令人悲傷的是原圖書主人的悲慘命運,例如這本小書的主人理查德·科布拉克。他的孫女埃爾斯告訴作者,身為公務員的祖父因為是猶太後裔而受納粹迫害,雖然一向睿智并關心政治消息,但是在緻命的套索慢慢收緊的時候還以為希特勒的統治不會長久——作者說,這很适用于當時選擇留在德國的人。最後醒悟過來,想盡辦法把子女送出國之後,自己已經走不了了。這本小書無疑是在家庭被納粹洗劫的時候一起搶走的,後來輾轉流到柏林圖書館,在這個圖書館有幾十萬冊這樣書。
作者寫這本書的起因是從關注納粹黨人盜竊、劫掠歐洲藝術品開始的。這種行為以及戰後的歸還過程在過去幾十年來一直備受關注,作者也在2013年出版了《掠奪者——納粹黨人如何盜取歐洲藝術瑰寶》。在這過程中他發現除了藝術品之外還有圖書,但是後者很容易被遺忘。原因很簡單,既是因為原來在博物館和藏家手裡的那些藝術品的價格、藝術市場的運作和媒體的興趣,同時也由于要整理出那幾百萬冊被掠奪而來的圖書的來源以及尋找原主人是何等艱巨的事情,簡直讓人望而生畏。
對于納粹來說,掠奪藝術品與掠奪書籍有什麼差別?前者主要分給了阿道夫·希特勒和赫爾曼·戈林等納粹上司人,他們打算用藝術品展示所統治的世界是美好的,也是因為貪婪;後者的重要性卻是為意識形态上的思想戰争服務,目的是要從思想上戰勝并毀滅“帝國敵人”,建構德意志帝國的正當性與光榮的、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神話。被掠奪的圖書主人很多是意識形态上的敵人——猶太人、共産主義者、共濟會、天主教徒、政權的批評者、斯拉夫人等,掠奪行為主要在納粹黨衛隊上司人海因裡希·希姆萊和納粹黨首席理論家阿爾弗雷德·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的上司下進行。在納粹上台執政後,一場有組織、有目的的掠奪圖書行動随着納粹在國内的反猶暴行以及對外的兼并、侵略行動而在歐洲各國發生,從大西洋岸到黑海邊,自阿姆斯特丹、巴黎、羅馬、塞薩洛尼基到維爾紐斯,從公共圖書館到私人住宅的藏書均遭受了最嚴重的劫難。由于整個過程延續時間長,涉及國家、機構、團體和個人的情況複雜,圖書的毀滅、流散和最終下落的真相直到今天難以弄清,對很大一部分罪行的認定也懸而未決。
萊德爾循着圖書搶劫者的蹤迹,穿越歐洲數千英裡,尋訪各地的圖書館、檔案館等機構和知情人,目的是了解和重制這段被遺忘的文化的劫難史。“我從散落在巴黎的流亡者圖書館輾轉到羅馬,查找可上溯至世紀之初、而今已不複存在的古老的猶太人圖書館。然後,我在海牙探尋共濟會的秘密,複至塞薩洛尼基尋找一個被滅絕的文明的碎片。我還從阿姆斯特丹的西班牙系猶太人圖書館,來到維爾紐斯的猶太人圖書館。在這些地方,人們和他們的書籍被拆散,有時被摧毀:痕迹無處不在,雖然往往僅剩一鱗半爪。”(序言)除了揭示這段曆史真相之外,作者記錄了那些至今仍在為整理和歸還那些圖書而努力的機構與個人,同時也表達了愛書人的共同心聲:“哪怕是一本書,也需歸還給那些已失去太多的書籍擁有者。”(《芝加哥論壇報》)更重要的是他提醒讀者,納粹獨裁者對圖書的劫掠歸根到底是要消滅人們關于曆史與文化的真實記憶。“撰寫本書時,我意識到這些記憶才是核心,它們正是書籍被劫掠的原因。搶走人們的文字和記述,是囚禁他們的一種方式。”(同上)
那麼,“說吧,記憶!”(納博科夫)雖然許多記憶一旦說出來,人們或許會發現原來太陽底下沒什麼新鮮事。
1933年5月10日晚上發生在柏林劇院廣場的納粹焚書事件成為現代史上滅絕文化的最強烈的象征和隐喻,在無數的納粹帝國研究著述中都會提到這一事件。也有不少研究者圍繞焚書事件發表了專題著述,如記者于爾根·澤爾克的《焚燒的詩人》(Die verbrannten Dichter,1977)、文學批評家、傳記作家福爾克爾·魏德曼的《焚書之書》(宋淑明譯,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等。萊德爾在書中一方面談到了發生在焚書事件前後的事情,另一方面更強調焚書這個象征性事件往往遮蔽和模糊了人們對納粹與圖書關系的認識。
1933年之前,納粹黨人對思想文化活動和作家、知識分子的迫害已經開始。“經過選擇,一些作家成為沖鋒隊巡邏員的監視對象,這些人守在他們家門外,他們走到哪兒,這些人就跟到哪兒。”(第2頁)《民族觀察報》發表了有四十二名德國教授簽名支援的宣言,宣稱德國文學要防範“文化布爾什維主義”,後來又公布了一份準備等納粹上台後就查禁的作家黑名單。1933年2月,興登堡總統簽署了“保護人民和國家”法令,限制出版自由。德國大學生聯合會發起了5月10日的焚書活動,但是早在1922年就發生過幾百名學生在柏林的滕珀爾霍夫機場燒書的行為。學生們先清理自己個人的藏書,後來延伸到公共圖書館和當地的書店,許多時候是大學教務長、教師和與學生合作清理學校圖書館。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經濟大蕭條和通貨膨脹使買得起書的德國人越來越少,傳統的圖書館無法滿足人們的需要,于是在德國出現了一萬五千多家小型外借圖書館。這些圖書館大量購買暢銷書,提供了價格低廉的借閱服務,即使在今天看來這也是令人驚訝的。但這些“人民圖書館”更容易落入學生之手。(5頁)大概有100萬冊屬于這些圖書館的圖書被掠奪。
在1932年,許多猶太人和共産主義者就開始處理個人藏書,銷毀照片、通訊簿、信件和日記。人們在自家的火爐、壁爐或後院燒書,這樣的例子有成千上萬起;後來許多人為了節省時間和怕麻煩,幹脆把藏書丢到樹林、河流或者行人絕迹的大街上,也有人匿名把書郵寄到子虛烏有的地方。(第6頁)但是,許多有名的德國知識分子對焚書行為的認識卻令人痛心,他們竟然會“相信焚書表達了春天的革命熱情,新政權遲早會從這類事情中‘成長’”。(11頁)
在另一面,“即便是納粹黨人也認識到,如果有什麼比僅僅摧毀文字更有力量,那便是擁有并控制它”。(序言)1930年代中期,納粹控制的讀書俱樂部“古騰堡讀書會”(Buchergilde Gutenberg) 有三十三萬三千名會員,納粹政權能夠高效地把從歌德、席勒到國家主義者、納粹分子的作品傳遞給了數百萬讀者。“激發了德國曆史上空前的、想必也是絕後的文學和政治熱情,它每年頒發的文學獎項超過了55個。”(第8頁)在1930年代,德國每年有大約兩萬部新作問世,納粹宣傳部認為“對人民有教育意義”的書用大開本大量出版。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僅1933年就印了八十五萬冊,在納粹帝國期間總共出售了六百多萬冊。(第9頁)不過這也不奇怪,以前新婚夫婦會收到《聖經》作為禮物,在納粹上台後會收到的可能就是《我的奮鬥》。
在五月的廣場上焚毀了數萬冊圖書,但是有更多的書被送到了沖鋒隊總部。作者認為,“确切地說,納粹既非人們認為的‘文化野蠻人’,也不是反智主義者。相反,他們試圖創造一種新的知識分子,這種知識分子所安身立命的不是自由主義或人道主義的價值觀,而是他的國家與種族。納粹黨人并不反對教授、研究人員、作家和圖書管理者,而是想吸收他們,組成一支由思想和意識形态戰線的鬥士構成的軍隊,用他們的筆、思想和著作向德國和國家社會主義的敵人宣戰”。于是,書籍也成了納粹黨的武器,他們要“用敵人自己的藏書、檔案、曆史、遺産和記憶對付他們。要奪取書寫他們曆史的權利,正是這個觀念釀成了世界曆史上規模最大的竊書慘劇”。(13頁)萊德爾對此有一段總結說得很到位:“納粹黨發動了兩種戰争:第一種是用正常手段,由軍隊在軍事沖突中與敵人對決;第二種是針對意識形态敵對力量的戰争。……打意識形态之戰不僅僅靠使用恐怖手段,因為它也是關于思想、記憶與觀念的戰争,一場捍衛國家社會主義世界觀并将其合法化的戰争。”(94-95頁)在這場戰争中,圖書就是極為重要的武器。
巴伐利亞國家圖書館擁有一批獨一無二的藏品,因為納粹最早偷竊的一些圖書就藏在這裡,因為這是在國家社會主義的誕生地慕尼黑。萊德爾這裡看到有一本書上蓋着“政治圖書館,巴伐利亞州政治警察”的印章,他感到看到了納粹掠奪圖書的源頭,“我們可以把這些書視為掠書計劃的考古遺迹,該計劃涵蓋了研究機構、精英學校和秘密警察組織的意識形态戰争。……這些印章代表着納粹政權最早的企圖,即企圖制訂思想方案,擷取知識。這個方案提出,不僅要研究敵人,而且要在第三帝國建設以意識形态為基礎的全新的文化研究和教育。……這種做法的基礎是極權主義意識形态,它想要全方位控制公民的生活。同樣的極權主義思維也應用于科學,試圖重新定義每一個科學領域。所有的一切都必須是國家社會主義的……。”(56頁)
但是應該承認納粹黨人對于管理和使用圖書是很重視、很認真的。萊德爾注意到,一部關于土著兒童保健的人類學研究著作中也有巴伐利亞政治警察的印章,“它表明安全警察的野心不僅僅局限于研究共産黨人和具有颠覆性的政治集團。事實上,政治警察是第三帝國内部貫徹極權主義哲學最為賣力的組織的早期組成部分,這一組織名為黨衛隊,簡稱SS”。(57頁)納粹上台以來,各聯邦的秘密警察和保安處就一直緊緊盯着圖書市場的各個環節,從文學批評、圖書館、圖書出版、圖書進口,到逮捕和騷擾作者、書商、編輯和出版商,一切都在監督審查之下。1936年在柏林正式成立了“異類政治文獻研究圖書館”,希姆萊下令德國所有的秘密警察部門查閱被沒收書籍的清單都要立即将有關材料送往這裡,同年5月圖書館的藏書已經達到五六十萬冊。(60頁) 這個圖書館在1939年納粹黨安全機構大改組中并入中央安全局第二處,不久後又移交給第七處,一個緻力于“意識形态研究與評估”的研究部門。這是納粹黨内部最進階别的圖書館,反映了希姆萊和黨衛隊的世界觀。萊德爾說這裡最令人好奇的藏書是神秘學圖書,說明了神秘主義是黨衛隊的嚴肅主題。在中央安全局成立之前,黨衛隊就有“神秘學圖書館”和專門研究部門,甚至還把一些猶太學者綁架到這裡來工作。作者指出,帝國中央安全局進行的研究不單是為了研究敵人以便更有效地擊敗他們,也是為了将這些知識灌注到黨衛隊的思想和知識發展中。“黨衛隊發動的是針對猶太智識主義、現代主義、人文主義、民主、啟蒙運動、基督教價值觀和世界主義的戰争,但是打這場戰争靠的不僅僅是逮捕、處決和集中營。……極權主義意識形态不僅想控制人民,而且試圖控制他們的思想。……在希姆萊的圖書館的陰影下,我們仍應當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極權主義政權對知識的破壞和它對知識的渴求到底哪一個更可怕?”(63頁)
問題來自納粹當權前後的形勢變化。在納粹運動中原來包含有許多不同的思想傾向,不同力量和群體經常試圖把納粹黨帶向不同的政治方向。“維系這場亂糟糟的政治運動的不變核心是希特勒本人以及在他身上成形的上司原則,即所謂的‘元首原則’——盲目、絕對地服從元首一一正是納粹意識形态最重要的柱石。”(67頁)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新成員源源不斷地加入納粹黨,如何統一思想、純潔隊伍是更為明顯的新的挑戰。為此,希特勒讓羅森堡負責納粹黨的精神與意識形态發展和教育,在柏林成立了一個統稱為“羅森堡處”的機構。羅森堡認為要轉變人的思想,最重要的工具是教育體制,從1933年開始逐漸從幼稚園到大學推行學校體系的納粹化。這種改革得到學校師生的大力支援,因為納粹黨長期以來重視在教師中開展工作,早在1929年就成立了納粹教師聯合會(NSLB) 。是以教科書要重寫,科目要更改,教師也要像軍人一樣向元首宣誓效忠。學校最重要的思想教育書籍除了《我的奮鬥》就是羅森堡的《二十世紀的神話》,學校課程裡增加了如“種族衛生”這樣的新科目。羅森堡還命人編寫了一本名為《意識形态的主題》的手冊,勾畫出納粹世界觀的主要基礎,在全國的學校使用。“這樣做的目的,如羅森堡所言,是讓納粹意識形态滲透到從曆史到數學的每-門課程。”另外,在這個納粹教育體系中,“不僅老師要監視學生,而且學生也監視老師,學生可以向希特勒青年團或蓋世太保舉報發表‘非德國的’言論的老師”。(80頁)1937年,希特勒準許成立由羅森堡負責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勞工黨高等學校”,因為培養未來納粹上司的教育不能交給傳統的學校體系,羅森堡希望這個“國家社會主義最重要的研究、教育與教學中心”能成為這所意識形态大教堂的基石。(83頁)
納粹對圖書的掠奪往往有很明确的目的和針對性。1940年6月,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國際社會史研究所(IISG)成為納粹在荷蘭掠奪圖書的第一個犧牲品,因為荷蘭經濟史教授尼古拉斯·波斯特姆斯(Nicolaas Wilhelmus Posthumus)在1935年創辦該所的目的就是反對當時肆虐歐洲的法西斯主義。1930年代,大量來自蘇聯、德國、意大利的難民湧入西歐,也帶來了許多有價值的文獻、書籍,波斯特姆斯極力收藏那些涉及社會主義、工會、勞工運動的書籍和文獻,為它們建立一個安全的港灣,因為納粹和蘇聯人都在無情地追蹤這些書籍。于是這裡收藏了包括《共産黨宣言》的手稿在内的馬克思與恩格斯檔案,總共有五個多書架的材料、筆記、手稿和二人無所不談的通信。這些檔案在1933被德國社會民主黨偷偷運出納粹帝國,在經濟困難之中隻能把它們賣掉。當時最熱切的、準備出最高價的買家是莫斯科的蘇共中央馬恩列研究院,但是社會民主黨認為賣給斯大林很丢人,于是被波斯特姆斯買了下來。這位經濟史教授真是神通廣大,他的藏品中還有無政府主義者巴枯甯和俄國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檔案,他設立在巴黎的分部還收藏了托洛茨基的兒子捐贈的托洛茨基檔案,蘇聯格勒烏(DRU)特工還從這裡偷走了很多托洛茨基的檔案。現在,納粹的羅森堡特别任務小組來了,圖書館的書籍和其他檔案全部運回德國,但是馬恩的檔案卻被波斯特姆斯搶先運到了他的牛津分部。
納粹在德國和歐洲各地對圖書的掠奪是有多個部門參與的,互相間也激烈的競争關系,從圖書這個視角也可以反映出納粹帝國内部的組織結構及其權力鬥争。在掠奪圖書活動中最大的兩個競争對手就是羅森堡特别任務小組與黨衛隊和帝國中央安全局第七處,為了取得包攬掠奪和配置設定某個圖書館的權力而進行惡鬥。一般來說黨衛隊擁有強大的兵力與警力,明顯占據上風;羅森堡的組織雖然沒有自己的軍隊,但他通過廣結戰略聯盟,最重要的是與戈林結盟,也纾解了這種不平衡。為了避免競争陷入無政府狀态,納粹也不得不用規章制度加以控制。是以黨衛隊與“羅森堡處”也會在圖書配置設定上達成妥協,凡是有助于保安處和蓋世太保對付國家敵人的材料歸希姆萊,而對意識形态研究有價值的圖書和檔案歸羅森堡。不過在現實中的事情永遠不會如此簡單。(97-98頁)
最後回到這些被掠奪來的圖書的歸還之難。
當年的普魯士國家圖書館(現名柏林國家圖書館)收藏了很多的納粹掠奪圖書。2006年有一位學生在其碩士論文中指出該館有近兩萬冊盜取的圖書,這段曆史才曝光。當年這家圖書館還承擔了負責配置設定納粹從各地掠奪來的圖書的任務,從掠奪到配置設定還有更多組織、機構和政府部門競相染指,戰争結束時又被蘇軍來圖書館洗劫過,據估計該館有兩百萬冊圖書被運到蘇聯。1960年代東德因為經濟原因又把大量書籍賣給西穗,這些書又被分給西德的大學圖書館。(28頁)現在要追查這些圖書的流散情況恐怕太困難了。
在柏林中央與地方圖書館,有一本賬簿在2005年被發現,上面登記了約兩千冊書,被證明是戰時劫掠而來的藏書中的一部分。更讓人驚訝的是賬簿上最後一本書的編目時間是1945年4月20日,這一天蘇軍炮火猛烈轟炸柏林市中心,部隊開始攻進城,這時居然還有一位圖書管理者坐在地下室為搶來的圖書作編目。2010年該館開始系統地調查其藏書,最難的是找到它們的主人或後人,以便歸還。2012年他們開發了一個搜尋資料庫,把被掠圖書的資訊、簽名和圖書主人留下的标記圖像都輸入進去,“讓那些後人來找我們”。這個方法有效果,目前這個資料庫共有一萬五千冊圖書,但是從2009-2014年隻有五百本左右的書物歸原主,而該館可能有二十五萬本搶來的圖書。除了柏林中央與地方圖書館,在德國的幾千家圖書館中大約隻有二十家在積極地核查藏書。(24頁)
在那些圖書扉頁上被撕去的藏書票、被塗抹掉的原主人簽名等印記,是無數被抹去、被竊取、被湮沒的曆史記憶。作者在全書最後以埃爾斯姑母的一句話作為結尾:“明天是複活節,我們能做的就是——永不放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