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讀書推薦
BENQIDUSHUTUIJIAN
《教育的情調》十二
愛滿滿 / 樂嘟嘟
為父母和教師而作,
助您成為“機智”的教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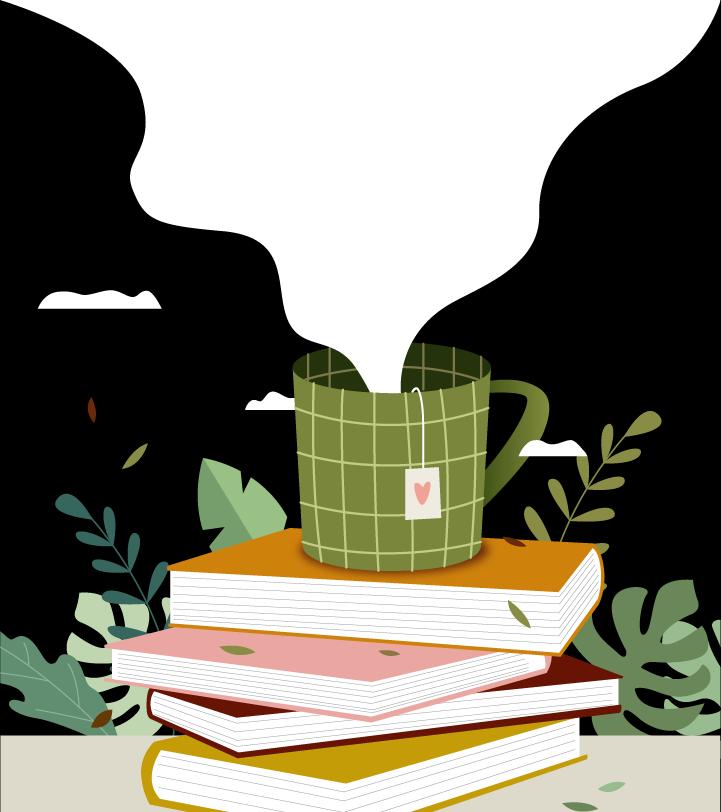
十二
孩子教會我們
心懷希望和保持開放
希望不是那種被動的、認為事情終歸會得到解決的樂觀主義。希望包含承諾和努力。即使在最荒謬、最痛苦的時候,我們也不會,也絕對不會放棄我們的孩子。
珍妮說:
大人們常常讓我們覺得人類沒有希望了。而我的看法也時好時壞。每當想到世上有那麼多的問題,比如環境惡化、宗教沖突、種族戰争、不治之症、能源不足、幹淨的水和空氣短缺,我就感到很失望。老師們甚至也認為他們過去的生活是現代年輕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他們說,“這将由你們自己決定,你們是決定人類命運的一代人”,帶着懷疑和不滿。可是,他們自己卻虛度光陰,什麼也沒有去做就感到沒希望了。……這真是世上最難的事。我經常會有和許多朋友一樣的感覺:世界末日到了。但是你知道嗎,你不能總是那麼悲觀。我時常有這種感覺,但整體而言,我還是覺得未來充滿了希望。我希望擁有好生活、好家庭、好子女,但在你的父母也不鼓勵你、不給你希望的時候,你就很難對前景一直抱有希望了。
基姆說:
有時候我覺得特别失望,好像沒有任何必要去學校上課,因為人類正在毀滅地球。我對上一輩人非常憤恨,他們留下了一個亂糟糟的世界。他們的生活即将結束,而我們的生活才剛剛開始。……我還想活下去,我想在年輕的時候體驗美好的人生。一想到生态垃圾、環境污染、森林破壞、生物絕迹,還有世界上人給人造成的痛苦,我就感到非常傷心。這些都是我們年輕人不得不承擔的可怕的責任。上一輩将這一切都丢給了我們,我們該怎麼辦呢?
海倫說:
還有一年我就畢業了,對于畢業後的去向問題我還沒有明确的想法。我的父母離婚了。我希望有一種安全感——有一個屬于我自己的地方和一些好朋友。上大學看來是沒有希望了,我能幹些什麼呢?有時我很擔心這些事情,也會和朋友們聊聊。有的人并不在乎這些。有的人甚至自甘堕落。有的人感覺和我一樣。
我們能對這些年輕人說些什麼呢?他們談到恐懼、破壞和災難。有時,那是他們體驗這個時代的方式。聽他們傾訴的時候,總會看到或聽到我們的失敗。他們說我們讓他們感到極端恐懼和浪費生命。更糟糕的是,他們指責我們把一大堆的責任推卸到了他們身上。
還有一個問題得提出來:我們是否有權力讓孩子們承擔原本該由我們自己承擔的責任?作為教育者,為了孩子們和這個世界,我們必須以身作則,傳播希望和信心。我們這些和孩子們生活在一起的人不能做一個虛無主義者,我們不能放棄我們在孩子生命中的教育地位。孩子是未來的希望。
一個沒有希望的世界是沒有孩子的生存空間的。但是隻要你的生活中、你的家中、你的教室中有孩子存在,你就應該看一看,好好地看一看,用教育學的眼光看一看。你看到的是希望。看到你的孩子,你的生活将充滿希望。和孩子們生活在一起,那些年輕的父母立刻就有了一種信念:這個世界應該——不,是必須——繼續存在下去。既然是一個孩子的父親,我就不能夠回避那些威脅整個世界的瘋狂行為。我把孩子看成生活的希望。我必須做到最好。希望在不斷地激勵着我。
其實,希望從一開始就存在,在第一次胎動時就存在了。然而,父母有時候會産生一種複雜而迷惑的期盼心理,最早和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對希望的體驗,這種體驗在這樣的想法裡變得具體起來,比如:我希望這個孩子很健康。不誇張地說,一個懷孕的女人和希望生活在一起。
教育的希望使得父母或老師和孩子們在一起的生活充滿了活力:它告訴成年人如何在這個世界上生活得更有意義,如何向孩子們描繪這個世界,如何對這個世界負起責任,如何用知識把這個世界展示、解釋給孩子們,讓孩子們了解關于這個世界的一切。對孩子們而言,那些對未來充滿希望的人才是真正的父親、母親和老師。失敗時,我們放棄了所應承擔的責任或拒絕展現與希望為伴的生活。我們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将使年輕人變得玩世不恭,使成年人失去希望、不承擔義務、不示範應該如何生活。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對這種情況深有了解,在其作品《鐵皮鼓》(The Tin Drum)中,奧斯卡拒絕長大,因為他認為沒有必要長大。
希望不是那種被動的、認為事情終歸會得到解決的樂觀主義。希望包含承諾和努力。即使在最荒謬、最痛苦的時候,我們也不會,也絕對不會放棄我們的孩子。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我們的生活中可能會發生許多的錯誤。然而在感覺無望的時候,恰恰是脆弱的孩子又一次讓我們體驗到了希望。多麼具有諷刺意味啊!
作為父母或老師,我們必須對孩子懷有期待和希望。但是“希望”隻是一個詞,詞是會被濫用、曲解,變得膚淺、空洞的。是以我們一定要看看和孩子們一起生活是如何被體驗為希望的,以及我們的行為本身是如何成為希望的。希望充滿了活力,它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和孩子們在一起。這不在于我們說什麼或做什麼,首先應該是讓希望出現在孩子們中間。
我們可以用“我希望……”來表述某些具體的期待和願望:“我希望你在學校裡表現好”,“我希望他能自己做作業”,或者“我希望她跟得上”。這些希望可以随着時間的變遷而更換。但是事實上,正是孩子使成年人超越了自我,使他們敢說:“我希望……”“我與希望同在。”“我的生活就是把孩子當作希望。”這種對希望的體驗将教育生活與非教育生活差別開來。從教育學意義上說,這也使我們更清醒地認識到,我們隻能對我們真正愛着的孩子抱有希望。希望給了我們一個堅定的信念:“我永遠不會放棄你。你會過得很好。”希望就是我們為了孩子而變得更有耐心、更有信心、更加寬容,希望就是去體驗孩子成長的無數種可能性。孩子讓我們懂得,不管經曆了多少失望,都要好好生活。這就是我們的信念。是以,是希望教會我們去教育。又或者,是教育教會我們心懷希望?
讓我們來看看“知識生産”“項目推廣”“成果導向的教育”“目标管理”這些新鮮話語。現在,工業化模式、電腦技術、資訊處理和市場思維已經大舉入侵校園。教育理論家和行政官員不時地引用它們來闡述教育實踐活動。我們該如何了解這些描繪教學的時髦話語呢?
我在這些話語中發現了一個很複雜的沖突。一方面,這些話語的運用鼓勵老師改變他們的教學活動,另一方面,他們又沒有實實在在地被“希望”所鼓舞。這樣的話語都是為了一個所謂的将來而“創造”的語言,而不是現在的、關乎我們此時此刻的生活的語言。它不允許将我們與孩子們在一起的生活等同于我們帶着希望和孩子們在一起。成果、推廣、評估、投入、消費信心是抽象的“希望類”話語,而真正的希望本身已經被有意識地抛棄了。因而它們是沒有希望的“希望類”話語,是浮躁的話語,是不能讓人覺醒的話語。
“有具體可衡量的目标”不同于“有希望”。當然,老師需要用期望、目的和目标來衡量進步或成長。但是,他們也必須非常信任和看重教與學的非技術性方面的神奇力量。期望很容易退化為欲望、企圖和預測。因而老師可能會放棄隐約可見的期望之外的可能性而裹足不前。而有希望就是相信這種可能性。希望使人集中力量去努力創造。
問題不是諸如“項目推廣”“目标管理”或“成果導向的教育”這些新鮮的課程話語有什麼錯誤。如果用得恰當,這些話語也許對行政管理工作有用。老師總是在安排、計劃課程和課堂。問題在于,“行政管理的”和“技術的”話語已經如此廣泛地深入我們的生活之中,這很容易讓父母和老師忽略另一種了解方式:首先要明白“生育”孩子和對孩子“懷有希望”意味着什麼,然後再去照顧和教導孩子。我們作為父母、老師應該經常反思這一點。
“要是能回到年輕時,同時又像現在這樣懂得這麼多就好了。”許多人很懷念孩童時代,但他們不是想再做一次孩子,而是想以孩子的方式來體驗這個世界。我們渴望找回孩提時候的那種認為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對任何事情都抱着一種開放心态的感覺,以及那種認為萬事皆有可能的自信。
孩子們知道,他們不可能做出電影中超人那樣的業績。但是,他們在玩耍時卻能體驗到這種可能性。年輕時,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希望的出現就是給父母和老師的回報,這就是孩子教給我們的。隻要我們是真正合格的父母或老師,孩子就一定能教會我們心懷希望。
我們了解孩子的方式很好地表明了我們了解自身的方式。當我們能夠體驗自己的開放性的時候,我們也就能對孩子們的生存方式保持開放性。孩子需要生活的開放性,以便形成自己獨特的個性。父母或老師需要開放性,以便成為自己并反思那些促使現在的自我得以形成的因素。
我們必須當着孩子的面公開檢討自己,經常問自己:“我們應該怎樣活着?”這樣,孩子們習慣了這種方式之後,也就能自由地問他們自己這樣的問題。做一個負責任的成年人,就是始終對人應該怎樣活着這個問題保持開放。“這是不是我最喜歡的生活方式?”這樣,我們的生活就一直是孩子的榜樣。不管我們是否喜歡,生活都會告訴我們:“人就應該這麼活着。”
我對孩子的責任感促使我不斷地行動,不斷地以這樣一種方式來展示自我和引導自我:要讓孩子能從我的身上看到一個成熟成年人的形象。
這就是我們必須向孩子學習的方面。我們一定要做一個更好的學習者,因為孩子們也在向我們學習。
待續
讀書使人進步
DUSHU SHIREN JINBU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