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沒有哪位哲學家像尼采那樣受到廣泛的閱讀,也幾乎沒有哪位哲學家像尼采那樣受到普遍的誤解。當美國著名分析哲學家、藝術批評家阿瑟·丹托的經典尼采研究在1965年首次出版時,許多人将尼采視為一位才華橫溢卻又難以捉摸的思想家。然而,丹托呈現了一幅極為不同的畫像,他認為,尼采提供了一種系統而又融貫的哲學,這種哲學超前思考了衆多界定當代哲學的問題。
尼采有時在言談中将他的哲學稱為虛無主義,在丹托看來,這個看起來十分合适的稱号所暗示的是否定性與空虛。丹托說,“我将把虛無主義了解為尼采哲學的核心概念,通過虛無主義,我将試圖表明在這些異乎尋常的學說之間的完全系統性的關聯,否則它們就會在周遭的格言與瘋狂的附帶論述中如此蒼白地隐約顯現。我甚至将努力表明,這些附帶論述既不是尼采必須說出的觀點的表面,也不是尼采必須說出的觀點的實質,而是諸多例證以及某些普遍原則對特别情況的應用。最後,我希望确定這些普遍原則在主要哲學傳統中的位置,并将之作為尼采對于所有時代的哲學家最為關注的一些相同問題所提出的解答。”
以下内容節選自《作為哲學家的尼采》中,小标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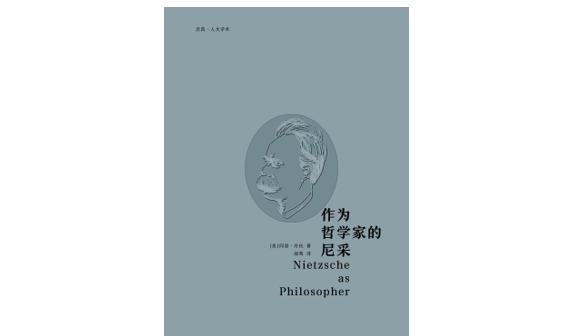
《作為哲學家的尼采》,[美]阿瑟·丹托 著,郝苑 譯,啟真館丨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一個人很快就會對作為作家的尼采感到厭倦
尼采的著作給人這樣一種觀感,即它們是彙集而成的,而不是組構而成的。它們主要是由短小而又尖銳的格言與篇幅幾乎很少超過數頁的短文組成的;每卷作品更多地類似于作者挑選的集錦,而不像一本當之無愧的論著。在一卷作品中任何給定的格言或短文,或許都可以輕易地被置于另一卷作品中,而不會對這兩卷作品的統一性或結構造成多大影響。除了按照時間前後排列的順序外,這些論著本身并沒有展示出任何特殊的結構。它們之中沒有任何一本論著以知悉其他任何論著為先決條件。
盡管尼采的思想與風格必定有所發展,但是,幾乎可以按照任意順序來閱讀他的作品,這不會對了解他的觀念造成巨大的妨礙。他數目繁多、秩序混亂的遺作已經形成多卷作品,并由他的妹妹伊麗莎白·福斯特·尼采——她自封為尼采文學遺産的遺囑執行人——賦予了書名。然而,即便存在某些證據,也幾乎難以找到什麼内在的證據能夠證明,它們是由尼采之外的某個人親手拼湊到一起的,甚至一個十分熟悉尼采作品的讀者也很難說出,在那些由尼采本人付印的作品與那些由尼采的編輯們用片段拼湊而成的作品之間存在何種差異。
在《悲劇的誕生》中的情況必定是一個例外,這樣的例外或許還包括《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因為前者展示了一種符合傳統的統一性,并展開了一個主題;而後者通過在每個部分提出由查拉圖斯特拉發表的說教性言辭獲得了某種确定的外在結構。盡管如此,這兩本書都沒有一種井然有序的發展,沒有論證或陳述的方向。人們可以從任何地方開始閱讀這兩本書。
在這些短文與格言中表達的思想,就像它們的文學表現一樣都擁有不連貫的外觀。僅就單個段落而言,它們是機智的與敏銳的——“布滿了刺痛與隐秘的情趣”——但是,在讀過一些這樣的短文與格言之後,人們就會覺得,它們易于令人厭倦且彼此重複,尼采将諸多幾乎相同的譏諷言辭,反複、再三地投向幾乎相同的目标。第一次看見大海的景象,第一次聽見海浪拍岸的聲音,這些的确能夠令精神得到陶醉與振奮,但當這種經驗被延長時,這樣的感受就消散了;畢竟,波浪在一種顯著的程度上彼此相似,它們很快就變得無法辨認,在某種整體的流動與單調的喧嚣中,我們就失去了它們的特性。
一個人很快就會對作為作家的尼采感到厭倦,正如人們或許會對由諸多鑽石構成的景象感到厭倦一樣,因為這些鑽石最終會讓彼此的光芒黯淡。在沒有結構來維持與引導讀者的思維時,讀者一旦開始閱讀,他們必然很快就會放下這些書,讀者會對這些書産生如此的經驗:它們或者是諸多彼此無關的孤立闡述,或者是模糊不清的光亮與噪音。
這些格言首先給讀者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它們是一個偏執的、惱怒的、具有破壞性的與不近人情的人對同時代的道德、政治、文化、宗教與文學做出的評論與嘲弄——他是一個聰明的怪人,他擁有某種被濫用了的文學天賦,他有一長串的私人煩惱,他更像是那種不斷給編輯寫信的人,而不是一位有建設性的思想家。這些格言會讓漫不經心的讀者覺得,充斥其中的是某種傳統的深刻思想與一種業餘的與難以捉摸的學識:這些格言提到了哲學家、宗教人物、曆史片段、文學作品、音樂作曲,在對這些發表了寥寥數語之後,就迅速改變了主題。人們感到,自己正在打交道的是一個自學成才的怪人,而不是一個大學的教授、一個在德國國文學的嚴格學科中訓練而成的學者,或一個哲學家(就此而言,即便是根據“哲學家”這個術語最敷衍的意義,也無法挽救尼采作為哲學家的聲譽)。專業哲學寫作的标志是精緻而巧妙的區分、周密集結的論證、謹慎而又有保留的推斷,而尼采明顯缺少這些東西。人們也沒有聽過這位哲學家裝出一種冷靜而又嚴厲的腔調。相反,這位撰寫小冊子的作者長期不滿現狀,他發出的是一種尖銳刺耳、吹毛求疵,時而近乎歇斯底裡的聲音。
尼采的作品多半并沒有對讀者的智力與學識提出苛刻的要求。這些觀點顯得清晰而又直接,目标重大而又顯著,語言即便激烈卻也明白易懂。一些讀者受引導後欣然相信,哲學是困難的,但由于尼采的易于了解,他們卻發現要麼是哲學比他們原本設想的更加容易,要麼就是他們自己比他們所認為的要更加聰明。或許也是出于同樣的理由,哲學家才不情願将尼采算作他們之中的一員。這些哲學家到處提及的是一些更加陰暗且更加令人困惑的學說:永恒複歸的學說、熱愛命運(Amor Fati)的學說、超人的學說、強力意志、阿波羅藝術與狄奧尼索斯藝術。
電影《戀上哲學家》(2016)劇照。
或許在這裡,在多少有點狹隘的意義上,尼采就是作為一位哲學家來進行言說的。但是,這些學說并沒有讓人感到,它們以任何系統的與融貫的方式共同比對起來,而且它們無論是在個體上還是在群體上,都無法被輕易歸于某些便利而又無可回避的論題——我們就是用這樣的論題來分辨諸多哲學觀念的。它們似乎也不是那些為我們所承認的哲學問題的解決方案。倘若确實要在這些學說中找到尼采的哲學,那麼,這種哲學就呈現為諸多完全不同的教誨的結合體,它仍然是一種彙集,而不是一種組構,它是由諸多未經證明、錯誤了解的獨特思辨組成的,不适宜将之定位于那種讓哲學批評家或哲學史家感到輕松自在的哲學分析的語境之中。
尼采的文集似乎是正規哲學史上古怪而又不協調的一頁,是插入這門學科的标準曆史之中的一個不合理的推論(non sequitur),而這大抵是因為将其歸于其他曆史時更不顯眼。即便在哲學史中,它也是有待繞開的障礙,而不是從泰勒斯到當下的大量思想或叙事舞台的組成部分。尼采似乎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faute demieux)才歸屬于哲學。然而,尼采自己卻覺得,他已經完全與正規的哲學斷絕了關系;假使尼采的确幾乎不适合這門被他如此頻繁抨擊的學科,那麼,尼采就會說,這對哲學這門學科而言就更為不妙了。如果此處存在一種反諷,這種反諷就是,尼采自己正是其期望摧毀的哲學史中一個引人矚目的組成部分。
毫不奇怪,對于尼采的哲學來說,并沒有類似觀念論、實在論乃至存在主義這樣現成的名稱。尼采有時在言談中将他的哲學稱為虛無主義(Nihilism),鑒于我對尼采的論著、風格與思想所談及的内容,這個看起來十分合适的稱号所暗示的是否定性與空虛。盡管如此,倘若我們多少希望能了解尼采,我們必須讓他的虛無主義擺脫這兩種暗示,并逐漸将之視為一種積極的并究其根本而言是可敬的哲學教誨。
我将把虛無主義了解為尼采哲學的核心概念,通過虛無主義,我将試圖表明在這些異乎尋常的學說之間的完全系統性的關聯,否則它們就會在周遭的格言與瘋狂的附帶論述中如此蒼白地隐約顯現。我甚至将努力表明,這些附帶論述既不是尼采必須說出的觀點的表面,也不是尼采必須說出的觀點的實質,而是諸多例證以及某些普遍原則對特别情況的應用。最後,我希望确定這些普遍原則在主要哲學傳統中的位置,并将之作為尼采對于所有時代的哲學家最為關注的一些相同問題所提出的解答。
一個像海狸那樣建構他的哲學的人,
必然并不了解他自己的哲學
我将提前把尼采的哲學視為一個體系,這個體系并沒有出現于尼采作品的某個地方。這部分是由于尼采特别缺乏組織的才能,他不僅無法在他的哲學作品中展示這種才能,而且無法在他的音樂作曲中展示這種才能。尼采在鋼琴的即興創作上有某種天分,他對于自己的作曲家身份有着高度的評價。尼采與盧梭共享的榮譽是,兩者在哲學史與音樂創作史中都擁有自身的地位。
但是,根據一位批評家的看法,尼采的音樂作品有一個主要的缺陷,即它們展示出了自身“缺乏任何真正和諧的界定,或雖有再現的動機,卻缺乏旋律的連貫性”。他的賦格曲“在華麗的開頭之後……很快就蛻化為更加簡單的結構,他在沒有不可抗拒理由的情況下,多次違背了聲部寫作的原則”。甚至在雄心勃勃的晚期作品中,“簡短的動機占據了支配的地位,完全缺少更加寬廣的旋律或引人入勝的邏輯結構,這些音樂片段從來也沒有獲得充分的動力來讓自己變得令人信服”。這些對尼采音樂的批判性評價,或許也在對尼采的文學産物發出呼籲。在這些文學産物中,沒有任何東西是用非凡的才智進行組織的,沒有任何東西具有知識體系的結構感,例如,它們就不像康德的作品那樣在職責工作的範圍之外都展示了這樣的結構感。事實上,它們就像是對于諸多邊緣的哲學主題的即興創作,突然迸發的即興曲。
除了這種無能之外,還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測,甚至尼采在自己的意識中也從來沒有完全弄清這個體系本身;或者即便尼采對這個體系有所意識,但在他的創作接近終結時,他正在忙于從事其他的規劃,卻不知道他自己可能已經沒有時間來清晰地寫下這個體系。尼采晚期有一封寫給格奧爾格·勃蘭兌斯(Georg Brandes)——他是第一位開辦講座論述尼采思想的學者——的書信,這封信似乎是在尼采生命中陽光格外明媚的時期撰寫的,尼采在其中說道,整整一周以來,他每天都能有數個小時享受到精力充沛的感覺,這讓他能夠從頭到尾地審視我的整個構想,伴随着它的是諸多巨大而又複雜的問題,它們顯著地位于清晰的輪廓之中,可以說,這個構想就在我下方擴充。這需要一種達到最大極限的力量,而我幾乎不再期望自己能夠擁有這樣的力量。多年以來,它一直行進在正确的道路之上,如今它已經全部連貫起來,一個像海狸那樣建構他的哲學的人,必然并不了解他自己的哲學。
電影《都靈之馬》(2011)劇照。
在哲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作者是一點一滴地建構他們的體系的,偉大的作者就更不可能這麼做,而尼采的比喻或許正确地暗示了他就是這麼做的。通常而言,一個哲學體系并不是通過堆積來獲得成長的。然而,對于一個哲學思考者來說,他有可能在一段時間之内以零敲碎打的方式對諸多主題進行分析,卻沒有意識到這些主題是相關的,而對于他尚不知曉的那些解答,他也沒有意識到它們支援彼此甚至有賴于彼此。接下來,他通過艱苦努力得到了一個體系,這個體系并未向他自身公開,除非就像尼采所表明的,這個人被準許在某個時刻綜觀全局,并在這段時間内揭示了他思想的統一性。于是,他就如同自己行為的旁觀者那樣,在不同的陳述與陳述之間,發現了一種他自始至終都在接近,此前卻從未能夠加以辨識的系統必然性。
當然,我們并不能從“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創造了一個體系”這一事實,推斷認為尼采以無意識的方式創造了一個體系,就像我們有時會自然而然地想到某些問題,這個體系深植于作家的潛意識之中,隐藏于這個創造性心智的隐秘幽深之處,直到最後才揭示自身。相反,我相信,我們能夠通過求助于兩個确切的事實來解釋這些成就。
第一個事實是哲學自身的系統本質。哲學學科的特點是,并不存在對孤立問題的孤立解答。諸多哲學問題的互相聯系達到了如此緊密的程度,以至于在沒有含蓄地承諾解決所有問題的情況下,哲學家就不可能去解決或是開始解決它們之中的某一個單獨的問題。在一種切實的(genuine)意義上,每個哲學問題都必然是同時得到解決的。隻有在他接受(即便僅僅是未曾明言地接受)的那個引導他研究的體系之内,他才有可能對孤立的問題進行零敲碎打的研究工作。
盡管如此,倘若他從一開始提供的東西即被證明為哲學中的嶄新答案,那麼就會将某種扭曲引入其概念架構之中,而這些張力或早或晚必定會被某些敏感的心靈感受到。尼采的作品被諸多哲學問題占據,也難以确定他提出這些問題的次序。而尼采在結構能力上的欠缺,讓他難以持久地思考一個問題或在心靈中固定一個問題,直到形成相應的解答。然而,仍然成立的事實是,這種哲學是具備知識體系的,它對它的那個最缺少系統性的踐行者強加了一種外在的系統化,是以,哲學家由于他們事業的本質而具備系統性。人們發現這一點在前蘇格拉底哲學中得到了反複例示。
熟悉某一作者思想的宏大綱要的讀者,或許會轉向該作者少年時代的作品,并在那裡發現令人吃驚的預兆。他将遇到那些預示着其成熟作品中所包含之主題的諸多措辭與觀念,倘若作者從未寫出成熟的作品,讀者就會毫無興趣地丢棄這些少年時代的作品。事實上,對我們來說,如果沒有這些後期文集的存在,我們或許永遠都不會發現,那些在後期檔案中令我們如此印象深刻地認識到的東西,早已存在于這顆年輕的心靈之中。
對尼采來說,也是如此。在他的那些出自19世紀70年代初期的作品中,我們偶爾會發現與他的整個後期作品發生共鳴的諸多觀念,就好像它們早已蘊含其中。事實上,對早期作品産生回響的恰恰就是這些晚期的作品。毫無疑問,在任何作者的思想中都存在着連續性,但這種連續性應當部分地歸因于他的讀者,他們在頭腦中帶着晚期作品來回顧早期作品。他們所能看到的晚期作品,卻是作者在撰寫早期作品時不可能看到的,因為他不可能知道那些他自己尚未撰寫的作品。我們無法思考一種并不統一的人生,如果是在這種意義上,一個人的人生就具備了統一性。
這就将我們帶向了第二個事實。我們傾向于将實際上屬于我們自己的認識歸于作者的潛意識,而實際上,作者卻無法對此類認識有所意識,因為與此有關的事實是,它們并不處于這位作者心靈的深處,而是處于未來之中。倘若他的晚期作品有所不同,這或許會有力地讓我們猛然想到,在我們對我們覺得如此超前的主題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時,事實上我們也無視了一批主題。由于曆史了解所強加的那種具有追溯效力的統一性,它們并未獲得關注。是以,曆史情報工作的統一力量和哲學思想進行系統化的有力行動,在作者的諸多作品(盡管并不包括其文學風格與創作方法)中形成了融貫的結構,這完全無關于他能否向他自己或其他任何人表述這樣的結構。
倘若要表明我希望讨論的體系确實是尼采的體系,就會引發某些關乎哲學史之誠實性的複雜問題。尼采并沒有和我們一起承認這是他自己的體系,他也不曾(或許是因為他無法做到)将他告知格奧爾格·勃蘭兌斯的那個融貫而又内在必然的看法給予我們。然而,尼采本人承認,他肯定沒有意識到這個假定為他所有的體系,盡管通過諸多格言的累積,這個體系正在顯露出來,是以,在他人生的所有時期内,他都不可能打算讓他的作品采納這種形式。
我提供的這個體系需要被了解為一種重構,它必須要按照人們了解任何理論都必然會采取的方式來獲得了解;也就是說,作為統一與解釋某些現象領域的一種手段——在這種情況下,是個人的諸多作品所構成的領域。我将以這些文本作為科學理論家的觀察資料——以便于在不同的觀點上來确證我的理論。我相當确信,至少在一種寬松的意義上,這個理論擁有某種預測的力量;換句話說,它或多或少會讓我們知道尼采将要說些什麼。它讓我們能夠找出我們的道路來穿越這個它意在給出秩序的領域,或至少是我希望如此。
當然,始終有可能存在其他理論,它們不相容于這個理論,卻完全相容于所有似乎支援我的理論的相同僚實。接下來,我的理論将被證明為僅僅是一個可供選擇的體系,倘若有人展示了另一個這樣的體系,它與我認為我已經發現的體系擁有同樣的融貫性,那麼,我也會感到十分欣喜。因為這将預設尼采的哲學是系統性的(無論我們将哪個體系歸于尼采),由此表明的立場将反對人們将尼采了解為某種更加天真率直與非理性的另類思想家的主張。
當然,還存在一種更進一步的可能性,即有朝一日或許會出現未知的事實(比如,出現了某些迄今為止都未被發現的文本這類情況),它們将證明我的解釋完全是無效的。人們不僅必須在建立科學理論的過程中冒這種風險,而且還必須在建立哲學理論的過程中冒這種風險。我們在各處發現,尼采除了提到他的體系之外,還對他的哲學的最終系統陳述做出了諸多概述與規劃。根據目前的知識所得出的結論是,它們之中沒有任何東西得到實作。
尼采在1889年陷入瘋狂,自此以後他就沒有撰寫任何東西;在其肉體之意義上的死亡之前的暮年,他在餘下的十一年時間裡過的是一種沉默的生活。但是,他死後出版的作品(即《遺稿》)那絕對龐雜的規模,以及除了最為外在的形式之外,他似乎完全沒有能力将任何形式施加于他的這部作品之上,這就幾乎可以確定,即便尼采仍然心智健全,他也不會對這部作品進行整合性的系統化。《遺稿》的淵博内容以及已出版作品的規模,確定了他不會對其他的某些作品進行整合性的系統化。
一旦尼采由于精神錯亂而陷入無助的狀态,其人、其作品與其聲譽就全都交由他的妹妹來照管。她與另一些人擅用編輯的自由來處理尚未出版的作品(乃至某些已經出版的作品),由此他們的編輯工作就醜聞纏身。“尼采的生平與著作遭受了現代文學史與思想史中最嚴重的僞造。”歪曲、遺漏、欺騙性的添加、虛假的結構讓這部文集大為遜色;直到現在,這些文字才通過最為耐心的文獻學工作而獲得了改善,諸多文本、信件乃至尼采的生平年表才被恢複成它們真實的次序。人們必須承認這是暴行,而根據學術的觀點,這些僞造完全是不道德的。
不過,我相信,對于我們有可能在尼采目前的論著或被清除謬誤後的論著中發現的哲學來說,這些複原工作幾乎不會産生什麼影響。伊麗莎白·尼采主要是在涉及她與她哥哥的關系的部分做出了帶有誘導性的篡改;她想要為自己争取的形象是尼采的知己以及第一個了解了尼采最陰暗思想的人。她随處篡改尼采的文本,以便于按照她了解的方式來拯救她哥哥的美好聲譽,而這則會不時地讓尼采顯得是在倡導他其實頗為蔑視的學說。她篡改的從來都不是哲學的學說;事實上,她對哲學觀念僅僅具備孩童般的了解力,而且她也不認識懂得曲解哲學的人。即便她對文本的幹預(連同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與其他人的幹預)要比我們現在想象的更大,但在我們闡釋尼采的哲學時,它們所産生的後果卻幾乎是可以忽略的。正是在這個方面,這些松散結合的格言、斷片和短文至少在這一點上是對尼采有利的。他的主題思想反複出現,以至于根據他作品中随意挑選出來的任何樣本,幾乎都能重構他的哲學整體。
有一種理論認為,我們的記憶貯存于蛋白質的分子之中,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體中都存在這種蛋白質分子,且數目巨大。這些分子具有引人注目的幂等性(idempotency),即精确複制自身的屬性。根據這種理論,相同的資訊被貯存于全身的各個位置,是以即便有一個部分被摧毀,我們的記憶仍然可能完整無缺,我們就會繼續将之與我們自身相整合。這種蛋白質分子的豐富性與幂等性,幾乎可被視為生物恰巧造就的一項避免自我毀滅的保障。尼采那些數量過多,卻又古怪地進行重複的格言,恰恰就是以相同的方式來處理相同的問題,在我看來,它們也會産生這個相同的結果。新的作品有可能被發現,舊的作品有可能被複原,但很難設想它們将為我們提供這樣一種哲學——它在任何本質的方面有别于我們可以通過仔細考察現有的尼采文本而發現的哲學。
原文作者丨[美]阿瑟·丹托
摘編丨何也
編輯丨申婵
導語校對丨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