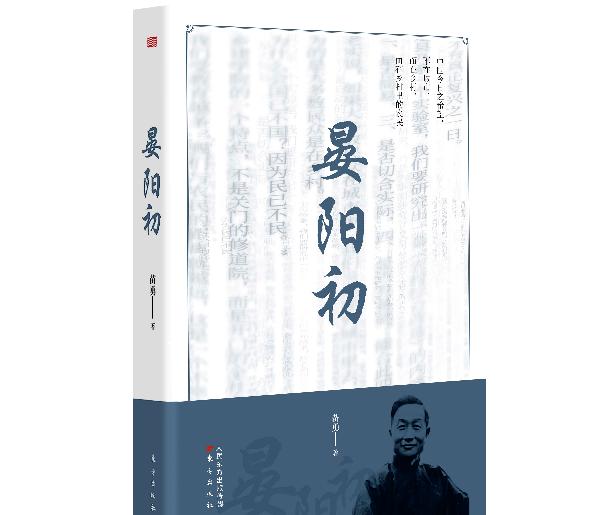
故鄉情懷與英雄情結對接之書
——讀苗勇新著《晏陽初》
凸凹
苗勇是一位文涉紀實文學、詩歌、散文、小說、評論等多門類著作等身的蜀中作家。在他的衆多作品中,其題材選擇,有一個占比很重的鮮明旨徑,那就是對故鄉巴中持續發力、深耕細作的呈述與熱愛——這已然成為他秘密公開的文學“宗教”與文學宿命。他的近五十萬言新著、傳記文學《晏陽初》依然沿襲了這一脈向。具體說來,他是将循環在自己骨血中的故鄉情懷轉切為對一位故鄉人物傾力複盤式的塑造上。不僅讓自己,也讓一位有大能量的人物,為故鄉賦能。這個有大能量的人物,自是顯示在書名上的晏陽初。
關于晏陽初,我最初是從我的國小并中學同學、巴中籍人士陳艾平口中知道的,那時我還在萬源縣城念國中。但我知道的,僅止于巴中有個名人叫晏陽初,他是民國時期的平民教育家、貧窮鄉村改造建設實踐者。事實上,他哪裡隻是離我們較遠的民國時期人物?壽齡百歲的他,活到了1990年。隻不過,他後來的事業發生地已轉移海外,面向全世界。
後來,我陸續讀到介紹晏陽初的一些文章和書籍,我認為自己比較全面地認識了同學口中的那位鄉黨。
直到這幾天放下手頭俗務,一口氣讀了苗勇筆下的《晏陽初》,才又臉紅地知道,我所謂的全面,實則片面。
首先,我之前讀到的晏陽初,是平面的、色彩單一的晏陽初,其呈現基本就一個範式,即,人生線等于事業線。
苗勇對晏陽初的呈現就不同了,既是曆史事實的陳列,更是文學藝術的建構。
全書由三條線在時間的順流與回流中,自覺不自覺地自然穿梭、交集構成。這三條線,除了其他文章家專營的事業線,苗勇還着力壘砌了情感線和故鄉線——這是此書的最大特色和價值所在,當然也是其可讀性強的核心密碼。
關于事業線,作者扭住“民唯邦本,本固邦甯”(《尚書·五子之歌》)八字理念不放,梳理、繪寫了傳主晏陽初從美國耶魯大學,到一戰歐洲戰場,到中國大地,到菲律賓,到世界諸國,憑一己之力,聚集同志,以民間行為方式,推動、整合包括國家在内的各種資源,在廣大的落後鄉村直面“愚、貧、弱、私”的農民兄弟,成功展開一系列令全世界矚目的變革時間程序的“四育并舉”實踐:用文藝教育攻愚,發揚知識力;用生計教育攻窮,開發生産力;用衛生教育防病治病,培養健康力;用公民教育攻私,發揚團結力。最終實作讓全世界文明的主體基底,即占全人類總量四分之三的廣大農民,迅速實作“除文盲,作新民”的宏大願景。
在無時不在的情感線裡,作者渲染出的氣場,端的是動了每一個字、每一個标點符号的情。“一到定縣來,晏陽初便用心學習定縣方言,以便更好地和當地的村民交流。如今晏陽初如果脫去這一身青色長衫,沒有人不認定他是一個定縣人。”“在往後的很多日子裡,晏陽初常常想起煙台那個身穿更新檔衣服的鄉下小姑娘。”從晏陽初對親友的情,對妻兒的情,對師長的情,對故人的情,對同學同僚的情,對祖國的情,對人類尤其是對農民的常含淚水的深沉情意中,讓讀者感到的是,那個在時間和空間的語境裡都遠離自己的平民教育家,其實就是我們在農貿市場看見的一位盤攤的低收入市民,在鄉村田坎上遇到的一位戴草帽、挽褲管的農技幹部。不用說,沒有作者對傳主的真情實感,就沒有傳主對自己鐘愛之人之物的真情實感。這不是虛構、非虛構的分歧認知,而是表達的實作、未實作。此哲學正理,正如沒有語言文字,就沒有曆史和世界一樣。
準确地講,我說的故鄉線,也是一條情感線,既指晏陽初對故鄉的情感,亦指故鄉對晏陽初的情感。我說的故鄉,既是那片有山有水有森林有藍天的土地,也指那片土地上的族人、朋友、恩師、曆史和民俗;既指傳主牽腸挂肚的狹義的巴中,亦指傳主蹤迹累疊的巴蜀大地。故鄉,是一個人的出處,是一個人成長、怎麼成長的根脈、氣口與初因。父母的血緣傳遞與耳提面命,巴中福音堂魏牧師的言傳身教,保甯府(今四川阆中)天道學堂姚明哲的培養與引薦,成都傳教士史文軒的傾力襄助——正是這些來自故鄉的接力加持,讓晏陽初在成長中壯大,完成了翻山越嶺從巴中到成都,沿古驿道東大路從成都到重慶,繼而順江出夔門、泊岸香港,直至進軍美國,實作了立志獻身拯救平民出苦海這項偉大壯舉。這是故鄉給予自己兒子的情感。在作者傾情的書寫中,晏陽初對故鄉的情感,貫穿密布了他漂泊五洲四海的一生。在香港,“他想到了史文軒兄妹為他的讀書慷慨解囊,想到了遠在巴中的白發蒼蒼的母親和親人,想到自己的志向和抱負”。在巴黎,“晏陽初收回目光,擺開架勢,打了一趟拳。這還是童年時在家鄉巴中時,央求二哥教的呢”。海外學成回到祖國,“一踏上回巴中老家的路,晏陽初就心潮澎湃,難以平靜。多少次,思鄉之苦牽萦着遊子的心,夢中母親白發蒼蒼的容顔,倚門回望,幾多次讓他夢醒後淚濕枕衾”。書中寫晏陽初與故鄉的故事容量與鄉愁體量,差不多占了全書近三成之多,而以插叙的形式嵌入書中的專章第八章,基本上皆為晏陽初與巴中的情感激蕩與遐思交割。他給予故鄉最大的回饋,是因為他的人傑式存在,故鄉感到了無比的地靈和驕傲。
事實證明,也隻有傳主的故鄉人,才能寫好傳主的故鄉事——包括情感在内的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讓外鄉人望洋興歎。
本書正叙、倒叙、插叙并施,但大緻還是依從了章回式的結構編排,細節描寫和氛圍營造也充分突顯了文學性品質與效果。此外,讀者還能夠在苗勇的叙述道法中看見一種平實中見奇崛的語言修飾風景,如,“母親的聲音真好聽,像緞子一般平滑柔和,絲毫沒有先前的威嚴”。再如,“也許多年以後,土街會溫馨地回憶起這樣的一個細節:一位四十左右儒雅的中年人身着青色長衫,雙目深邃,面帶微笑,在定縣街上從容不迫地走着”。
作者行文介紹晏陽初的同時,不時穿插對晏陽初的評論。從這一表征看,将這本傳記歸類評傳文學體式也未嘗不可。“可他俯下身來,滿懷悲憫為全世界最底層的人們奔走,一生都在為改變底層群眾這個最大公約數的生活狀況而奔走,無怨無悔,窮盡一生。這不禁讓人想起弗羅斯特的那首著名的詩歌《未選擇的路》。”
古代科舉,有文狀元和武狀元之分。同理,英雄自是有戰鬥英雄和文化英雄之别。晏陽初無疑是文化英雄,一名出自巴中、完全徹底不折不扣的世界級文化英雄。而與生俱來的古老的英雄情結,不僅結實在苗勇這個名字上,更結實在整部書的陽光、雨水和晨鐘暮鼓中。其實,書劍飄零一生,對清代名将、蜀中鄉人楊遇春特别敬仰的晏陽初,在多年的時間段裡将自己易名為晏遇春——從這一點即可看出,他的救萬民出離深淵,由家國意識、故鄉情懷和英雄主義思想晶凝成的英雄情結,是多麼具體和彰馳!
這是一本什麼書,為什麼要寫這本書,怎樣寫這本書?這些問題,其實作者已在後記中道出了底牌:“原來,遠在幾十年前,那個從巴山深處走出來的名叫晏陽初的寒門子弟,在神州廣袤的農村裡,和一群當時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進行着一場多麼廣闊的鄉村教育運動。他和他的同僚,躬身前行,一心為民,為了中華民族的振興,而努力奮進着。後來,他把自己的鄉村改革理念,推向全世界,為地球上最苦難的人們的幸福,窮盡了一生的心力。不知道者,是無知。現在,我知道了,而不告訴更多的人,就是對偉人的不敬。一個願望就在心裡悄悄滋生:總有一天,我要寫一本書,寫一寫晏陽初,寫出我心中的仰望,讓許多尚不知道他名字的人,熟悉他,了解他,記住他,緬懷他。同在桑梓,後輩如我,以筆為口号,當是最好的紀念方式。”
(凸凹,本名魏平。詩人,小說家,編劇。四川省散文學會特邀會長,四川省詩歌學會副會長,成都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大三線》《甑子場》《花兒與手槍》《蚯蚓之舞》等書共20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