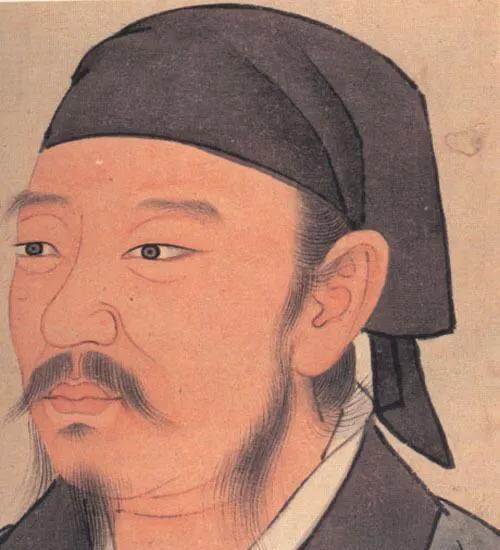譯注:方勇 李波
出版:中華書局
議兵
三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是以得天下也;不由,是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鲛革犀兕以為甲,鞈如金石,宛钜鐵釶,慘如蜂虿,輕利僄遬,卒如飄風,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為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是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颍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是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纣刳比幹,囚箕子,為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懔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是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诎;城郭不辨,溝池不拑,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内者,無它故焉,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響,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由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利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
譯文:“禮,是治理國家的最高準則,是使國家強大的根本,是威力盛行天下的途徑,是建立功名的綱要。天子諸侯遵循它,就能得到天下;不遵循它,就會毀掉社稷。是以堅固的铠甲和銳利的兵器不足以取得勝利,高高的城牆和深深的護城河不足以堅不可破,嚴厲的法令和繁多的刑罰不足以威吓人民,遵循禮義之道就通行,不遵循禮義之道就失敗。楚國人用鲨魚皮、犀兕皮制成铠甲,堅硬得就像金石一樣,宛地的鋼鐵制成的矛,厲害得如同毒蠍一樣,士兵行動輕快靈活,迅速得就像旋風一樣,然而兵敗垂沙,唐蔑戰死,莊蹻起兵反叛,楚國就四分五裂了。這難道是沒有堅甲利兵嗎?是因為他用來統治的辦法并不是禮義之道的緣故啊!楚國以汝水、颍水作為天險,以長江、漢水作為護城河,用鄧林作為屏障,用方城作為圍牆,然而秦國的軍隊一到而鄢、郢就被攻陷了,就像搖落枯樹葉一樣。這難道是因為沒有堅固的要塞和險阻嗎?是因為他用來統治的辦法并不是禮義之道的緣故啊!商纣王将比幹剖腹挖心,囚禁了箕子,制造了炮烙的酷刑,殺人随便,臣下心驚肉跳,不知是否能保住性命,然而周軍一到而政令就不能在下面執行了,也不能役使他的人民了。這難道是政令不嚴厲、刑罰不繁多嗎?是因為他用來統治的辦法并不是禮義之道的緣故啊!古時的兵器,隻不過是戈、矛、弓、箭罷了,然而不等使用就使敵國屈服了;城郭不修理,護城河不挖掘,要塞不設立,權謀機變不施展,然而國家安然不畏外敵而且非常鞏固,這沒有别的原因,是因為實行了禮義之道而用等級名分來協調,按時使用民力而真誠地愛護他們,人民和君主如影随形、如響随聲,有不遵從指令的然後用刑罰懲治。是以懲治一人而天下就順服,犯罪的也不怨恨他的君主,知道罪過在于自己。是以刑罰簡省而威力強大,這沒有别的原因,是因為遵循了禮義之道的緣故。古時帝堯治理天下,隻殺了一人、懲處了兩人而天下就得到治理。古書上說:‘威勢勇猛卻不使用,刑罰設定而不施行。‘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勢詐不足以盡人之力,緻人之死。為人主上者也,其是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勢詐除阸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犇,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故賞慶、刑罰、勢詐之為道者,傭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緻忠信以愛之,尚賢能以次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顧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後刑于是起矣。是大刑是以加也,辱孰大焉?将以為利焉?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戆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于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于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将以為害也?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于其前,縣明刑大辱于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化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願,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矜糾收缭之屬為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譯文:“大凡人們的行動,為了獎賞才去做的,那麼看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就會停止。是以獎賞、刑罰、權勢欺詐不足以使人竭盡全力,以緻獻出生命。作為君主的,對待百姓不用禮義忠信,大抵隻是使用獎賞、刑罰、權勢欺詐威逼他們,獲得他們的功用罷了。強大的敵人來臨,讓他們堅守危城就一定會叛變,遇到敵人進行戰鬥就一定會失敗,安排勞苦煩瑣的事情就一定會逃跑,渙然離散,人民反過來挾制了君主。上是以獎賞、刑罰、權勢欺詐作為一種方法,實際上是雇傭人出賣力氣的方法,不能團結大衆,治理好國家,是以古人恥于這樣做。是以,要加強道德聲望來引導人民,明确禮義來指導人民,務求忠信來愛護人民,尊崇賢人,使用能人來安置人民,用爵位、服飾、獎賞來激勵他們,依據時節安排事務、減輕他們的負擔來調節他們,養育他們,就像保護嬰兒一樣。政令已經确定,風俗已經一緻,有背離風俗而不順從他的君主的,那麼百姓就沒有不怨恨厭惡他的,沒有不認為他是禍害妖孽的,就像驅除不祥一樣鏟除他,然後刑罰從此興起了。這種人是大刑所施加的對象,恥辱還有比這更大的嗎?認為這有利嗎?但大刑加在身上了,如果不是狂惑鄙陋的人,誰看到這種情況會不改過呢?然後百姓都清楚地知道遵循君上的法令,依從君主的意志而安心快樂,于是有能夠改惡從善、修養身心、端正行為、奉行禮義、尊重道德的,百姓沒有不重視尊敬他的,沒有不親近贊譽他的,然後獎賞從此興起了。這種人是高官厚祿所授予的對象,榮譽還有比這更大的嗎?認為這有害嗎?但高官厚祿來供養他,凡是人,誰不願意呢?清楚明白地把高官重賞擺在他的前面,把嚴明的刑罰和最大的恥辱放在他的後面,即使不想變好,可能嗎?是以人民歸順他就像流水一樣,凡是到過的地方都得到全面治理,凡是施行的地方都得到教化而順從。兇暴、強悍、勇猛、強壯的人得到教化而忠厚,偏頗、邪僻、自私的人得到教化而公正,急躁、暴戾的人得到教化而心平氣和,這就叫做最高教化的極點。《詩經》中說:‘王道遍行天下,徐國也來歸順。‘說的就是這個情況。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強,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勢,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衆,奉養必費,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饑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委之财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期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譯文:“凡是兼并他國的君主有三種方法:有用道德兼并他國的,有用武力兼并他國的,有用财富兼并他國的。那些國家的人民尊重我的名聲,稱贊我的德行,想做我的臣民,是以打開城門清掃道路來迎接我入城,我順從該國人民的習俗,不改變他們的住處,百姓都安定,制定的法律與頒布的指令沒有不順從的,是以得到土地而權利更大,兼并别國而兵力更強,這是用道德兼并他國。那些國家的人民不尊重我的名聲,不稱贊我的德行,隻是懼怕我的威力,迫于我的權勢,是以他們雖然有離去之心,卻不敢有背叛的想法,像這樣,那麼兵士就會越來越多,供養花費越來越大,是以得到土地而權力更輕,兼并他國而兵力更弱,這是用武力兼并他國;那些國家的人民不尊重我的名聲,不稱贊我的德行,因為貧窮追求财富,因為饑餓追求溫飽,空着肚子張着嘴巴來投奔我求食,像這樣,那麼就一定拿糧倉、地窖裡的糧食來喂養他們,送給他們錢财貨物使他們富裕,設立善良的官吏來接待他們,三年之後,這些人民才可信任,是以得到土地而權力更輕,兼并他國而國家更貧窮,這是用财富兼并他國。是以說:用道德兼并他國的就稱王,用武力兼并他國的就衰弱,用财富兼并他國的就貧窮。古今是一樣的。
“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裡,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而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皆百裡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譯文:“兼并他國容易做到,隻是堅守和鞏固它很難。齊國能兼并宋國但不能鞏固,是以被魏國奪走了;燕國能兼并齊國但不能鞏固,是以被田單奪走了;南韓的上黨,方圓數百裡,城池完整、府庫充足而投奔了趙國,趙國不能鞏固,是以被秦國奪走了。是以,能兼并他國,卻不能鞏固,就一定會被奪走;不能兼并他國又不能鞏固已有的土地,就一定滅亡。能鞏固本國,就一定能兼并他國。得到他國的土地而能鞏固,再兼并就不會有強大的對手了。古時湯憑借亳地,武王憑借鄗地,都是百裡見方的領土,卻統一了天下,諸侯臣服,沒有别的原因,他們能鞏固已取得的土地。是以團結士人要用禮義,團結人民要用政治,禮義美好那麼士人就臣服,政治清明那麼人民就安定。士人臣服、人民安定,這就叫做最大的凝聚,用來守衛就堅固,用來征伐就強大,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稱王天下的事業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