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8月,郭沫若的詩作《女神》問世,在詩界引起了革命性的震撼。以《鳳凰涅槃》《天狗》為代表,其空前激蕩的情感,傳達了"五四"時期除了老創新精神。
熟悉西方詩歌的讀者很容易發現美國詩人惠特曼對郭沫若的重要影響。
不過,細心的讀者一定會在其他幾首安甯祥和的美麗詩中感受到另一首韻律——《新月與白雲》《太陽》、《春之悲》、《歌聲》《遲到的腳步》......這些詩歌在詩集中彼此排列。有的讀者,甚至是評論家,認為那些随心所欲、粗俗的詩歌是作者初期對激情青春的嘗試,而這些安靜、平和的詩歌,想要來的是詩人的激情褪去,技巧的成熟逐漸稀釋了收益。雖然這種考慮有相當的道理,但事實并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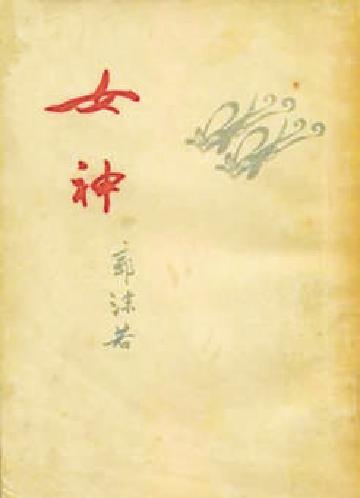
郭沫若第一次了解泰戈爾的詩歌
1914年9月,郭沫若努力學習了6個月,考入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學校。他和一個三年級的大學生親戚住在一起。有一天,學生從學校帶回了幾頁油印版的英語課外朗讀,郭沫若看了一眼,是印度詩人泰戈爾的《新月集》中的幾首短詩:"寶貝路"《偷睡》《雲海》《岸邊》......初讀時,郭沫若非常驚訝。因為這是他以前從未見過的東西:"首先是對詩歌的易懂;""這不是押韻,但超過兩節,或三節戰争詩,那新鮮的和平很容易讓我感到驚訝,是以我跳得更年輕了二十歲!"
于是,郭沫若與泰戈爾的詩歌形成了莫名其妙的關系,他開始四處尋找泰戈爾的詩歌來閱讀。當時,泰戈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不久,他的詩歌在日本非常受歡迎,他的詩集在東京并不容易獲得。郭沫若讀了整本書《新月》,已經一年後進入岡間高中大學生的事情:"我拿到了他的《新月合集》,看到那種優雅的裝訂和幾頁無聲的插圖,我心裡真的很開心,仿佛一個孩子有了一個畫像。
1916年秋天,郭沫若突然在岡山圖書館發現了泰戈爾的《吉丹加裡》、《園丁的收藏》和《愛情贈品》等詩歌。乍一讀,用他自己的話說,"我似乎真的找到了我的'生命',我找到了生命的春天。"看書時,由于害怕打擾人,郭沫若發現一間很暗的閱覽室,坐在角落裡,面對面靜靜地拿着書。在這樣特殊的情況下,郭沫若甚至因為激動和淚水而感激不盡。他長時間沉浸在這種安靜的氣氛中,有時從中午兩三點開始,直到光線亮起。這樣的讀書和感受,讓郭沫若在思想和藝術上深受泰戈爾的影響。
兩個世界之間的距離
在此期間,郭與日本女子安娜(現稱為佐藤福子)發生了關系。泰戈爾的影響與愛情相撞,使郭沫若的創作欲望受到強烈激發。他在一些牧羊人的歌曲中寫了"新月和白雲","死亡的誘惑","離開","維納斯"和"牧羊人的悲傷",其中大部分是為安娜寫的。例如,這個"後期步驟":
松林!你怎麼這麼新鮮!
我和你一起住了半年。
從未見過
這條沙路太平坦了!
兩人車廂從我面前經過,
疲憊的兩個司機在唱歌。
他們的空車裡有什麼?
應該聽到潮汐:和平!平靜!
詩中泛愛的思想,精緻清新的風格,清晰地展現了泰戈爾的深遠影響。
1917年前後,由于他的愛情,郭沫羅翻譯了許多泰戈爾的詩歌。下半年,他和安娜的孩子們就要出來了。這樣,郭沫若有限的出國留學費用,顯然無法支撐家庭的需要。然後,他從新月集《吉丹加裡,園丁的收藏》中挑選了一部分,并将其編纂成"泰戈爾詩選",用中英對比進行注釋,并被送往該國尋求出版,以換取一些手稿來補貼家庭,但結果适得其反。
當時,中國大陸,知道泰戈爾的人民非常有限;鮮為人知。他的詩歌,要麼被唱出來,要麼被平靜地淡化,僅僅幾年後就被中國人民所接受,進而震撼了詩歌界,獲得了廣泛的聲譽。是以,他寫信給當時著名的商業印刷廠,要求出售"泰戈爾詩歌選集",該書由博物館歸還;在青春的敏感階段,飽受生靈雙重痛苦的郭莫羅,遭受的一擊可想而知。
結果引起了郭沫若的不同反應。他忽然覺得自己和泰戈爾不是那種人:泰戈爾是高貴的聖人,他是個平庸的人。兩個世界的距離讓他覺得自己對泰戈爾的愛是"一條鴻溝"。很難想象,真正的壓迫,竟然能給人類精神帶來如此巨大的變化。但事實正是如此:"從那以後,我與泰戈爾的精神聯系受到了打擊。"
由于看似偶然的因素,世界上的事情有時會發生很大的變化。這從郭沫若對泰戈爾觀的轉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遺憾的是,費了郭沫羅費了不少功夫的泰戈爾詩歌選編,在轉彎的路上卻丢失了,以至于後來收集他譯本的《摩洛翻譯詩》沒有收到泰戈爾的詩。不過,在郭沫若的文章中,我們偶爾可以讀到他對泰戈爾詩句的翻譯,這裡不妨摘錄一節,一睹豹子的一瞥。1920年2月,郭沫若寫了一首詩《論詩的三顆藍寶石》。文章關于詩歌的内在節奏,這種讨論:"内在的節奏吸引着沒有耳朵的心靈。泰戈爾有一句詩,最好用這一點來說明。
請把這個秘密放在心裡,我的朋友!
請對我說,隻是悄悄地對我說。
你笑得那麼委婉,請輕聲說,我的心能聽,不是我的耳朵。園丁收藏,第42号
這種節奏是如此微妙,以至于任何曾經到達過詩歌的人都無法了解它。這意味着它是"音樂的精神",但它不能說是音樂。音樂已經變得有形,内在的法則是無形的交流。"
他的歌曲"On the Shore"的第三節也直接指向泰戈爾:"我的Ahe/And Some Kids/Play in the Sand"/我讀了泰戈爾的一首詩,/我也去和他們一起玩。/ 嘿!我怎樣才能成為一個純潔的孩子?"
後來,這些受泰戈爾影響的詩歌發表在《時事》的"學習之光"欄目中,極大地激發了郭沫若的熱情。然而,不久之後,他讀了惠特曼的《草和樹葉集》。即擺脫了所有舊形式和内容的風格,強而宏偉的天氣,與"五四"時期的青春精神非常和諧。在惠特曼的影響下,再加上《學光》主編宗百華的熱切催促,郭沫若的詩火火山"噴發"了。在1919年至1920年的三四個月裡,郭沫羅創作了一些他一生中最好的詩歌:"站在地球的邊緣","地球,我的母親","晨好","鳳凰涅槃","心光","爐子裡的煤""大炮的教訓"......他們還催生了詩集,這是中國新文學史上浪漫主義詩歌的基礎和巅峰作品《女神》。
從上述課程可以看出,郭沫羅最初深受泰戈爾的影響,但他的名氣卻取決于一些受惠特曼影響的詩歌。在時代需求和創作之間,往往不作為人們的主觀想象,而是有意或無意地影響了詩人的創作方向。此後,郭沫若的詩歌反映了泰戈爾的影響因素,一直很單薄。不僅如此,随着時代的發展,郭沫若給自己送出了很多近乎"涅槃"的快樂詩人,也有不少不滿意。
1941年,郭沫若在重慶
藝術家創作之路的轉變
1924年,偉大的詩人泰戈爾應邀通路中國。在中國訪華之前,國内多家報紙為此目的做了大量宣傳:或者翻譯自己的詩歌,或者出"專号"引起宣傳......此時,郭沫若,無論在文學界的名聲、地位如何,都無法與往年相提并論,思想的轉折點,也是意料之中的。
此前,1923年10月,郭沫若寫了一篇題為《泰戈爾來華見我》的文章,表達了他對詩人訪華的看法。文章中,郭沫若對當時國内的熱議邀請文化名人杜威、羅素到中國發言,表達了不滿。他認為,普通中國人沒有研究這些名人的思想,要求他們隻不過是虛榮的标志。在他看來,這一熱鬧的事件就像是一次又一次的"神會"的演戲,而當他準備邀請泰戈爾訪華時,在他看來,這隻是又一次"神會"。
泰戈爾(第二排右)1924年在清華大學
這時,郭莫若想:"他(泰戈爾)的思路我認為是泛神論的思想,他隻是把印度的傳統精神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在西方過于活躍以至于無法失去根基的時代,泰戈爾先生的森林哲學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福音。但我們早已沉浸在死去的東方民族中,我們的生死代理人不在這裡。"
至于泰戈爾的宣傳,郭沫若認為,在當時的中國,沒有必要:"梵文的一切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隻能作為無産階級的嗎啡和椰子酒;無原則的非暴力宣傳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毒藥。"我們可以看到,此時,郭沫若,已經自覺地堅持了唯物主義的曆史觀,站在底層觀察、分析事物,運用各種主義,而不是因為愛泰戈爾而放棄有意識的轉移立場。郭沫若的文章,或許還有文學同仁的影響不為人知,但他的改變心思卻是顯而易見的,雖然時間隻是在過去幾年。
人的生存之路,藝術家的創作之路,有時會改變。這種變化,有時是有意識的,有時是非自願的,由時代的潮流推動和移動。郭沫若之前對泰戈爾的迷戀,僅僅幾年後才重新了解他的思想,批評可以稍加證明;當我們分析和了解一個人或詩人的思想或詩歌的演變時,我們有時必須簡單和模式化。但人類的實際發展是極其複雜的,與時代、甚至許多偶然因素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