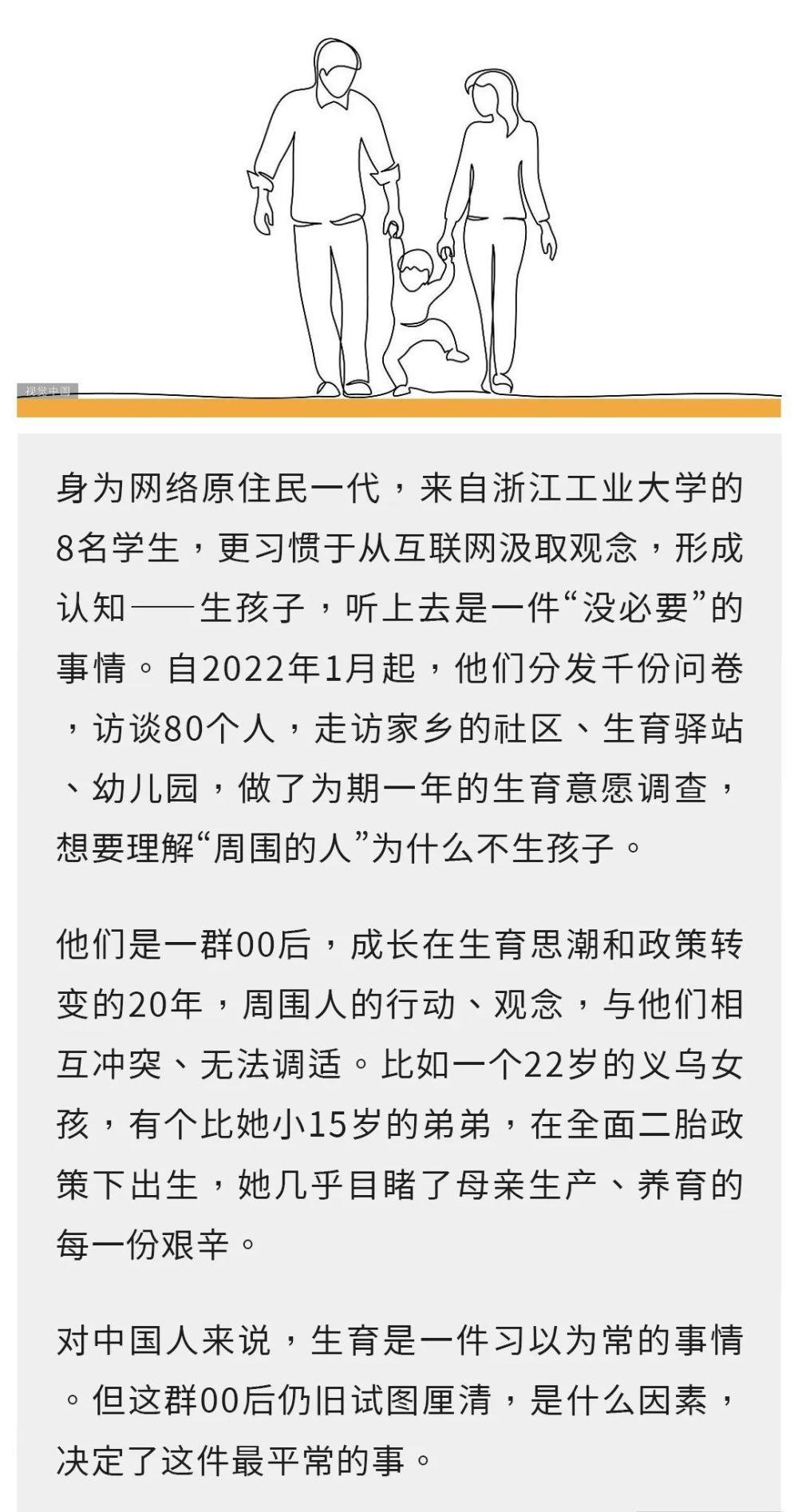
文 | 徐巧麗
編輯 | 陶若谷
“不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想不想要一個妹妹?”50歲的爸爸把這句話抛給了黃一鳴。
那是去年6月底一個普通的周六,屋外蟬鳴,暑意飄過紗窗。電視機前,黃爸爸躺在貴妃椅上,刷着抖音裡咿呀學語的萌娃們,露出由衷的笑意。黃一鳴坐在旁邊的沙發上,以為聽到的是個玩笑。
“你都多大了?”黃一鳴也像玩笑般回他。黃一鳴在浙江工業大學讀大三,暑假回家,發現爸爸總是刷一些萌娃視訊。他以為,是短視訊讓爸爸産生了這個念頭。爸爸年紀大了,突然開始健身鍛煉,性格變得有些啰嗦。多一個妹妹,意味着維持20多年的家庭結構徹底改變,有什麼必要?
加班的媽媽下班後,他從媽媽口中得知,這個念頭,爸爸在媽媽面前念叨了好多次,“他不是開玩笑的”。但黃一鳴仍舊覺得太草率了。
為着這個念頭,家裡開了一次家庭會議。“誰來生,誰來養?”黃一鳴比爸爸考慮得更多,“一個是媽媽的年紀是不是适合生育,一個是你們還是上班族,有沒有精力帶孩子,總不能去找外婆、爺爺奶奶來養。”黃媽媽表示支援。面對這些質問,坐在他們對面的黃爸爸,未置一詞。
黃一鳴覺得,在上一輩眼裡,就像瓜熟自然蒂落,草自然結籽,“生孩子也好像就是這麼随口一說的事情。”但他很難了解這種生育觀。對他來說,生還是不生,是需要反複權衡的——“從想要生孩子的那一刻起,你就必須要承擔一種責任,你沒有做好對未來所有可能的預估的話,幹脆就不要結婚、不要生孩子。”
他出生于2000年,漫畫、小說伴随他長大,高中擁有了手機,就看微網誌、逛貼吧,最喜歡的是B站,和裡面的使用者“同頻”。作為獨生子女,他出生在一個開明的環境,初高中,母親就建議他多談戀愛,他也嘗試過幾段戀情。
“會覺得我是獨立完整的個體,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家人的束縛。”他從小就和父親對着幹。小時候,父親會給他布置奧數題,他做不出來會挨罵,甚至挨打,他一言不發。國中,他和朋友出去玩,時常會和掌控欲強的父親争吵。大學裡,他放棄父親給他選擇的制藥專業,選擇了文科。
每次被衣架追着打、被罵“你怎麼這麼蠢”的時候,他會覺得,“這種你累我也累的關系,完全是人生的累贅。”
有一年春節,爺爺殷切叮囑他“早點讓我抱重孫”,他嘴上應付着,等到晚上和爸媽散步,他突然問他們,“你們可不可以接受我不結婚,也不生小孩。”他記得,爸媽第一反應是“這不正常”,但想起他的叛逆,才改口說“随便你”。
和黃一鳴一樣,他的同齡好友,都覺得生育沒必要。他們的觀念反映了新世代的生育意願。2020年,第三屆人口與發展論壇一項調查顯示,作為生育主體的00後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僅為1.48個,低于90後。一份《2021年廣州市生育意願調查報告》則顯示,育齡女性的生育意願有随年齡減小而降低的趨勢,其中00後最低。逐漸進入婚姻、生育的年紀的00後,卻開始選擇“自願少生、放棄多生甚至不生”。
●杭州某街道的生育宣傳手冊。講述者供圖
作為00後女生,義烏人李芳菲就覺得,“不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現在讀大三的她是一個古靈精怪的女孩,肉嘟嘟的臉上架着細框眼鏡,會戴上10塊錢的黑色爆炸頭假發,在朋友圈發四宮格照片。
“不生”的想法源自高中。那時的英語老師曾留學國外,日常上課時,會強調“女孩子一定要有經濟能力,不要習慣于依靠其他人”“學識上的眼界比男朋友更有安全感”。那是李芳菲第一次接觸女性思潮、男女平權的觀念。
上大學後,她開始建構對婚姻、家庭的想象。周圍的同學、朋友,無不經曆着戀愛的“苦澀”而非“甜蜜”。情感控制、因為不回消息而生氣、不負責任……聽多了,她覺得談戀愛确實是一件挺花費精力的事情。
尤其是在越來越卷的當下。拿出國留學舉例,“想申請好一點的學校,都會要求你平均分90以上,還要你做科研項目、發論文,要有實習經曆、大賽經曆,最好還有一點學術的身份在身上。”根本無暇顧及戀愛、婚姻,遑論生育。
2016年,也是全面二胎政策實施的那年,李媽媽取下了留在肚子裡十多年的節育環。不久之後,李芳菲多了一個小15歲的弟弟。
父親常年在外,是媽媽一個人負擔起全部的撫養任務——下班之後接小孩、接完小孩做飯、吃完飯送興趣班、做家務、陪玩、輔導作業、哄睡,“之後,才能做自己的事情。”有一次,她半夜起床,發現弟弟發了高燒。她陪着媽媽去醫院,忙活下來已是淩晨4點。媽媽一夜未睡,第二天仍舊準時上班。
她目睹了這份艱辛,更加疑惑,“父母這一輩對于孩子的執着,和現在年輕人不願意生的沖突或者悖論,背後的社會因素到底是什麼?”
和她一樣,黃一鳴也試圖厘清,應該如何了解爸爸想生二胎的想法?出于自身困惑,兩人加入了生育意願調查的研究,試圖尋找答案。
一代人的理想和現實
楊妍是這個研究的發起者,也是一個00後。2021年12月,她偶然看到人口學家穆光宗的兩篇論文,才發現,中國的生育率一直在走低、育齡女性生育率一直在下降,“真的步入了一個少子化的社會。”
某一天,她看到一則新聞。婚禮上,新娘高高地把捧花扔向未婚的女性來賓,出乎意料的是,人人躲閃,沒有一個人願意接,“為什麼尤其我們00後,不生會成為一個趨勢?”
在此之前,她從未關注過生育話題。楊妍22歲,留着一頭長卷發,在同齡人眼中,做事負責,有拼勁,很多加入生育調查的人都說,是出于對她的信任。在爸媽眼裡,她是一個乖孩子,成績出色,懂事。問起未來打算生幾個孩子,她會說,“一男一女,湊個好字。”一個令人欣慰的答案。
楊妍的世界純粹、完美。她是家裡唯一的孩子,承擔着父母望女成龍的期盼。因為是最小的孫女,也沒體會到爺爺奶奶重男輕女的對待。
但是平順的表象下仍舊隐藏着“不對勁”的細節。在把人口當成勞動力的遙遠時代,遠在安徽山村的奶奶,生下了4個男孩。6歲,她跟着父母來到杭州,高中買房前,一家三口租一室一廳的房子,她睡小床,爸媽睡大床。同學過來瞪大了眼睛,“你家怎麼這樣?”
逼仄的、不屬于自己的空間,也是楊妍對杭州的印象。“小時候我挺叛逆的,到了杭州之後,變得很乖,也很卷。”随着她長大,天平的另一端,已是父母所能給出的最大砝碼。每當爸媽調侃想不想要一個弟弟妹妹時,她都會回一句,“你們養得起嗎?”
走進一段親密關系也很難。她不排斥戀愛,但周圍好友經曆的吵架、冷暴力,會讓她一再提高标準。“婚戀難是一個普遍現象。”她看到穆光宗在論文中提到,“社會轉型導緻生育成本急劇升高,養兒防老的實際作用被削弱,都導緻了‘生育恐懼’的出現。”
完美世界的殼被敲碎了,那些“不對勁”的細節全都裸露了出來,她窺見了社會更為現實的樣貌。
●楊妍在做訪談。講述者供圖
導師鼓勵她去做一個調查。原因很簡單,出于競賽、成績的需要,學院會給每個同學一個科研的機會。在正式報名科研項目之前,楊妍找了6位研究所學生學姐,做了初步訪談。
那是第一次,她發現周圍有這麼多不婚族、不生族。6個學姐中,有3人不想談戀愛,1人可談可不談。3人不想結婚,剩下3人,也隻說“發自内心想結婚再結”、“沒遇到合适的可以不結”。提到生育,有人說,“結婚是願意的,但生孩子就不大願意。”
她又找了幾個上班族。上海一家外企的學姐告訴她,“來上海的人基本上是來打拼的,社會關系鍊條比較脆弱,會更注重個人事業的發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有了房子之後,再去結婚。”
也有一些人,困囿于生與不生、結與不結的難題。她記得,一位在英國讀人類學的學姐,是大家公認的“獨立女性”,身材健美,一個人去倫敦、巴黎旅行,在朋友圈,也會發表一些女性主義的見解。
訪談中,她堅持不婚主義,認為“将生殖行為社會化,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以來形成的,以性為中心的知識與權力的特定機制”。但在訪談時,她又寫下,“我還是挺适合結婚的,受母親的影響,我其實是一個比較願意為家庭操心的人,願意進行一些體力勞動,甚至做好了成為全職太太的準備。但另一方面又始終會想要保持獨立女性不斷Lean In的願望,是以浸泡在沖突與兩難之間。”
這種沖突感,楊妍了解為是這一代人的“理想和現實”:理想上,希望一切都自己做主,有堅定的觀念選擇;現實中,卻掙紮在對傳統的、家庭的妥協之中。而這個學姐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在逃離自己傳統的那部分。
那段時間,她有些許的動搖,“是不是現在社會普遍的情況是這樣子?”反而那個想生的自己,成為了社會中的少數?
跨越階級的向往,與重男輕女并存
在這群年輕人面前,現實的一隅被一點一點地掀開了。自2022年4月開始,陸續有8人參與進了這項調查。他們收集了1500份問卷,訪談了80多人,試圖了解年輕人為什麼不生育。也走訪了家鄉的社群、街道、醫院、幼稚園,了解機構如何面對低生育的現實。
一位杭州工作的31歲男性提到,在買房的焦慮面前,孩子仿佛一個提速器。訪談時,他妻子已懷孕近4個月。原本,夫妻二人計劃結婚後,雙方一起奮鬥,積攢積蓄後,再找個好房子。但孩子隻能等10個月,房子成了10個月内就要解決的事兒,接下來,教育訓練班、輔導課,一系列的開銷也會蜂擁而至。
“孩子生下來沒幾個月,就要上思維課、邏輯課,動辄上萬,還要上好幾年的教育訓練班,和結婚的時候相比,天差地别。”男人說。
生了孩子,意味着同時要做“房奴”、“車奴”,最根本的還是“孩奴”。問卷中,有812份資料表明,近70%的人,将經濟與居住條件、養育孩子的費用,視為影響生育的第一、二要素。
不過,在養育成本這座大山下,問卷也反映出對待生育的性别差異。願意30歲之後結婚的女性,比男性高出6個百分點;在生育面前,女性對身體狀況的考慮,也比男性高出20個百分點。
“一開始,我設想的是,大家不願意生小孩,應該是經濟方面承受不起。”楊妍說,“但後來慢慢會發現,女性考慮的是職場、事業上,權益如何保障的問題,以及家庭養育的問題,而男性則更多考慮學區房、托育的費用這些經濟壓力。”
她接觸到一位二胎媽媽,覺得婚姻很不符合自己的預期——在孩子的養育上,丈夫沒有分擔一分,而自己要一邊帶娃一邊工作,“帶孩子累,教育孩子也累,養家養孩子又花錢。”
有了孩子以後,在職場與家庭的權衡中,許多女性選擇了家庭。一位在投行工作的職場女性,生了二胎之後,辭職做了全職媽媽。最初的四年裡,她陷在退出職場與整日“雞娃”的落差中,孩子成績不好成了她最大的困頓,之後,她開始投向心理學,寄希望于此,能讓自己接受不再成功的現實。
即使孩子長大,女性得以重回職場,她們也會發現,世界完全變了。一位36歲的二胎媽媽,為了生老二,去做了保育員。她覺得做全職媽媽是一件很無聊、沮喪的事,想回去工作。老二7歲後,她做了一名幼師,因為教育孩子是目前唯一擅長的事。她的父親對此感到不滿,“好不容易大學畢業了,卻去做一個幼稚園的阿姨,而女婿(她的丈夫)卻是西裝革履。”
累、與社會脫軌、圍着孩子轉……經曆這些的人,都不希望再生一個。一位80後爸爸總結,現在的生育趨勢是“在精不在多”。以他自己為例,獨生子女會希望孩子還是要有個伴兒,一個不行,兩個就正好,生三胎的話,“吃不消這個生活”。他繼承家族企業,金錢不是問題,有資本生兩個孩子,但也逐漸感覺到吃力,因為要買學區房,盡管對杭州的應試教育不滿,他還是從上海搬到了杭州。
●團隊小組讨論。講述者供圖
一線城市不适合養孩子,更不适合生孩子。壓力早在生育之前就壘在年輕人身上。
楊妍的一位學姐,在北京做傳媒工作,朋友圈中時常可見與明星的合影。她并不排斥生育,也喜愛孩子的陪伴,在她的暢想中,至少要有兩個孩子,理想的生育年齡是32歲。但如今,她已33歲,還是覺得工作不穩定,還有身材和容貌焦慮,一再推遲生育。“生孩子回來,也許這個崗位在不在都是個問題。”
與大城市不同,在縣城,生育本身成為了一項拼搏的事業。26歲考到金華的公務員,一畢業就結婚生子了,她對自己的現狀很滿意。一位受訪者提到自己在邊遠地區感受到的震撼,“一生生五六個孩子,太羨慕了,我自己生一個已經很不快樂了,他們那麼多照樣生。”
為什麼那些地方,他們會生好多個孩子,但是在大城市,大家反而不願意生?楊妍在訪談了20多個人後試着去解釋背後的社會圖景——
“大城市人有非常高的向上去跨越階級的想法,婚姻和生育變成了阻礙。而城鎮中人,家庭就是他人生當中最大的一份事業。生育的背後,是結構性問題的折射。”楊妍說,橫向上看,城鄉流動,造成了生育觀的迥異;縱向上看,生育政策的轉變,也導緻了代際生育觀的沖突。
李芳菲的大姨是一個很好的樣本。她60多歲,是農村戶口,計劃生育時期,可以生“一胎半”(農村第一孩為女性的農戶,在間隔4到5年後允許生育二胎)。生了一個女兒後,再生一個,還是女兒。她不死心,偷偷懷了第三胎,躲到了鄉下,卻還是被超生隊抓到,送到醫院打掉了。
那一胎是男是女,大姨并不知道。但生兒子的念頭,成為一個未完成的執念,困擾着她幾十年——直到兩個女兒也步入生育年齡。
一個女兒頭胎就生了兒子,“已經生兒子了,那也不強求她生了,再生一個是更好。”一個女兒生了女兒,“那就得再生一個兒子出來。”
這個女兒與母親的沖突就在于此。因為知道兄弟姐妹的依靠、陪伴,她不排斥二胎的想法,但她抗拒母親對男孩的執念,“我是女孩兒,我生的也是女孩兒怎麼了?”
李芳菲此前從未想過,“這都21世紀了,還有重男輕女的問題。”關鍵是,還發生在自己的周圍。進行了為期一年的調研之後,團隊的成員都覺得,“生育指向的,好像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的、更深層次的問題。”
看見自己的附近
一開始接觸這群00後,我很難将其定義為一項“規範”的社會學研究。看起來,這就像是一群年輕人憑借着某種源生性的沖動,花了一年時間,采訪了很多身邊的人,僅此而已。沒有研究問題,沒有理論對話。
但那些訪談的學姐、老鄉、大姨,讓我想起項飙提到的小區保安、菜場商販、快遞小哥。這些身邊“最熟悉的陌生人”,似乎讓這群生活在網絡世界的新世代,接觸到了一個新的“附近”。
生育可能是人們最習以為常的事情。但李芳菲試圖記錄下身邊的草蛇灰線。
那是今年寒假,她的調查到了收尾階段。在鄉下一個熱鬧的集市中,她擡起頭,看到一塊紅色的牌子,角落卷曲、落滿灰塵,鑲嵌在一座破舊的“小洋房”二樓,寫着:“計劃生育,丈夫有責。”落款是鄉人民政府。
時代的烙印镌刻在每個人的周圍——就是這塊牌子所代表的時代,造就了她的大姨,連及了她的女兒,影響了幾代人的生育觀。李芳菲把它拍了下來。
●講述者供圖
調研之後,李芳菲對這些有了更為敏銳的觸角。“簡單來說,原來腦子裡很抽象的問題,變成了更加具體的執行個體。”
調研團隊中,有一個溫州女孩王染,也在“生男生女都一樣”的智語底下長大。這些智語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她的性别觀,“女孩子哪裡沒有男孩子好?”她周圍有許多“姐弟”組合,包括她自己。父母給出的理由總是,“一男一女,湊個好字”。
這次調研,一個女同學向她傾訴,弟弟成績不好,父母會花錢給他上一個好大學,弟弟也心安理得接受一切,而自己想要出國留學,就會對父母産生虧欠感。同校時,她們不會聊起這些,但這次訪談,讓她意識到,那些“姐弟”組合,就是性别偏見的結果。她媽媽的朋友,生了一個兒子就覺得“任務完成了”。與之相對,生了一個女兒的舅媽,47歲了,還會被親戚念叨再生一個兒子。
從前,她是一天裡有大半天泡在網上的人,許多概念、觀點,都經由網絡建構。周圍的人與事,像蒙了一層迷霧。“我們這一代對生育、婚姻,會更恐慌。”但這次調研,如同在家鄉的航道中投擲了一個浮标,讓王染對這個地方有了真切的思考——“為什麼溫州重男輕女的觀念,比别的地方要嚴重?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大家産生這樣的想法?”
這種“觸摸”到真實可感世界的感覺,對楊妍來說,則是“理論照進現實”。她告訴我,調研後,她結識了自己小區裡的一些二胎、三胎家庭。有一個父母的好友,2008年,他們生了二胎,是女兒,2012年交了2萬罰金,又生了一個,才是兒子。
媽媽跟她說,這家人一直都想要一個男孩。她想起自己查找資料時發現的資料,三胎往往是性别最為失衡的一胎,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三胎性别比為132.9,而國際公認合理的性别比為103-107。她了解了三胎的選擇,但也無奈于這樣的現實。
李芳菲們也在拓寬“附近”的廣度。社群、醫院、幼稚園甚至中學告訴她們,低生育率背後,是一個努力調試的社會。溫州本地婦保、兒保醫院的醫生感受到,相比全面二胎,三胎開放之後,自己的工作反而閑了下來。為了提高競争力,這些醫院更換了沙發、裝修了病房、改善了生産流程。但仍舊無法避免人口減少的趨勢。
給自己國中的學弟做家教時,楊妍才知道,由于生源不夠,下一屆,這所國中就要砍掉3個班級。為了流通生源,當地的中考也不再劃分片區。
不隻是機構在做這些努力,一個社群的全職媽媽成立了一個“全職媽媽讀書會”,互相讀道德經,借此傾吐生活的苦悶。楊妍訪談的那天,一個40多歲的媽媽,剛因孩子教育的問題,跟丈夫大吵了一架。分享時,她無法平複自己的心情,流下了眼淚。楊妍發現,其他媽媽仍舊在很認真地聽,時不時拍一下她的肩膀,等她分享完了,再給她出了點主意。她在這十多位全職媽媽身上,感受到個體與個體之間親近的、具體的交流。
楊妍覺得,這種感覺甚至久違了。“現在,我們習慣通過網際網路、社交媒體與遠方産生連接配接,而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情感交流,常常被忽視了。”
●社群組織的全職媽媽讀書會。講述者供圖
00後的反擊
一台錄影機架在了李芳菲和她媽媽之間,訪談開始了。媽媽的眼神有點閃躲,李芳菲的心裡也挺微妙。屋外的天非常非常熱,辦公室裡,除了兩個人的談話聲,隻剩下空調發出的聲響。
這場訪談,李媽媽是被拉來“湊數”的。由于需要許多樣本,李芳菲首先想到的就是從身邊入手。生活中,媽媽并不壓抑自己的情緒,每天和外地的丈夫通一次電話,都要訴訴苦,講講委屈。她生李芳菲時,順産順不下來,又轉了剖腹産,想到那種滋味,有時還會掉眼淚。
李芳菲上高中時,媽媽就給她上過性教育課,和媽媽讨論戀愛、性、生育,就像聊天氣一樣日常。她以為,這次不過是一場有錄影機“監督”的聊天而已。事實和自己預想的也差不多,但在最後,當問到,你對你子女未來生育有什麼看法時,李媽媽的回答是:我希望,你以後找老公一定要找能夠在身邊的,能夠參與到家庭的付出的,不要找像你爸這種天天出差,一年四季不到家的。
那可能是第一次,她捕捉到了媽媽的一絲後悔。“原來媽媽也有意識到生育中的不平等。”在以前的交流中,兩人常因生育觀争吵,李芳菲表示不生孩子、想30歲之後結婚,李媽媽都會極力反對。但這次訪談之後,媽媽再和人聊起天,會很平靜地表示,我女兒以後想30結婚,35生小孩。在“晚婚晚育”上,母女倆擁有了一點默契。
如今,生育意願的調研周期已經結束。相比起一年前,幾乎所有人都覺得,生育是一件更需要慎重對待的事情。“很少有人可以決定我就不要孩子,一輩子一個人,這也需要莫大的勇氣和精神世界。能真正做出這個決定是挺酷的。”
這一年來,爸爸的那句“想不想生一個妹妹”,一直環繞在黃一鳴的心裡。自己真有一個妹妹會怎樣?四個人的家庭,會不會比現在熱鬧一些?訪談二胎、三胎家庭的時候,他總是經不住這樣設想。
今年春節,在一個看似随意的時機,他和爸爸重新提起了生妹妹的那個念頭。爸爸解釋,這個念頭的産生,是想彌補自己對兒子教育的強硬。他想起自己考察家鄉的政策,問爸爸,“你知道有男性育兒假嗎?”調研時,他發現,雖然存在這種育兒假,但并不會有人使用這個假期,甚至也從未聽說過。
“生育不是單方面的事情,是男女雙方的事情。”黃一鳴說,“你不能從自己的角度考慮問題。”
當聽到爸爸說“是我考慮的太理想化了”的時候,他意識到,父親終于不再認為生孩子是一件随意的事情了。
不過,也有家長沒有妥協。感覺到具體而實在的生育壓力之後,楊妍把自己的“一男一女”改成了“隻生一個”。聽到這裡,楊媽媽吓了一跳,“我看你們就是太懶了。”女兒第一次變得不乖了。甚至某天,楊媽媽和女兒在陽台晾衣服,提到杭州三胎獎勵2萬元,女兒突然激動地嚷嚷,“生孩子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在文化層面已經成了一種風氣,獎金能解決什麼……”
覺得煩了,楊媽媽下了定論,轉身離開:“我看你是讀書讀傻了。”
(應講述者要求,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版權聲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權歸屬極晝工作室,未經書面許可,不得轉載、摘編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聲明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