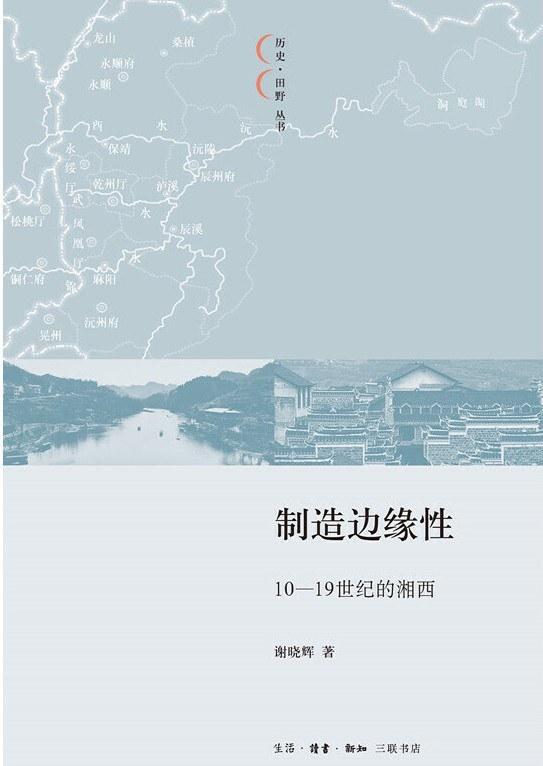
《制造邊緣性:10-19世紀的湘西》,謝曉輝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6月出版,257頁,68.00元
傳統“湘西”的曆史坐标
對湘西曆史的好書我總是特别留意,既因我是學曆史的湘西人,也因自己曾經立志卻沒有實作的研究西南民族史的初心。近年來,很欣喜地看到,在西南研究熱潮帶動下關于湘西曆史的好書好文越來越多,但一字不落地讀完的隻有謝曉輝博士的《制造邊緣性:10-19世紀的湘西》(以下簡稱《制造邊緣性》)。
這本書首先吸引我的是其對湘西曆史的定位,即“西南傳統”中的“湘西”和土苗共生的湘西。對傳統“湘西”的曆史坐标的定位,作者的把握宏闊而準确。盡管對湘西曆史的專題研究不乏精深的佳作,我還是覺得對湘西有整體和透徹了解的無過沈從文。雖然他以文學的眼睛看湘西,但與曆史學者們觀察的對象是同一個湘西。沈從文曾說他的寫作與水不能分開,他筆下的湘西沿着“水”——辰河(沅水)及其支流白河(酉水)而展開,關注沿河的碼頭及水上和岸上的各色人等。他也曾說自己和黃永玉是遊離于家鄉鳳凰“共同趨勢”以外的“衍化物”。這個共同趨勢就是從苗防衍生的武勝于文的地方好尚。這也使得沈從文書寫的那個時代,即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鳳凰和“筸軍”站在了湘西與外部世界互動的最前沿。而之前這個角色屬于酉水流域的永順土司和保靖土司。
不深入酉水流域社會,就不能了解湘西彭氏集團何以能在中原王朝的卧榻之側割據八百年,不關注邊牆之内外的苗疆,就不能了解鳳凰及其“共同趨勢”何以平地産生。沈從文關注的水(沅水、酉水)和苗防(實即土、客、苗的互動)正是了解湘西曆史最核心的兩個因素。沈從文談及的三四十年代,不論湘西人的自我意識,還是内地人對湘西的認知,都還帶着“邊鄙之地”的定位,即使向雲貴川大轉移時,各類人等由湘西轉向西南,對途經的湘西仍懷着某種“誤解”和“戒備”,而湘西地方勢力正縱橫捭阖地緻力于維持自己的“割據”。
沈從文書寫的是其所處時代的湘西“當代”史,在他的“湘西”裡,曾經扮演曆史主角的永順已經成為“湘西”的邊緣,而土苗互動的鳳凰,或更大點說是“三廳”(即清朝改土歸流後在苗疆設定的鳳凰、乾州、永綏三個直隸廳)來到前台,而不變的是揮之不去的湘西的“邊緣性”。這既是湘西傳統的衍變,也是湘西曆史的結果。這個格局不僅延續到沈從文的時代,眼下也似乎某種程度地在延續。而這個既有格局的生成原因需要到曆史長河中去探尋。
《制造邊緣性》選擇十世紀溪州之戰為追溯的起點,梳理了降至十九世紀湘西地區與王朝國家的互動方式、區域社會内部的構成和運作形态。該書所要揭示的不是單向的王朝國家對湘西的拓殖史,或湘西地區華夏化的曆程,而是王朝國家、有君長的土司政權、無君長的苗疆勢力之間的幹預與能動,擴張與因應。沒有一方是簡單的設計者或被安排者,曆史正是在各方的拓展、逃避與自存的互動中演進。
湘西曆史的十世紀轉折
改土歸流是湘西曆史最重要的轉折,追溯改流産生的源起,則是發生于《制造邊緣性》起論的十世紀的曆史轉折。漢代以降,西南各族與王朝國家互動并行着兩條線索。一是羁縻體系,“因其故俗治”,從西漢賜封王侯,到唐宋設定羁縻州。二是直轄郡縣體系,即西漢的“初郡”到唐朝直轄州,流官掌治郡,駐軍隊,興屯田,通道路,置郵亭。湘西地區設定直轄郡縣的具體形态因裡耶秦簡的發現,可以追溯到秦代,而内地勢力的進入則更早。深入西南腹地的直轄郡縣對蠻區的實際控制是有限的,但發揮了宣示王朝國家的存在、抑制地方勢力、傳播華夏文化等多方面的作用。不論是漢族姓氏、家族意識,還是地方政治體的制度設計,都日益顯現潛移默化卻十分深刻的影響。
從王朝政策而言,宋代呈現重大的轉向,即宋王朝全面放棄漢唐時期在西南腹地設定直轄郡縣的傳統,雖然這一轉向是對唐末五代既有格局的延續,但明确為王朝的基本政策,與漢唐經營西南的政策表現出重大的變化。這一轉向在湘西地區得到明确的展現。從秦代設遷陵縣到唐代的溪州,酉水流域一直延續着直轄郡縣的傳統。唐代的溪州轄大鄉、三亭兩縣,“編戶”曾有兩千一百八十四戶、一萬五千二百八十二口,繳兩稅,納土貢,有完備的統治體系。這些郡縣控制的範圍和程度應是十分有限,從漢代到唐代都可見蠻人不斷的反叛,“溪州賊帥向子琪連結夷獠,控據山洞,衆号七八千”,從叛亂武裝的規模可知溪州地區“夷獠”的人數當不小于“編戶”。這些編民也并非完全逆來順受,他們曾向黔中觀察使訴告溪州刺史魏從琚于兩稅外,每年擅自加征朱砂和水銀。
十世紀初,溪州彭氏及其他當地豪酋的割據自署中斷了直轄郡縣的曆史,建立了自治的地方政治體。秦代至唐朝直轄郡縣傳統不隻是宣示王朝國家在湘西腹地的存在,而且成為彭氏建構其地方政治體和社會文化的重要模式來源。首先,唐代溪州及其所轄大鄉、三亭的設定成為彭氏塑造其合法性的手段,彭士愁使用了溪州刺史的身份。其次,借用郡縣制建構其統治體系,稱“當州大鄉、三亭兩縣”,任命部下首領為刺史、知州、縣令等。再次,建立賦役制度,以團保組織群眾,征收賦稅,“複溪州銅柱記”所稱“歸順之後,請隻依舊額供輸”之“舊額”當指唐代稅額。而蠻酋使用漢姓漢名則早見于唐代以前。
彭士愁自立,并在溪州之戰中取得馬楚政權的承認,成為溪州地方曆史的轉折和分野。溪州通過盟約得到的“本州賦租,自為供養贍。本都兵士,亦不抽差”的自治地位在宋代西南政策下得到鞏固。宋王朝放棄了漢唐在西南腹地設定的直轄郡縣,幾乎全面退出對西南“蠻夷”地區的直接經營。這一秦漢以來中原王朝西南政策的重要轉向在溪州得到典型的展現。盡管宋朝通過武力征讨、築城設寨挾制溪州彭氏,但在西南政策的大背景下,彭氏仍得以延續其自治狀态。元及明清實行土司制,與宋代自署屬官不同,王朝不僅配置流官,還直接幹預土司之下長官司的任免,但直到雍正初年實行改土歸流,溪州地區自治的格局仍得以維持。
因而,要回答《制造邊緣性》開篇提出的問題:“湘西地處中國腹地,與中原互動了上千年,為何直到清朝才系統設立州縣、建立王朝國家的直接統治秩序?為何直到民國,位于南部的苗區還跟邊牆、邊政、邊城這一類詞語挂鈎?”“其曆史過程與機制何在?”即要揭示近代湘西格局何以形成,則必須以彭氏自立的十世紀為追溯的重要源頭。這既因溪州彭氏政權八百年割據延續了一個完整的曆史階段,也因永、保土司作為湘西最強大的軍政力量,自明代便令分别擔承,“永順限制鎮苗,保靖限制筸苗”,有力地影響着苗疆事務。而這又成為雍正改土歸流後湘西地區管理方式和社會形态格局的曆史慣性。從十世紀彭氏勢力崛起的節點上前後瞻望,都可看到湘西與西南區域整體曆史演進的同頻脈動。
湘西鳳凰
“西南傳統”中的湘西
《制造邊緣性》所緻力闡釋的是“西南傳統”中的湘西。作者通過湘西這一“個案”讨論了“西南傳統”的内涵及其整合入大一統中國的方式。湘西的“西南傳統”首先是其西南區域共有的地理環境,即曆代所稱的“溪峒”所賦予的。湘西地處雲貴高原的邊緣,武陵山區的“溪山阻絕”既成為王朝進入湘西的“地形阻力”,也為雙方的溝通提供了通道。直到明清,自中原進入湘西北永保土司區的主要通道是酉水,進入湘西南苗疆的主要通道是武水。永保土司的統治區域正是酉水及其支流覆寫的、自成單元的地理環境。而溯沅水入武水,可以深入苗疆腹地。辰州扼守着兩條“諸蠻咽喉出沒之地”,“諸蠻不由此,則商販不通,武陵不得此,則諸蠻不通”,頗似陶淵明的桃花源。而苗疆進入“生苗”積聚的臘爾山則是“溪峒”之“溪峒”。如《制造邊緣性》所揭示的,王朝國家進入這個湘西腹地需要面對地理環境和“蠻夷”勢力的阻力,但另一方面,以酉水、武水為主要通道,湘西地方又與王朝國家展開互相間的物資、人員和文化出入互動。
西南“溪峒”環境不同的生态衍生了不同的生計方式。《制造邊緣性》将其歸納為兩種類型,即“各有君長”和“無君長不相統屬”兩種土著社會。在上千年的曆史長河中,西南區域内兩大土著社會在“共生生态與多邊互動”中,經營邊緣性,展開與王朝國家的互動,“它不僅決定了曆代中原王朝與其互動、管理的基本政策與制度,也深刻影響了西南地方社會的模塑及其整合入大一統中國的程序和模式”。作者提出“西南傳統”,并揭示了“西南傳統”上述核心内涵。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需要闡釋的重要問題。探索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需要更深入地認識西南區域曆史自身的軌迹和特點,在草原、西南、西域等不同區域曆史比較中了解中華民族曆史的整體性與多樣性。
兩大土著社會類型的構成和互動構成了《制造邊緣性》論述的十到十九世紀湘西曆史的基本架構。兩大土著社會類型在湘西的表現就是永保土司區和苗疆社會,使得湘西北和湘西南表現出不同的發展路徑。永順和保靖兩大土司建立了從土司、到長官司、到旗(村寨)的統治體系,有完備的賦稅和兵役征調制度。永保土司也與王朝國家有制度化的互動機制,即土司任免、戶籍申報、土兵征調、資源擷取等穩定制度。永保土司對内部有較強的統合力,從永保土司的土兵征集能力和土兵的戰鬥力即可窺見。而苗疆則沒有建立起這樣系統化的社會組織架構,王朝國家與其也無法建立如永保土司區那樣的互動關系。
兩大類型的差異也決定了改土歸流後,清王朝處理湘西北和湘西南的政策上表現出兩種不同的開發和治理模式。清王朝在永保土司區廢除大土司,實行直轄的郡縣制度,将其原有的基層組織“旗”以新瓶舊酒的方式整合到基層體制之中,土司區的“土蠻”通過戶籍和地權登記進入編戶齊民的體系。而湘西南的“苗蠻”并未獲得“編民”身份,亦未進行土地登記,其地權未獲得承認,而以“人丁”為征稅依據。乾嘉起義後仍是以屯田制度這一國有制度配置設定苗疆土地。而行政管理則以百戶、屯長等代理,采取重修邊牆的“苗防”政策,法律施用也保持“苗例”的特殊性。如作者所論,在清代的苗疆開發過程中,酉水流域的永保土司區從核心區域中退去,逐漸成為苗疆的“邊緣”。
湘西的“西南”屬性還展現在王朝國家的西南戰略格局考慮中。元代重新在西南腹地建立直轄郡縣,明清繼承元代的趨勢,不斷強化對西南區域的治理。雲貴大通道成為王朝控制西南的命脈,而沅水及其支流穿過的湘西地區成為保障雲貴大通道必須着力治理的地區。考慮到統治成本,王朝國家選擇了不同于内地的土司制度,一方面與宋代羁縻制度相比強化了對土司的控制,另一方面以永保土司擔承苗防。這樣的互動方式既是王朝國家處理西南問題的基本方式,也展現出湘西與整個西南内在的共性。
合力制造的“邊緣性”
沈從文所觀察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湘西仍然被視為“邊鄙之地”,湘西的内部仍在努力地維持自己的“邊緣性”。如《制造邊緣性》所指出的,西南邊疆的曆史并不是單向的王朝國家開拓史,或“走入内地”的曆史,而伴随着多方對“邊緣性”的制造和維持,王朝國家對湘西的經營也并非僅以使其内地化、華夏化、實作一體為目标。
從王朝國家而言,應對湘西地形阻力和多種勢力構成的複雜局面的統治成本,是一定程度維持其邊緣性的動機。明代為了保障雲貴大通道和實作對湘西地區的控制,建立了衛所體系,甚至深入永順土司腹地建立了羊峰衛和崇山衛,在苗疆腹地設定鎮溪所,駐屯正常漢軍,并編訂裡甲,化土著為編民,使湘西分别處在土司、州縣與衛所、生苗多種體系之下。但是,裡甲之民和衛所之兵大量逃離,州縣與衛所體系難以為繼。州縣财政困窘、衛所廢弛,使官府弱、土著強的格局日益突出。明朝廷不得不選擇利用土司力量控制苗疆。官府所設堡哨的兵力與明初的衛所漢軍大異,其主力已逐漸改為土官土民。嘉靖年間又約定了永順土司和保靖土司分别擔承鎮溪所土巡檢、五寨和筸子坪長官司治下村寨和苗寨安靖。羊峰衛和崇山衛也因道路險遠,運糧不繼,最終或遷或廢,鎮溪所在明中葉以後基本上為土著首領所把持。
明中葉作為甯靖苗疆的措施,修築邊牆,清代繼之,乾隆時期再修邊牆,已将其作為區隔土民、熟苗與“化外”生苗的界限,跟王朝關系較為密切并獲得王朝認同的土官部下的土人、熟苗有權駐紮在邊牆之内,被排斥于邊牆之外的生苗成為不被保護和防禦的對象。客觀上,邊牆成為王朝區分内與外、民與苗,固化土著不同身份的手段。如果說,王朝對永保土司的利用和倚重,鞏固了其地位延續的合法性,保持了與“内地化”相背的邊緣性,邊牆修築及其對土著身份的劃分則是對民、土、苗人群構成中制造出邊緣之邊緣。總體上都并非以一體化為必然目标,而制造着不同程度的邊緣性。
湘西邊緣性的塑造還來自于湘西社會内部的能動性。大小土司利用王朝在苗防上對其的倚重,一方面維持其強有力的武力,頻繁應調出征,在安撫苗疆中發揮不可取代的作用,另一方面有意維持着苗疆的不安及其與王朝的離異。平苗既成為土司延續的合法性,也成為其增強軍事和經濟實力的途徑。永保土兵應調的“月例”較兩廣土兵高出一倍有餘,而土司對其臣民按“旗”征兵時應征者卻自備器糧。朝廷的征調成為土司營利的途徑,不僅樂于應調,而且設法多出兵力。而“苗亂”的存在即其利源。如明朝官僚指出的“土官高坐營中,計日得銀,隻願賊在,豈肯滅賊”。甚至出現苗疆奸人擄略人口賣與土官,割首級以邀賞,土司以“窩苗”,維持“亂苗”為利。
不論土司,還是苗疆,都努力維持自身傳統。土司使用漢姓漢名,攀附家族曆史,纂修族譜,建立祠堂,甚至延請漢人儒士,傳習詩文。特别是永順土司修撰了《永順宣慰司曆代稽勳傳》和《永順宣慰司志》,修建了湘西第一所學校——若雲書院。這些既是土司介入王朝體系的途徑,也是增強自身實力和影響的手段。土司間還通過聯姻和結盟,彼此支撐,鞏固既有的格局和地位。土司區還通過幾乎遍布土民村寨的土王祭祀宣示土王的正統和權威,塑造土王與土民的權力結構和君臣秩序。苗疆廣泛傳播的白帝天王土著信仰也具有強化苗疆社會整合和認同的意義,而且獲得了王朝的敕封,展現了國家與地方彼此的認同與妥協。湘西的“邊緣性”并非僅因其地理環境的邊緣或行政疆域的邊緣,而是王朝、土司、苗疆不同勢力在特定曆史時期合力制造的結果。
永順不二門發掘的商周文化和保靖四方城的漢代墓葬文化,都與江漢洞庭湖區文化無同質關系,而與西南地區屬同一體系,顯示着湘西地區自古的西南屬性。《制造邊緣性》揭示了湘西西南屬性的延續、衍變及固化。“西南傳統”是湘西曆史的和自然的屬性。王朝國家在一定曆史時期維持湘西邊緣性的同時,也日益強勁地牽引着湘西走向“内地”。元明清湘西在行政區劃上歸屬于湖廣行省、湖廣布政司和湖南省,王朝國家通過省級行政的湖廣或湖南實施對湘西不斷強化的管理,湘西作為“湖南一個機關”的行政屬性日趨明顯。正如《制造邊緣性》的旨趣,即探尋“西南傳統”與中國社會的整合,政治、經濟和文化整合累層地推進,正是沈從文所說“使湘西成為中國的湘西”的過程。
《制造邊緣性》揭示的議題還有廣闊的讨論空間,書中有的論述也可再加完善和充實。作者通過對“複溪州銅柱記”“盤瓠遺風”一語及彭氏為會盟一方推斷溪州彭氏集團為盤瓠蠻,需要明确彭氏集團作為土家族先民這一民族屬性,與土家族族源已有研究進行應有的學術對話;自秦到唐,王朝國家一直延續着在湘西地區的直轄郡縣傳統,這一傳統對十世紀以後的湘西社會産生了深刻影響,該書未能充分重視和揭示;該書因揭示“制造邊緣性”這一旨趣,主要着眼于政治角力,正如作者在書中表達的對湘西地區的社會、經濟和文化運作機制可作更為深層的探索。諸如此類,還可以展開更多重要的議題。我們期待作者對湘西曆史更為豐滿和深入的研究成果,展現傳統時期湘西社會經濟更具體的形态及其演進軌迹,揭示不僅是“西南傳統”中的湘西,也是“西南傳統”寓含的多樣性中特殊的湘西。結果必如沈從文所說:“這是可能的嗎?”“不,這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