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Philosophia 哲學社
哲學園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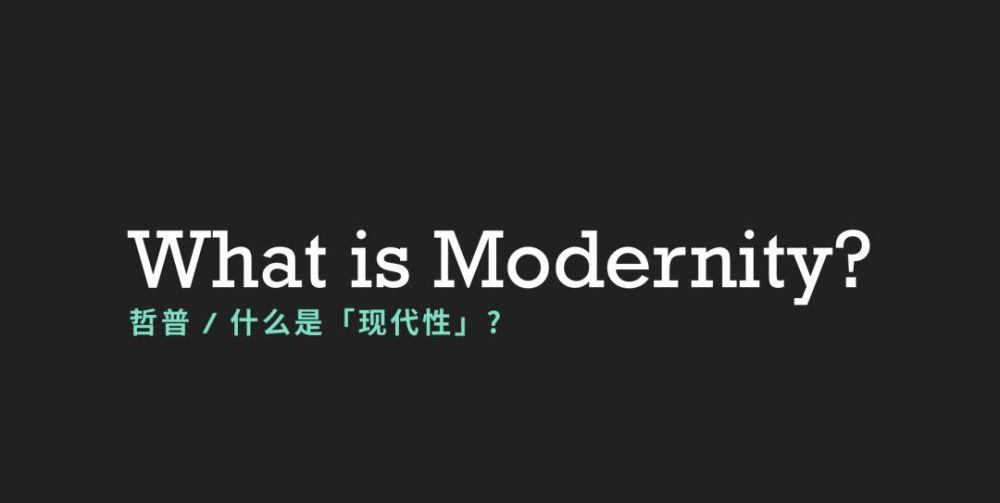
「現代性」是一個在哲學、社會學甚至文學、藝術等領域都被廣泛使用的一個詞語。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就現代性話語而言,從18世紀後期開始,它「就已成了哲學讨論的主題」。但即使是這樣一個重要的詞,當我們在 Merriam Webster 上查詢它對應的英文名字 "Modernity" 的時候,仍然會發現這樣語焉不詳的解釋:
1. The quality or state of being or appearing to be modern;
2. The modern era or world and especially the ideas and attitudes associated with the modern world.
是以這篇文章要做的,便是簡要介紹「現代性」的定義、來源、及其蘊含的核心價值。本文大部分内容整理自陳嘉明教授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十五講》一書。此書通俗易懂、深入淺出,強烈推薦讀者們前去購買。
/ 定義
在現今我們所知道的有關現代性概念的界說中,比較著名的有如下三個。
一是吉登斯将現代性看作是現代社會或工業文明的縮略語,它包括從世界觀(對人與世界的關系的态度)、經濟制度(工業生産與市場經濟)到政治制度(民族國家和民主)的一套架構。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性大緻等同于「工業化的世界」與「資本主義」,包括其競争性的産品市場和勞動力的商品化過程中的商品生産體系。現代性與傳統的差別,在吉登斯那裡根本在于一種制度性、文化與生活方式等方面發生的秩序的改變。它具體表現為兩個突出的結果:一是對于社會而言,它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會聯系方式的「全球化」;二是對于個人而言,它确立了西方的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即以自我實作為核心的「我該如何生活」的思考與追求。
二是哈貝馬斯把現代性視為一項「未完成的設計」,它旨在用新的模式和标準來取代中世紀已經分崩離析的模式和标準,來建構一種新的社會知識和時代,其中個人自由構成現代性的時代特征,主體性原則構成現代性的自我确證的原則。在哈貝馬斯看來,現代性的一個最為核心的問題,就是它的自我了解與自我确證的問題。對于中世紀社會來說,并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因為在一個神權的社會裡,宗教意識形态已經提供了有關的答案。而自啟蒙運動以來,當人們試圖建立一種新的社會與文化的時候,這種以自由等天生不可剝奪的權利為核心的價值系統,以及相應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安排,随着價值來源根據的轉換,其合理性何在,就成了需要确證的問題。既然世界已不再被看作是上帝的造物,而是人的理性的設計,自然這種合理性的根據也就出自人本身,出自人的理性。是以理性成了真理之源、價值之源,進而也成了現代性的安身立命之地。
三是福柯将現代性了解為「一種态度」。他說,「所謂态度,我指的是與當代現實相聯系的模式;一種由特定人民所作的志願的選擇;最後,一種思想和感覺的方式,也就是一種行為和舉止的方式,在一個和相同的時刻,這種方式标志着一種歸屬的關系并把它表述為一種任務。無疑,它有點像希臘人所稱的社會的精神氣質 (ethos)。」特别地,這種現代性的「态度」或「精神氣質」,福柯把它解讀為一種「哲學的質疑」,亦即對時代進行「批判性質詢」的品格。在論述啟蒙的意義的時候,他特别強調,我們應當從啟蒙中繼承下來的精神财富,或者說能夠連接配接起我們與啟蒙的共同的态度,正是這種對時代進行永恒批判的哲學氣質,而不是去忠實于某種信條。是以,對于福柯來說,現代性從根本上意味着一種批判的精神。
/現代性的來源:啟蒙運動
一般認為,現代性的基本觀念來自啟蒙運動的精神,是啟蒙精神哺育了現代性的産生。
「啟蒙運動」指的是在 17 世紀和 18 世紀的歐洲所發生的一場廣泛而有力的思想運動,其宗旨是運用理性來破除宗教迷信和盲從,用科學知識來消除神話和幻想,使人擺脫其蒙昧狀态,達到一種思想與政治上的自主性。啟蒙運動的上述特征,得到許多思想家們的認同。例如,在18 世紀,偉大的德國哲學家康德就講啟蒙概述為使人脫離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态。要做到這一點,根本上在于人們要「敢于運用自己的理智」。以賽亞 · 伯林同樣把啟蒙運動的核心觀念概括為:「宣揚理性的自律性和以觀察為基礎的自然科學方法是唯一可靠的求知方式,進而否定宗教啟示的權威,否定神學經典及其公認的解釋者,否定傳統、各種清規戒律和一切來自非理性的、先驗的知識形式的權威。」
是以我們可以看到,啟蒙的目标既然是消除蒙昧、開啟民智,那麼價值之源自然就不能像以往所信奉的那樣來自神的啟示,人們所能依靠的隻有自己的理性,大膽地去思想。這樣,在啟蒙的時代,理性就擔當起思想批判的重任,成為審判一切已有的宗教、哲學、法律與政治觀念的「法庭」。理性主義首先是建立在對「理性」能力的确認之上的,也就是把理性确認為一種不同于感性、情感、意志的能力。這種能力主要表現為思想、反思、從事邏輯判斷與推理的能力,集中表現為一種「自我意識」的能力,或者說「我思」的能力。在哲學史上,理性主義在認識論、倫理學與宗教哲學上有着不同的表現。認識論上的理性主義是其他領域的理性主義的基礎,它主張在擷取知識方面,理性比其他認識能力具有優越性。
宗教哲學中的理性主義則是反對宗教知識中以「天啟」為核心的觀念,主張一種理性化的宗教。啟蒙的理性主義對宗教信條的批判,其實質就是對宗教神聖化的解構。在歐洲邁向現代文明社會的程序中,制度化的天主教會作為宗教神聖化的化身,曾經是進步思想與科學的敵人。哥白尼的「日心說」由于摧毀了經院哲學納入自己體系之内的托勒密的「地心說」,并且影響着人們的思想和信仰,因而被教會宣布為「錯謬的和完全違背聖經的」,在未經改正之前不許發行。教會所設定的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甚至将主張人們有懷疑宗教教義的自由的哲學家布魯諾判處死刑,燒死在羅馬。哥白尼學說與布魯諾本人所遭受的厄運,皆是因為他們挑戰了基督教的世界觀信條,冒犯了基督教的權威。宗教蒙昧對文明進步構成的巨大障礙,使得啟蒙思想家必然要與之進行鬥争。他們訴諸理性來猛烈批判宗教蒙昧,尋求削弱宗教教會所強加的信仰和懲罰的權利。對基督教神聖化的解構的結果,使得西方的現代性程序展現為一種韋伯所刻畫的「祛魅」過程,即宗教世界觀的逐漸瓦解與消除,世界擺脫了制度化的教會的控制與影響,逐漸走向世俗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同時也是文化的理性化過程。
除了掃除宗教蒙昧,為思想的啟蒙與自由掃清障礙之外,啟蒙的理性主義為近代西方思想至少還灌輸了這麼一些意識和精神,它們為現代性的産生提供了思想基礎。
啟蒙的理性觀
在認識論上,理性主義确立了近(現)代的知識标準,即知識必須具有這麼一些屬性:客觀性、普遍性、必然性、确定性。伯林甚至把這種知識觀看作是「啟蒙運動的中心原則」。這展現在真理觀上,就是真理是一進制的。與這樣的知識觀與真理觀相聯系,就有了知識論上的、笛卡爾式的古典基礎主義,即知識表現為一種雙層的結構,底層是某些确定的、不證自明不證自明的基礎信念,它們表現為類似于幾何學的公理,可以用來支援處于其上的非基礎信念,為它們提供理由方面的确證,使之成為具有确定性的知識。
作為上述知識觀的延伸,理性主義在科學領域确立起這樣的觀念:存在着普遍的、永恒的自然與社會規律,任何科學的目的都是要把握這類普遍的規律;存在着真實不變的、普遍的客觀價值,它們對一切人、一切地方和一切時代來說都是正确的,這些價值至少從原則上說是可以實作的。這種有關把握規律的觀念,一方面有助于引導人們關注對自然與社會發展規律的探讨,促進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它也膨脹了一種「理性萬能」的觀念,導緻了理性的盲目樂觀與僭越,試圖對未來社會的秩序與模式進行人為的設計。
深究下去,有關「理性」能力如何的主張乃是尋求從根本上把握人性的努力,這一努力從休谟的《人性論》這一著作的題名中可以體會出。休谟認定「關于人的科學是其他科學的唯一牢固的基礎」,而這一科學的「首都或心髒」,又是「人性本身」。人性的設定為啟蒙哲學提供了一塊基石。
然而,對于一些哲學家而言,他們基于古代的自然法學說而産生了這樣的信念:存在着一種恒定不變的人性。人之是以為人,正是由這一人性所決定的。盡管時代與地域可以有所不同,顯示出其多樣性,但人性卻是永恒的。就像對自然規律的把握使我們得以解釋自然現象一樣,對人性的把握也使我們能夠了解人的精神與文化現象。
不論是知識觀、真理觀還是人性論,總之它們都屬于一進制論的思想方式,這種思想方式是與當時所具有的唯一的邏輯形态——形式邏輯相适應的。形式邏輯的基本思維規律是同一律:A=A。凡違背這一規律的,皆被視為沖突而要予以排除,因為沖突意味着錯誤,是以是不允許的。
随着18世紀啟蒙運動的推進,哲學家們對理性的實質與作用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這一認識集中展現在康德與黑格爾那裡。我們先來看康德。如所周知,康德寫下了著名的三大批判以及其他論著,系統地對理性的能力與作用進行了思考,使理性與現代性有了明确的關聯,成為現代性的基本構成要素,這集中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首先,理性的運用是啟蒙發生的前提,而啟蒙則是現代性産生的先決條件。在康德看來,啟蒙的目的是使人擺脫其思想的不成熟狀态,而所謂的「不成熟狀态」則是指如果不經别人的引導,就無法運用自己的理智,也就是處于一種蒙昧的狀态。而要進行啟蒙,就「必須永遠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惟有它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
其次,理性是認識之源、價值之源。從認識上說,這一方面表現在統覺的「我思」是一切認識的最高條件,它是對感性質料進行綜合的最高根據,另一方面表現在經驗認識的規則先天地在于理性自身中,也就是說,理性自身能夠提供有關經驗判斷的系統規則或原理,正是依據這些原理有關現象世界的科學認識才得以可能。此即康德的人為自然立法,或曰他的認識論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從道德倫理上說,一方面實踐理性的本源根據作用表現在它能夠提供一種絕對的道德律令,并以此作為人的道德責任,使之在道德判斷與行為上實作自律,另一方面這一道德律令提供了一種善惡的價值标準,符合這一道德法則的動機及其行為就是善的,否則是惡的。這裡,不論是作為認識的還是道德的最高根據條件,總之理性都具有至上性。
繼康德之後,黑格爾把理性概念推向最高峰。首先,他以展示一種從意識、自我意識再到理性的「精神現象學」的方式,來證明理性是所有人類精神意識的最高表現與成就;其次,他進而把這種理性的精神發展史,以先後相繼的方式展現為一個嚴格的概念體系,并證明這本身就是一種曆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思維邏輯。最後,也最為重要的是,他為事物建立了一個理性标準:「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這一标準的重要性,突出表現在韋伯那裡,「合理性」成為衡量現代資本主義以及現代社會的經濟、政治、法律等各方面的進步性的标準,「理性化」是以成為現代社會及其現代性的标志性符号。
韋伯把「理性主義」視為西方文化所特有的東西,把「找尋并從發生學上說明西方理性主義的獨特性,并在這個基礎上找尋并說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獨特性」作為當務之急的一個目标。在德國理性主義的思想背景下,他對現代社會的分析突出了兩個概念——「理性」與「理性化」,前者在他那裡演化為「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這一對立、沖突的概念,後者則成為他用來描述、刻畫與評判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法律等行為規範的特定概念。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過程,在韋伯的這種分析中,表現為一個全面理性化的過程,而理性化也是以成為「資本主義精神」,亦即資本主義的現代性。在經濟行為方面,這種理性化表現為精确計算投資與收益之比的「簿記方法」;在政治行為方面,表現為行政管理上的科層化、制度化;在法律行為方面,表現為司法過程的程式化;在文化行為方面,表現為世界的「祛魅」過程,即世俗化過程。
然而,這種「形式」方面的行為合理性,造成的結果隻是一種「工具合理性」,即運用某種手段來達到某種特定的目的,而不顧及行為在「内容」上的合理性,即它所應有的道德價值考慮。然而社會本應以「公正」「善」等價值為指歸,是以現代社會在「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方面發生了分裂,這不僅意味着形式合理性所蘊含的「工具理性」成為純粹功利主義的東西,而且意味着形式合理性已走向理性的反面,成為一種非理性的東西。西方的現代性由此蘊含着内在的沖突。韋伯這方面的分析、特别是他所運用的「工具理性」與「理性化」這兩個概念,比較深刻地把握了西方現代性的特征與問題,是以,這成為有關現代社會分析的經典學說,構成後現代主義産生之前的有關現代性解釋的基本概念系統與分析架構。西方的現代化過程與現代性的形成,循此被解釋為一個理性化的過程。他的「工具理性」的論說,則被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别是法蘭克福學派用來作為資本主義社會與現代性的弊病的一個主要符号,進而成為他們進行「技術理性」批判的一個主要概念根據與話語源泉。從霍克海默、阿多諾的社會批判理論,到馬爾庫塞的發達工業社會的研究,再到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莫不如此。
啟蒙的科學觀
與啟蒙時期的知識觀、真理觀相伴随,啟蒙也發展出了一套新的科學觀念。不過這種觀念的發展卻經曆了一個變化,即從以笛卡爾為代表的演繹型的方法論,轉變到以牛頓、洛克為代表的經驗型的方法論。之是以有這兩種方法的差別與轉變,是由于這兩種方法論的倡導者分别信奉的是不同的科學模式。對于演繹型的方法論者而言,他們以數學、尤其是歐幾裡得幾何學為楷模,認定理想的科學方法是從某些作為前提的普遍性的公理、原理中演繹出個别性的結論。笛卡爾、萊布尼茨等認為,由這樣的推論中得出來的真理是具有必然性的,其思維過程是從普遍到個别。而對于經驗性的方法論者來說,他們主張一切認識都是從觀察、從個别性的知覺出發,經過試驗等環節,最終形成普遍性的經驗。
從伽利略開始,實體學的研究走上了一條從觀察出發,提出假設,并通過試驗等手段來檢驗假設的正确之途。這一方法的要義在于,它反對單純的構造「假設」,僅僅通過頭腦中的構想來臆測事物。牛頓說,一切并非由現象中推論得到的東西,均屬「設定」,不問其為玄學的、實體學的或力學的等等,都不能用于實驗實體學之中。這裡,牛頓明确反對制造「假設」,亦即制造那些形而上學的、不能證明的假設,而且他從來不發表不能用觀測或試驗證明的學說。需要說明的是,牛頓使用的「假設」一詞,與我們現在所說的科學的「假說」不同,它指的是用來記述某些表示「神秘的質」的術語,而對于這些「神秘的質」,我們甚至連測量它們的程式都還沒有找到。相反,對于牛頓而言,正确的科學方法應當是,在對現象的仔細觀察的基礎上,「特殊命題從現象中推出,然後通過歸納使之成為普遍的命題」。
牛頓的科學上的經驗方法論與哲學上的經驗論的合流,使這種強調認識的經驗來源的思想成為方法論的主流。18 世紀的法國啟蒙哲學家,如伏爾泰、孔迪亞克、拉美特利等,基本上贊同牛頓、洛克的經驗論主張。例如,伏爾泰有代表性地指出:「洛克在摧毀了天賦觀念之後,……很好地證明了我們的一切觀念來自感官。」這種方法論思潮後來繼續延伸下去,演變為19世紀的實證主義哲學,在20世紀上半葉以強化了的邏輯經驗主義的主張出現,它以「命題意義的可證明性」為标準,力圖掃除一切非科學的命題。邏輯經驗主義使啟蒙時期以來的經驗主義哲學成為顯學,後來更以「分析哲學」的面目出現,成為了20世紀西方哲學的一個主流學派。
從經驗主義強調的認識的感覺經驗的來源說,一直到邏輯經驗主義堅執的命題意義的可證明性标準,它們關涉到的實質性問題,都是有關科學劃界的問題,亦即劃清科學與非科學的界限。對于啟蒙時期的科學與哲學來說,非科學的東西不僅包括牛頓所反對的非經驗的「假設」、形而上學的臆測,而且包括宗教的迷信。劃清這樣的界限,一方面能使科學明确它的研究性質與方法,排除舊形而上學與宗教信條的幹擾,使科學能夠沿着正确的軌道發展,另一方面,它逼使非科學的東西(包括形而上學的、宗教的)退出科學的領地,使得它們不能再幹預科學的活動。相應地,宗教退出科學的領域,退出政治的領域,實作宗教與科學的分離、宗教與政治的分離,宗教回到它本來應處的精神與文化領域,這就使社會的結構及其各個要素的功能明晰起來,使之能夠各司其職,進而使現代性所展現的社會世俗化過程得以真正可能。與此相關,啟蒙思想家所追求的宗教成為真正個人的理性信仰的目标,也才能夠得到實作。
/現代性的核心價值:自由
構成啟蒙的思想大廈的,還有自由主義思想這一重要次元。盡管對于自由主義的定義與解釋衆說紛纭,但自由主義的基點無疑是對于個人權利、尤其是其核心——自由權利的保護。由此基點出發,邏輯地演繹出這麼一些問題與回答:首先,對個人自身而言,由于認定個人的自由、财産等權利屬于一種「自然權利」,是不可侵犯、不可剝奪的,是以個人對于一切事物來說,是最為根本的、高于社會與國家的存在,這就使自由主義表現為一種「個體主義」。其次,對個人與外部國家的關系而言,基于對個人權利的捍衛,自然得出國家不得幹涉、侵犯個人權利的結論,而要做到這一點,國家的統治(具體表現為政府)就必須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這兩個要義,也正是自由主義學說的主要奠基者洛克所要論述的。
自由主義的上述兩個要義,抓住了政治哲學的根本,為西方現代國家的建立、現代性的形成奠定了相關的思想基礎。這些基本觀念的重要性及其實踐方面的意義,已經由曆史提供的經驗與教訓所證明。民主社會以人為本,保護了個人的自由,使個人的才能得到充分施展,個人創造的财富得到保護,社會就繁榮就發展;反之,極權社會「苛政猛于虎」,扼殺人的自由,封殺了思想與财富創造的空間,社會就爆發各種危機,最終衰敗。
對于啟蒙的個人主義,我們應當辨明的是,它的精神實質簡單說來就是「以人為本」,也就是說,在人與社會這兩極中,個人是本原的、根本的存在,社會是由個人所組成的,是服務于個人的。個人是目的,社會隻是實作這些個人目的的手段。個人之是以為「本」,這個「本」乃是在于他的不可剝奪的生命、自由與财産等權利,在于這些權利自身所具有的寶貴價值。正是由于如此,是以政府必須通過人民的選舉、獲得人民的同意而産生,并以服務人民為宗旨。
除了作為思想基礎的個人主義之外,啟蒙的自由主義還涵括了政治與社會哲學中的廣泛内容,包括自由、平等、寬容等價值,以及民主、法治、權力的分立與制衡等為實作上述價值而必需的手段。自由主義的這些思想,為西方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提供了制度設計所需的理論指導,并由此形成了西方社會的現代性。
對于上述的自由主義所關涉的諸種價值及其實作的諸種手段而言,「自由」乃是其核心的價值,在一定的意義上,民主、法治與權力的制衡等,都是為實作「自由」的目的而服務的。比如洛克就認為,在自由、生命和财産這三者中,自由是本質,人的一切權利都不過是自由的展現。啟蒙的自由主義者所說的自由主要是個人在政治和法律意義上的自由。霍布斯所提出的定義:「自由這個詞語,按照其确切的意義來說,就是外界障礙不存在的狀态」,被看作是有關自由概念的「經典陳述」。這種「外界障礙」,在根本上是政治方面的「權力」,這意味着,自由本質上就是不受權力控制的。
而盧梭則在這一問題上思考得更深,他的著名的問題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包括處于強制性的法律的限制中,是以他試圖加以解決的難題是,人如何在遵守強制性的法律的同時,又能夠不失去自己的自由。盧梭用「公意」理論來解決這一難題,他設想人們制定某種社會公約,結合為某個道德的與集體的共同體。由于公約是大家共同制定的,是以服從這一公約乃是在服從公共意志,是以也就等于服從自己。這樣,如果任何人拒不服從公意,社會全體就要強迫他來服從,亦即強迫他自由。盧梭的這種自由觀,在伯林所作出的「積極的自由」與「消極的自由」的區分中,被劃歸「積極自由」的範疇。所謂「積極的自由」,伯林指的是「成為某人自己的主人的自由」,也就是說,這種自由是通過理性的自我主導、自我控制與自我實作來獲得的。
對于這種自由的主體來說,他隻做自己願意做的事情,這意味着假如遇到障礙的話,那麼他就要清除阻礙其意志的障礙,不管這些障礙是什麼,不論它們來自自然、主體的未被控制的激情、非理性的制度或其他人的對立的意志或行為等等的反抗。一言以蔽之,伯林稱這種「積極自由」的學說是積極的、通過理性獲得解放的學說。将這種學說的邏輯推演下去,對于自然,積極的自由主義者從理論上說可以通過技術的手段加以改造,但對于頑抗他的自由意志的人類将如何處置呢?如果可能的話,他也應該将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對方,同樣将障礙加以掃除,哪怕這樣的掃除活動含有暴力、殘酷、對别人的奴役,可能也會在所不惜;特别是,當這種自由的主體由個人而膨脹成某種超人的實體——國家、階級或民族的話,「積極自由」的學說會将導緻極權、專制的結果。是以,伯林認為,「積極自由」乃是當代許多民族主義者、極權主義者等的信條,而這種積極自由也便是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進行批判的焦點之一。
我們可以進一步從康德與黑格爾的哲學那裡,來看看自由在現代性中所具有的根本價值。康德明确宣稱:「人類理性的立法(哲學)有兩大目标,即自然和自由。」這裡的「自由」,指的是道德的自由。作為對道德進行形而上學思考的哲學家,康德所論述的自由,與盧梭、孟德斯鸠等人着重于政治學意義上的自由不同,他的「自由」概念是「形而上」層面的,也就是進入到對「人是什麼」,對人之是以為人的根據的思考。他對這一問題給出的答案是,「人是目的」。人格的價值與尊嚴,在于它在道德上是自律的,即自己為所要遵守的道德立法,并服從自己所頒布、确立的這些道德法則;而不是他律的,即被外在的感性欲望所左右。更進一步說,道德之是以能夠是自律的,是由于作為道德的主體,人具有自由意志。「自由」與自然的因果決定論不同,後者隻能無條件地服從原因決定結果這種機械的因果關系,例如天下雨了,地就必然濕,「地濕」是「天下雨」這一原因的必然結果。而「自由」則是能夠自發地開始一個原因的系列,也就是說,它是自我決定的,自己是自身行為的原因,可以不受其他條件的左右。通俗地說,就是我能夠對自己的行為作出決定,作出選擇,比如,我現在可以選擇去教室自修,也可以選擇去圖書館,甚至可以選擇去看電影。
康德的這種道德自由在性質上是一種「先驗的自由」。所謂「先驗」,是與「經驗」相對而言的。經驗的東西是來自于外部的可感覺的事實,而先驗的自由則是來自于非經驗的、純粹的「理性」本身,在道德行為中,是來自于人的「意志」或曰「實踐理性」。這種「先驗自由」的确立,對于「人是什麼」的認識來說,它确立了人的主體性。再也沒有什麼淩駕于人之上的造物主了,人是真正的「萬物之靈」,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他依靠自己的理性與意志,不假他求,就可既為自然立法,也為道德立法。
與康德旨在提供作為道德立法基礎的「先驗的自由」不同,黑格爾的自由觀更多地表現出的是它的現實的品格。之是以說黑格爾的自由觀的基調是現實的,是因為他強調「隻有在個人屬于倫理的現實時」,他們的主觀上所規定的「自由的權利」,才能得到實作。這些所謂的客觀自由的「倫理的現實」,在黑格爾那裡表現為三個環節:家庭、市民社會與國家。黑格爾把市民社會作為一個獨立于國家的公民「自治」的領域,賦予公民一個保有自己的利益,不受國家幹預的自由的空間。在他那裡,市民社會作為「家庭」與「國家」之間的一個「中介」環節,其目的是「私人的利益」,它是一個經濟活動意義上的「需要的體系」,是人們以契約性為基礎而追逐私利的領域。由于滿足需要的手段主要是勞動,因而勞動與分工構成市民社會的主要内容。此外,黑格爾的市民社會概念的一個主要特點,還在于它強調市民社會通過同業公會和各種自治團體所表現出的組織性和秩序,這蘊含着市民社會的自治的性質。他認為沒有組織的個人,其行為隻是完全自發的、無理性的甚至是野蠻與恐怖的,是以個人是無法直接與國家打交道的,隻有通過以有組織的方式進入國家這一有機的整體時,其利益才能得到實作和保護。
/現代性的基石:主體性
作為規範性的現代性哲學,我們已經提到它要提供的是有關現代性的目的、現代性的原則等一套哲學論辯的話語系統。哈貝馬斯曾經将現代性的這套哲學話語系統歸結為「現代性的自我确證」。這種自我确證中最可寶貴的是有關人的觀念,它是由形而上學來提供的。
形而上學按照康德的界說,是來自純粹理性的、非經驗的學說,亦即關于「範疇」或「理念」這類純粹知性或理性概念的學說;這意味着關于人的觀念隻能由純粹的思想來給出,屬于「形而上」的東西。之是以說人的形而上學對于現代性的自我确證來說是最可寶貴的,是因為現代性對其目的與原則的确證,既然排除了由上帝那裡獲得合理性的根據,那就隻能由人自己來給出;既然無法由神學來給出,那就隻能由超驗的形而上學來給出。
而當形而上學将「理性」認定為人的本質後,現代性的自我确證就還原為“理性”的問題,還原為理性不僅能夠為自然、而且能夠為道德立法的能力問題。隻有超驗地論證了理性的這一形而上的能力,人才能取代神,哲學也才能取代神學,世俗化的現代性也才能具有它的合理性,進而為曆史掀開嶄新的一頁。這種對人及其理性的認識,在哲學上表現為一種「主體性」哲學,以及因圍繞着對作為「自我意識」的理性的論證而形成的「意識哲學」。這兩種哲學形态成為現代性哲學的基本形态,康德哲學成為其中突出的代表。康德哲學的主題「人是什麼」,由此可視為現代性哲學的主題;現代性的哲學話語,相應地可以視為圍繞着理性人的軸心而展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哲學意義上的現代性是人的現代性;正是由于有了現代的人的觀念,才催生了現代意義上的人,并由這樣的人建構出理想的現代社會。
康德的主體性哲學為現代性所塑造的「人」的觀念,是把人視為目的,而且是宇宙世界的「終極目的」。康德不吝用各種最強烈的用詞,來贊譽人的終極目的性。人是「唯一的」一種存在,他的目的性是一種原因性,能夠據之來為道德立法;人作為終極目的是「無條件的」,他不需要任何别的東西作為他的可能性的條件;人之是以是終極目的,在于他是道德性的存在,他的「善良意志」使其具有某種「絕對價值」。甚至,整個宇宙大千世界,盡管有着多種多樣的造物,但如果沒有人的話,就都會是「無意義的」;也就是說,「沒有人,這整個創造都将隻是一片荒漠,是白費的和沒有終極目的的。」
康德如此,黑格爾也是如此。黑格爾哲學的一個明确宗旨是把握所處的「現代」的時代。這是一個「舊世界行将倒塌」,「一個新時期的降生和過渡的時代」。作為哲學家,黑格爾對時代的把握着眼于它的「新精神」與「原則」。因為精神是「最高貴的概念」,是事物的「本質」。他明确提出,「現代世界是以主體性的自由為其原則的」。這一自由表現在認識中,就是對「必然」的把握,對自然規律與社會曆史規律的把握。在《精神現象學》中,他緻力于把握的是人類精神(意識)在其發展過程中所展現出的「内在必然性」,這就是,從最初的、直接的感性意識開始,經過自我意識、理性、精神、宗教這幾個辯證的自我發展環節,最後達到對「絕對知識」,即人類精神對其最高知識狀态的概念上的把握。這一自由表現在國家與社會中,就是為理性精神所認識到的一切本質的東西,都會在現實中得到實作。這是對「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的觀念的進一步延伸。黑格爾不滿于使精神僅僅停留在主觀觀念的層面上,而是堅信思想必定能夠轉化為現實。同理,「自由」也一樣并非僅僅是主觀的觀念,而是能夠在包括家庭、社會與國家這些「倫理實體”」展現為客觀的、實在的權利。黑格爾并且進一步把主觀的、觀念上的自由與客觀的、現實的自由的統一,看作是構成了「合理性」的内容,而把合理性的形式解釋為「根據被思考的即普遍的規律和原則而規定自己的行動」。由此,在黑格爾哲學那裡,理性的主體性原則通過展現為規律、自由與合理性的内在的統一,而成為貫穿于知識與道德倫理,亦即真與善的所有領域的原則。這樣,雖然黑格爾與康德的哲學表現為不同的形态,康德哲學通過對「人是什麼」的命題的回答,直接為「主體性」作出有關理性能力(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肯定,進而為現代性的自我确證問題給出了理性為自然立法、為道德立法的題解,而黑格爾則通過對「絕對知識」亦即本質、真理的把握,來展現理性精神的自由本性,進而借助包含着主觀自由與客觀自由的統一、規律(原則)與行為的統一的「合理性」概念,來給出有關現代性的自我确證問題的答案。這樣,盡管康德與黑格爾這兩種哲學的形态不同,但它們在本質上卻同屬主體性哲學的範疇,都是通過對人、對其理性與自由的本性的了解,來達到對現代性的建構——在康德那裡,表現為人為自然與道德立法,在黑格爾那裡,則表現為把握了現代社會的「絕對知識」或「絕對精神」在道德倫理、社會國家等領域實作其自身的過程。既然現代性的自我确證建立在理性的主體性哲學上,是以一旦這種主體性哲學被否定,整個現代性的立論基礎就會被摧毀,現代性的話語也将被改寫乃至為後現代所取代。
是以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否定,首先否定的就是這種主體性哲學,否定其有關人的觀念。尼采否定了人的理性本質,而把人的本質定位為生命及其意志。現代性的「特點」或弊病,被他歸之為生命意志的衰微而導緻本能取得統治地位,缺乏意志的現代人成了「頹廢的象征」。現代精神由此陷入一種傳統價值體系崩潰的「虛無主義」,已經「無藥可救」。福柯則反思了他認為自18世紀以來哲學和批判思想的核心問題——理性是什麼?其曆史後果又是什麼?他通過揭示「主體」乃是由無所不在的權力之網(包括監獄、醫院、學校、性的控制、知識話語等)進行的規訓所造就而成的,是以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獨立自主、無處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體」,相反,「主體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來的」。福柯既對「主體」的性質得出這樣的判斷,那麼他把啟蒙哲學中的「人」的概念歸結為某種「發明」,并宣稱這種意義上的「人死了」,也就是一種自然的結果。
從以上粗線條的勾勒中,我們便可以窺見「主體性」概念對于現代性哲學的意義,以及它在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哲學兩軍争戰中所處的前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