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現在新疆木壘縣菜籽溝村跟大家交流。這邊天還很亮,落日還在地平線上,你們那邊應該是黑夜了吧。”劉亮程略帶滄桑的聲音從微信群裡傳來,一句問候,忽然拉開廣袤的時空感。
這是“南都讀書月”的首場線上活動。著名作家劉亮程攜新作《本巴》做客南都讀書俱樂部微信群,為我們講述“從《江格爾》到《本巴》:童年、夢與遊戲中的曆史”。
《本巴》是劉亮程繼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提名獎後的最新長篇小說,榮獲2021花地文學榜年度長篇作品。它以史詩《江格爾》為背景展開,另辟蹊徑再創現實,以追溯逝去的人類童年。劉亮程說:“《本巴》是我寫得最愉快的一部小說,也是我寫給自己的童年史詩,是我寫作曆史中最天真的一次。”
在講座中,作家從偉大的英雄史詩《江格爾》談起,他講到自己早年如何被《江格爾》史詩所吸引、所撼動,又如何以《江格爾》史詩為土壤和肩膀,在心裡孕育出《本巴》的故事。《本巴》的大部分情節由“搬家家、捉迷藏、做夢夢”等孩童的遊戲推動,劉亮程也莊重地談及草原上遊牧民族的“轉場”,以及搬家家、捉迷藏等遊戲所指涉的現實意涵。與上一部小說《捎話》相比,《本巴》采用了舉重若輕的寫法處理曆史題材,達到“曆史的個人化”效果。在劉亮程看來:“一個作家需要用文字去了解曆史。作家會将自己置身于曆史的空間中,讓一個地方的曆史變成個人的心靈往事。”
4月23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讀書日。線上上書會上,劉亮程推薦讀者閱讀《江格爾》《格薩爾》和《瑪納斯》三大史詩。他說:“尤其對那些已經讀過荷馬史詩、印度史詩等世界著名史詩的讀者來說,讀一讀我們國家的史詩,你可能會感到非常親切。史詩中的故事都是這塊大地上原生的故事,你在這樣的史詩中可以讀到祖國的山河,可以讀到你熟悉的氣候、草木、馬匹,肯定也會讀到讓你感到熟悉又陌生的邊疆民族的英雄精神。”
部分講座實錄:
【主持人】:英雄史詩《江格爾》主要流傳在中、蒙、俄三國的衛拉特蒙古人當中,大約産生自13世紀,由演唱《江格爾》的民間藝人“江格爾奇”代代相傳保留下來。首先想請問劉亮程老師,您是怎麼接觸到《江格爾》這部蒙古族的史詩并被其吸引的?為什麼我們說史詩駐足的地方,《本巴》開始講述?
劉亮程:大家好,我現在新疆木壘縣菜籽溝村跟大家交流。這邊天還很亮,落日還在地平線上,你們那邊應該是黑夜了吧。我們在不同時區存在着時間差。其實史詩跟我們現代人有着遙遠的時間差,那時文字還沒有出現,或沒有廣泛應用,人們靠口口相傳記憶他們認為重要的曆史、文化、思想和想象。神話、史詩是在人們相信神的年代才有可能被創造出來。今天我們讀史詩還會相信它嗎?當然會。至少我會。我們可以通過閱讀史詩,回到我們的祖先曾經相信的那些事物中去,回到那個有聲的遙遠時間。
我讀《江格爾》史詩比較早。因為我在新疆文聯工作,文聯有民間文藝研究會,專門收集整理民間文藝作品,出版幾大類的民間文藝內建等等。我是它們少有的讀者,因為這樣的書出版量很少,幾乎不在書店銷售。隻有個别的專家會借來閱讀。
新疆文聯的民研會對《江格爾》史詩的收集整理大概是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史詩工作小組在全疆20多個有蒙古族居住的縣做采錄,先後采錄了100多位江格爾奇,對大量的錄音資料進行整理篩選,才有了我們現在讀到的《江格爾》史詩這樣的文本。現在翻譯成漢語的《江格爾》史詩有六卷本。
我對《江格爾》史詩這正發生興趣大概是在十年前。以前隻是讀,後來有機會真正走到了史詩故鄉。那時候我有一個工作室,我們在《江格爾》史詩傳承地,新疆和布克賽爾蒙古自治縣做了一個文化旅遊項目,叫“牧遊”,就是把“遊牧”兩個字倒過來。非常有意思,跟着羊群去旅遊,把那些山野草原中的古老牧道當成旅遊路線,把牧民的氈房當作客房,每天都搬家,走羊的路,看羊眼睛中的風景。當時我們接觸的牧民多數都是蒙古族。
我們還參與設計了和布克賽爾縣《江格爾》史詩廣場,在廣場上樹立了一宗主題雕塑,72位勇士舉着一口直徑9米的大碗給江格爾汗敬酒,這個雕塑的創意靈感正是來自江格爾史詩。我的小說《本巴》中也寫到了這一章。
那時候我隻是給江格爾文化做傳播工作,有機會接觸到當地的蒙古族人,也能聽到江格爾奇的演唱。但并沒有想到以後會以江格爾為主題寫一部小說。多少年之後,一部叫《本巴》的小說在心中發生了。
有時候覺得作家可能真的不是為了寫作而生活,但作家的生活、閱曆和經驗可能是成就作品最重要的東西。一段生活經曆在内心沉睡多年,後來在某一個瞬間被喚醒,它成為了一部作品。《本巴》就是在心中沉睡多年,被喚醒的那個故事。
當我在寫小說《本巴》的時候,我自己有了江格爾奇的感覺。我覺得我從世世代代的江格爾奇的講述中,學會了另外一種講述。我從他們停住的地方開始了自己的故事。這也是這部以史詩為背景創作的現代小說《本巴》的寫作動因吧。
但《本巴》是一部現代小說,它隻是借用了史詩開頭的模式把讀者引入到史詩的空間。接來下的故事就全是作家自己創造的了,故事的結構也不再在史詩的模式之内。史詩有自己奇妙的想象和自由,但古人的想象總有盡頭,小說《本巴》其實是在古人想象停駐的地方往前展開作家自己無邊無際的冥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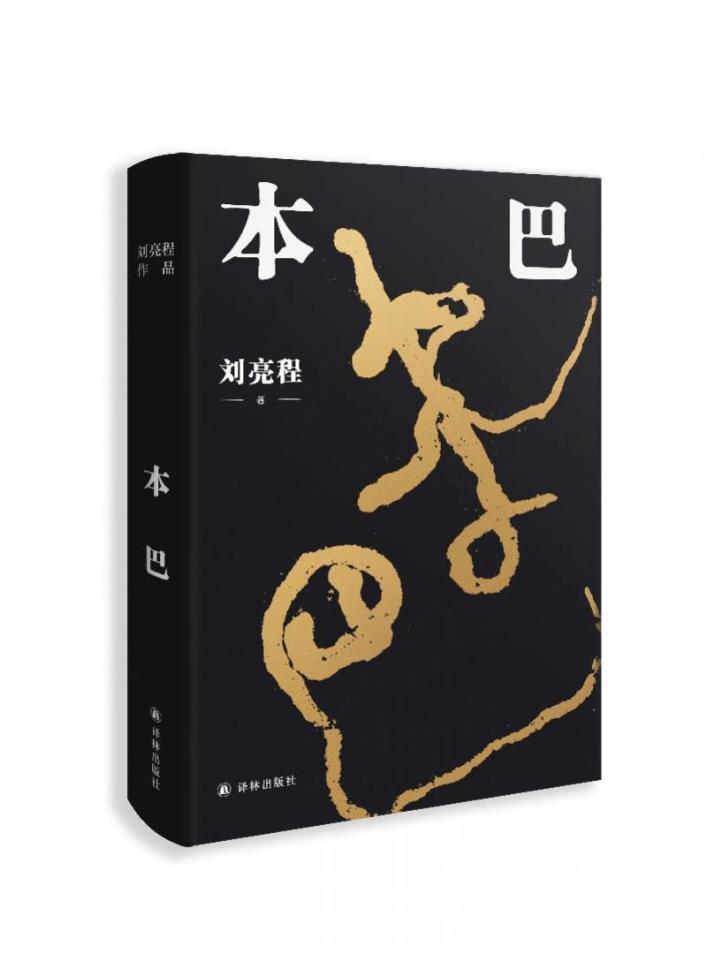
【主持人】:《本巴》的主人公是幾個孩子,赫蘭和哈日王在母腹裡久久不願意出生,洪古爾則是沒有斷奶,一直長不到車輪高的小孩。您為什麼要把小說的主人公設計為這樣的角色?
劉亮程:我在寫這部小說時感到自己真正回到了童年時代。假如史詩是人類幼年時代的文學講述,那麼通過《本巴》的寫作,我也一步步地回到了自己的幼年。其實每個作家都會在内心中養育一個不會長大的自己。無論我們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寫作,寫到極深情處,總會覺得内心中有一雙孩童的眼睛在睜開,有一顆孩童的心靈跳出來,掠奪我們的話語權。他要站出來去感覺這個時間,說出這個世界。《本巴》這本書就是我心中那個孩童蘇醒了。平常他一直沉睡着,用童年的方式隐藏在我這個大人的身體中、大人的心靈中。到了關鍵時刻,他開始蘇醒了,他要用童年的眼睛看世界,用童年稚嫩的嘴巴說出這個世界。
【主持人】:赫蘭從母腹裡帶出來的搬家家遊戲,把地上的羊糞蛋看成羊,馬糞蛋看成馬,把草葉看成拆散又搭起來的家……搬家家遊戲其實模仿的是草原民族的“轉場”,您在生活中目睹過遊牧民族轉場的情景嗎?它為什麼讓人震撼?在《本巴》裡,為什麼無論大人小孩、牧民士兵都沉浸到遊戲當中?
劉亮程:其實新疆這個大的地理環境本身就有遼闊的史詩味道。我在心境經常能碰到《本巴》裡寫到的轉場,尤其到了轉場季節,經常會遇到成千上萬的牛羊要過馬路,你的馬路橫在人家的牧道中間擋了羊的去路。羊過去的時候,車就得全停下來讓羊過去。有些地方,人的路跟着牛羊轉,和羊的牧道是重合的。人也要耐心等羊過去,因為這條路最早是羊走出來的。
在新疆,現在依然能夠看到一些古老牧道深嵌在山林草原,好多是羊走了數千年數萬年的路。對于轉場的牛羊來說,其實可走的路并不多,都會沿着原有的牧道在轉。是以每年的牛羊轉場可能是新疆僅存的遊牧文明的壯闊景觀。我去過哈薩克斯坦,在哈薩克斯坦遼闊的草原上都沒有轉場了,他們的牛羊早都已經圈養了。新疆現在的轉場牧道有很多也已經被農田阻斷了,現在很多的轉場都靠汽車運送。
以前牧民轉場其實是一件辛苦但又很幸福的事,因為轉場路途遙遠,長的牧道有好幾百上千公裡。牧人趕着自己的牛羊,沿途吃别人家的草,長自家牛羊的膘。夏天的時候趕着牛羊上山,往最涼快的山上去走,牛羊和人都避暑。冬天來臨前,又趕着牛羊下山,往沙漠戈壁的開闊地走,因為開闊地常年刮風,會把厚雪吹開,牛羊等吃到雪下面的草。
我小時候生活的村莊一直都是農區和牧區挨着,村莊附近是農田,農田外就是戈壁草原。農民和牧民一直是沖突體,因為農民種地需要開墾牧場,把牧場開墾成農田,農民和牧民對土地的争奪,一直就沒有斷過。這場争奪或許已經延續了幾千上萬年。這幾千年來,我們這塊大地上發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滄海變桑田。曾經是牧馬之地的滄海,全部變成了農田。
著名作家劉亮程
小說《本巴》中的搬家家遊戲有可能來自遊牧轉場生活。但它和捉迷藏遊戲一樣,是我們小時候必玩的遊戲,從童年玩到少年,有時候大人也跟着玩。那時候可玩的遊戲有限,甚至單調,但一直都沒有玩煩。它顯然是一個非常古老的遊戲了,就像小貓很小就會練習捉老鼠一樣,我們的孩子其實也在搬家家遊戲中學會了安置一個家,學會把家搬來搬去。對于這一代在城市租房住的年輕人來說,搬家可能是常有的事吧。搬家家可能對他們而言是一個很沉重的遊戲。
捉迷藏遊戲的現實意義可能在于預習現實生活中的躲藏和尋找。這些孩子在成人前要學會的遊戲本身有技能訓練的意義。這些古老而簡單的遊戲陪伴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度過了童年。他們在童年時期開始練習搬家,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開始練習躲藏和尋找。
《本巴》中寫得最驚心動魄的地方可能就是赫蘭深陷在捉迷藏遊戲中。一開始,他布置了一場搬家家遊戲,讓草原上所有的大人都在遊戲中回到童年。因為在《本巴》這部小說中,這兩場遊戲都有特别的功用。人們在玩搬家家遊戲時童心複發,很快在遊戲中回到童年。而在捉迷藏遊戲中,人又會藏起來,不被找見。赫蘭就是在捉迷藏遊戲中被人們遺忘了。一開始他藏得很深,害怕被找到。後來他知道沒有人找他了,他就故意顯露出身形。其實跟他一塊玩捉迷藏遊戲的這一代人都從遊戲中離開了,他一個人被單獨地留在遊戲中,再也出不來。後來,赫蘭借助各種各樣的辦法想從捉迷藏遊戲中出來,可是,那些陪他玩捉迷藏遊戲的孩子早已長成了大人,早已把這場遊戲忘記了。直到他最後回歸母腹,他都沒有從遊戲中出來。他帶着遊戲中的遺憾,回身藏到了自己的母腹中。
【主持人】在《本巴》裡,赫蘭們用遊戲取代了沉重的生活。我記得德國哲學家康德說過,藝術本質上是自由的遊戲。我們應該怎麼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系?
劉亮程:文學是現實世界對面的一個存在。當你覺得這個現實世界太真實,太堅硬,太讓你失望,讓你心灰意冷,那麼你隻要打開一本書,就會進入到另外一個世界。這個文學世界中,有我們現實世界的所有的情感模式,有所有的你能想到的或想不到的古今中外的故事。當你在讀一部作品的時候,你和這部作品的關系就在于,你從文學中讀到的是自己的感動,你流的是自己的眼淚,書中人物也是你。當你讀到最動心處時,那個書中世界就是你的世界。你在其中歎息,你在其中開心微笑,你在其中痛苦,在其中流淚,在其中多了許多希望,也多了諸多的失望和不如意。這就是文學跟我們的關系。
它不占這個世界的多少地方,就是一本書,平常擺在你家的書架上,看似就像一個擺件。但是一旦你有閑暇打開它的時候,你就打開了一個無窮奇妙的世界。那個書中有我們的精神家園。
【主持人】本巴東歸的故事,是《本巴》單行本裡額外添加的一章。其實《本巴》所涉及的真實曆史也充滿血腥和屠戮,是十分沉重的,但小說裡卻使用了舉重若輕的筆法,用遊戲、夢境、停頓的時間解構了曆史,用一種很靈性和詩意的方式去解釋衰老、死亡、戰争和人間的苦難。能否談談您自己的曆史觀?您覺得文學應該怎麼樣去呈現曆史和人生?
劉亮程:這個問題提到了《本巴》的輕與重。其實一部小說如何去寫是作家的政策。我的上一部小說《捎話》寫一千年前發生在西域大地上兩國的信仰之戰,極其殘忍。書裡寫了一場又一場的戰争。《本巴》其實也寫到了土爾扈特東歸這段曆史,12個英雄一個一個赴死的情節不是遊戲。我用史詩的方式呈現了每一個英雄赴死的過程,這一塊是重的。它平衡了整個小說遊戲的“輕”。我的《捎話》和《本巴》這兩部小說的發生地都在新疆,在我的生活之地。那些曆史中的、史詩中的地名今天都還在,阿爾泰山、額爾齊斯河等等,這些偉大的地名也穿越了整個曆史。《江格爾》史詩的開頭就是這樣寫的:“當阿爾泰山還是小土丘時,江格爾誕生了。”
《本巴》這本小說也是借用了江格爾史詩的開頭。我生活的地方在天山和阿爾泰山的中間,能望到西邊遙遠的地平線,也能通過曆史了解到發生在這塊廣袤區域的故事。其實,所有的曆史事件可能都沒有過去。我曾經說過,曆史是不會過去的。我們今天所在的生活可能正是曆史中某個事件的結果。比如《捎話》寫一千年前的信仰之戰,因為有了那場戰争的結局,才有了現在我們這個區的人的信仰。它是一場決定人們日後心靈的戰争。兩種信仰靠戰争對決。我把故事安排在那樣一個時間點,就是為了看到,在面臨信仰和心靈的抉擇時,人的身體會怎樣反應。
《捎話》中,許許多多的軀體選擇了為信仰而捐軀,許許多多的生命改變信仰了活了下來。我在那本書中寫了許多割裂的生命。那麼多那麼多割裂的東西,為什麼會出現在小說裡?因為這是我對這塊區域曆史的真實感受。我們一直在感受這塊土地上的割裂,但是一直也在以文學的形式去彌合它。是以文學對曆史的了解代表了一個作家活在此時此刻對曆史的真實感受。不管曆史過去多遠,曆史中的那些疼痛,我們都會感受到。
但《本巴》不一樣。我在《本巴》中用另外一種方式解讀了曆史。盡管我們從今天的生活中可以感受到曆史深處的疼痛。但是,作為一個作家,需要用文字去了解曆史。作家會将自己置身于曆史的空間中,将一個地方的曆史變成個人的心靈往事。新疆是一個多民族居住的地方,各民族各宗教各文化都有所不同。在新疆寫作,一個作家更容易感覺到這些文化的不同和共同。這也是寫《本巴》這本書的意義吧。我用一個漢族作家的心靈,去感受蒙古族英雄史詩的偉大魅力。以它為土壤,以它為肩膀,從它出發,去書寫一本屬于我個人的童年史詩。這是我的《本巴》,也是對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的另一種繼承和發揚光大。
南都記者 黃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