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造成了研究遲緩。不過在那段時間,我有大量的 Bench-free Time,自學了 Python 語言,後來已經可以獨立寫代碼分析資料,這反而加速了後來的研究,也算是彌補了因疫情導緻的延緩。”雖然是藥理學博士,但浙大校友梅柳竟然自己學會了計算機程式設計語言 Python。
Python 也助力她發表了一篇頂刊論文,完成發論文這件大事之後,33 歲的梅柳即将迎來另一件大事——成為一名媽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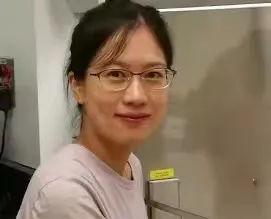
圖 | 梅柳(來源:梅柳)
在半個月前發表的論文中,利用首創的分析 MCM 加載動态的方法,她和團隊首次将活細胞成像技術與固定細胞免疫熒光成像技術,聯合用于檢測單細胞水準 MCM 複合體在人類亞細胞核内的加載動态,填補了該複合體在不同染色質環境的加載動态研究的空白。其中,MCM 的全稱是 Minichromosome Maintenance Protein Complex,指的是微染色體維持蛋白複合體。
1 月 26 日,相關論文以《在不同染色質環境中起源許可動态差異的後果》(The consequences of differential origin licensing dynamics in distinct chromatin environments)為題,發表在 Nucleic Acids Research(IF 16.971)上[1]。目前,梅柳在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生物化學與生物實體系做博後研究,是此次論文的第一作者。
細胞周期第一階段的晚期,對異染色質 MCM 加載極為重要
一般來講,細胞在每次分裂之前都要完成 DNA 複制,以確定分裂之後每個後代細胞仍然含有與母細胞數量相同的 DNA,隻有這樣才能保證遺傳穩定性。
但在 DNA 複制之前,細胞得先給部分 DNA 發放複制“起源許可”,這樣一來 DNA 隻能在獲得許可的位置開啟複制。DNA 複制許可(DNA Replication Licensing)假說認為,染色質 DNA 在細胞分裂發生之前精确複制、且僅複制一次的過程中,“起源許可”的作用至關重要。
細胞内所有 DNA 都必須被複制,無論是處于緻密的異染色質環境,還是處于疏松的常染色質環境。這意味着在有限的 DNA 複制準備時間内,也就是在 G1 期之内(G1 phase,一個細胞周期的第一階段),所有 DNA 都要獲得合适的起源許可。
已有研究發現,起源許可數量不足、或分布不均,都會導緻染色體遺傳的不穩定。對于“起源許可”的生化過程、即 MCM 複合體的 DNA 加載來說,此前已有大量詳實報道。
(來源:Nucleic Acids Research)
但是,關于這一過程本身對于染色質環境是否具有偏好性、或優先級的研究,目前尚未報道。
而在該研究中,梅柳通過向人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導入帶有不同熒光的細胞周期追蹤蛋白,并使用活細胞成像記錄細胞的生長周期。
在活細胞成像結束後,梅柳又通過特殊試劑去除遊離的 MCM 并固定細胞,随後進行 MCM 以及染色質标簽的免疫熒光染色實驗,并通過高分辨率共聚焦顯微鏡、對單個不同時期的 G1 期細胞進行多層次 3D 成像。
這時根據活細胞成像記錄,即可知曉每個細胞的分裂史、以及所處時期;而根據固定細胞免疫熒光成像,則可獲得 MCM 複合體的亞細胞核加載的數量。
綜合兩者得到的資訊,即可繪制出 MCM 在不同 DNA 複制準備時期、以及不同染色質區域的加載量,進而得到 MCM 的加載動态。
基于以上方法,梅柳發現在 G1 早期異染色質加載 MCM 複合體的速率低于常染色質,然而在 G1 晚期異染色質與常染色加載 MCM 速率相當。
基于此現象她推測,相比常染色質來說,G1 晚期對于異染色質加載足量 MCM 更重要。為驗證這一假設,梅柳通過誘導表達細胞周期蛋白 cyclin E 進而縮短 G1 期長度,迫使細胞過早進入 DNA 複制期也就是 S 期(S phase,即 DNA 合成期)。
在這些具有極短 G1 期的細胞中,其 G1 晚期異染色質 MCM 加載不足的現象顯著高于常染色質。在随後的 G2 期,這些具有極短 G1 期的細胞核内異染色質的 DNA 損傷程度,明顯高于正常細胞。而在兩組細胞中,常染色質的 DNA 損傷則無明顯差異。
進一步研究發現,導緻常染色質和異染色質 MCM 加載動态的差異,部分源于 ORCA 蛋白在常染色質和異染色質在 G1 不同時期的分布差異,進而導緻了所招募的 ORC 的分布差異。
梅柳表示:“我們的研究首次發現:相較于常染色質,異染色質許可在 G1 期相對延後,這意味 G1 晚期對于異染色質 MCM 加載極為重要。而這一特殊的許可動态,決定了在 G1 期異常縮短的細胞中比如原癌基因激活或抑癌基因丢失的細胞,異染色質極易因為遭受許可不足,而導緻基因組不穩定性增加。是以,完整的 G1 期對于維持基因組的穩定性極其重要。”
回顧研究步驟,她表示首先是提出立題依據,其所在實驗室對于“起源許可”的研究經驗比較豐富,此前該實驗室的博士生雅各布·馬特森(Jacob Matson)發現,幹細胞的“起源許可”速度明顯快于已分化細胞。
相比分化細胞,幹細胞的染色質環境通常更為疏松。這些背景促使梅柳和團隊提出如下研究假設:疏松的常染色質和緻密的易染色質,是否也在“起源許可”過程中存在差異?如果存在差異,那麼對細胞有怎樣的意義?其中的分子機制又是如何?
有了假設,就要建立實驗方法,這一過程非常耗時。因為細胞中的 MCM 大部分遊離于細胞中,隻有一部分 MCM 會加載到 DNA 上,且加載過程是單向不可逆的,而目前并沒有任何可用的實時 MCM 加載追蹤标記物。
為了研究 MCM 加載動态,梅柳不得不先依靠活細胞成像技術,去擷取大量單個細胞的“分子年齡”,并通過免疫熒光染色及共聚焦 3D 成像,進一步測量單個細胞 MCM 加載情況,以根據這些資訊繪制出 MCM 在不同亞細胞核内的加載動态。
同時,大量單細胞成像的資料分析也十分複雜,梅柳的合作夥伴通過各種調試,開發出一系列 Python 源代碼,這時終于實作了在不同染色質環境内,對批量單細胞 MCM 的定量分析。
接下來,便是實驗實施和結論得出的階段。
期間,梅柳對比了 MCM 在常染色質和異染色質的加載動态,發現 MCM 在異染色質的加載過程相對延後,但是最終進入 DNA 複制期時,機關含量 DNA 的 MCM 加載數量相當。
進一步研究後,她發現如果人為縮短 G1 期,會導緻異染色質的 DNA 損傷,不過并不會對常染色質産生影響。這說明,對于維持基因組的穩定性來說,合适長度的 G1 期的極其重要。此外,梅柳還發現了 MCM 在常染色質和異染色質加載差異的分子機制。
疫情導緻研究延遲,“被迫”學會 Python 程式設計
概括來說,此次研究揭示了縮短 G1 期可導緻 DNA 的損傷的其中一個原因。如果開發出可以明顯縮短 G1 期的藥物、并用于 G1 期較長的惡性良性腫瘤細胞,就能損傷惡性良性腫瘤細胞的 DNA,進而促進惡性良性腫瘤細胞的凋亡。
“也就是說,我們為将來抗惡性良性腫瘤藥物的研發提供了一種新的角度和理論依據。”梅柳表示。
同時,她也坦言研究遇到了許多挑戰,尤其首創的追蹤 MCM 加載動态的方法。期間嘗試了許多方法,才優化出最好的方法。
其中一個挑戰是活細胞成像在普通熒光顯微鏡下完成,而固定染色後的細胞最終成像要在另一台共聚焦顯微鏡下完成。
她遇到的難題之一是如何在共聚焦顯微鏡下找到活細胞成像時記錄的細胞,為此梅柳最開始應用了底部帶有網格标記的培養皿,每次都能根據網格位置找到目的細胞群,但是這種培養皿價格昂貴且隻能做一組實驗。
經過與該校顯微鏡中心專業人士的多次讨論,最終決定使用普通活細胞成像的培養闆,但是需要人為在闆底标記一個特殊位置,并設定該位點的坐标軸為(0,0),這意味着其他成像位點相對于該标記也有了自己的相對坐标。如此一來,無論将培養闆轉移到任何顯微鏡下,都可根據這些坐标找到初始成像位點。
對于後續計劃,她表示該研究的實驗手段仍有改進空間。接下來可能會在檢測手段上進一步優化,或采用完全不同的手段,比如利用 DNA 成像技術以便更精确地揭示不同染色質環境下的 MCM 加載動态。
“我是有回國打算的”
梅柳是黑龍江海林人,大學畢業于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制藥工程專業;碩士畢業于哈爾濱醫科大學藥理學專業,師從楊寶峰院士,期間她主要研究心血管疾病;博士畢業于浙江大學基礎醫學院藥理學專業,師從吳希美教授,博士期間以第一作者發表高品質 SCI 論文兩篇(Cancer Letters, 2016; Oncogene, 2021)。
其表示:“我在博士期間的主要工作,在于首次鑒定了 Hippo 信号通路的關鍵激酶 LATS1 的 SUMO 化修飾,對于 LATS1 激酶活性的調控至關重要,并且發現這一修飾決定了 LATS1 的生物學功能的多樣性。”
在博士期間,梅柳曾多次獲得“優秀研究所學生”稱号并獲得國家獎學金一次。目前,她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生物化學與生物實體系從事博士後研究,導師為簡·庫克(Jean Cook)教授,研究方向為細胞周期調控機制。
目前國内對科研越來越重視,科研環境也越來越越好。對于博後出站後的安排,她說:“我是有回國打算的,打算一邊找工作一邊把手上目前在研的課題做完。”
-End-
參考:
1、Mei, L., Kedziora, K. M., Song, E. A., Purvis, J. E., & Cook, J. G. (2022). The consequences of differential origin licensing dynamics in distinct chromatin environments.Nucleic Acids 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