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白居易《長恨歌》
曾經看過一個視訊作者講安史之亂,這人認為安史之亂是唐朝統治階級的内鬥,甚至直接把諸如張巡之類的殉道者,也看作為是殉“唐”者,對其吃人的行為進行大肆批判,認為其吃人守城行為也不過就是為了維護李唐的統治而已。無論是當時的唐朝朝廷,還是民間的百姓(紀念張巡的活動非常多)都對張巡尊重有加,當然,批判者也不是沒有。實際上,這就引出一個問題,安史之亂的性質是什麼?或者說安史之亂究竟是一場漢胡大搏鬥,還是隻是一場唐朝統治階級的内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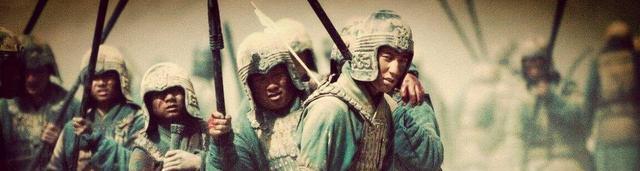
其實先說後者“安史之亂是一場唐朝統治階級的内鬥”其實這一點我都覺得不值一駁,把安史之亂這樣一場滔天巨禍說成是“唐朝統治階級的内鬥”要按這個思路,那...... 算了,你們自己去想吧,把幾千幾百年前的中國社會斬成兩節,并且把上千年的曆史直接粗暴地概括為封建統治者對于絕大多數人的壓迫,而把一切的細節原因抛之腦後,和這種網友說話辯論也隻是浪費口水而已,說穿了這種思維也不過就是毫無文化底蘊的現代人特有的傲慢而已。
而安史之亂是不是一場胡漢生死大搏鬥呢?可以這麼說,不全是,首先安氏叛軍就有大量的漢族士兵,比如安史之亂後被任命為昭儀節度使的薛嵩,此人的祖父就是唐朝名将薛仁貴,此人出自于河東薛氏,算是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北方漢族豪門,還有在潼關打的哥舒翰老頭屁滾尿流的崔乾佑,此人也是漢族,後來出賣史朝義的田承嗣也是漢族。安祿山身兼範陽河東盧龍三鎮節度使,受其影響的部隊達到15萬人,其中,漢族士兵肯定占大多數。
唐王朝的擁趸卻有非常多的胡人,比如斬殺劉龍仙的白孝德,郭子儀手下的名将仆固懷恩,甚至唐中前期令人頭痛不已的吐蕃名将論欽陵後代都已經為唐朝效力,薛仁貴的後代反而追随安祿山。
但是能就此否認安史軍事集團的異域色彩嗎?當然不能,我們知道唐朝軍隊中的胡人是很多的,雖然安史軍事集團在反叛之前名義上屬于大唐這個漢族政權,其核心組成卻是多民族的,我們以安史之亂後,安史叛軍舊部河朔三鎮為例。
所謂河朔三鎮指的是範陽節度使、成德節度使、魏博節度使三個節度使。範陽(又稱幽州或盧龍,在今天的河北省北部包括北京一帶)、成德(今天河北省的中部)、魏博(在今天的河北省南部、山東省北部)。成德鎮初設于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一直到九世紀初,數任成德節度使竟然沒有一位是漢人,基本都來自于契丹和奚這兩個民族。盧龍節度使和魏博節度使則以漢族居多,其中安史之亂後的第一任盧龍節度使李懷仙為鮮卑族人。
安祿山的核心親衛被稱為“曳落河”這是突厥語,意為“健兒”“養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餘人為假子”。
普通士兵以河北燕地漢人為多數,但是胡人比例依然很高。《舊唐書安祿山傳》記載“(天寶十五年)十一月,反于範陽,矯稱奉恩命以兵讨逆賊楊國忠。以諸蕃馬步十五萬,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裡。”由此可見追随安祿山的胡人也絕不在少數。而張巡守衛睢陽時“分别其衆,妫、檀及胡兵,悉斬之;荥陽、陳留脅從兵,皆散令歸業。”從這裡也可以窺見安史亂軍中胡人的比例。
而安祿山不僅是混血(突厥粟特)胡人,自身也頗具異域色彩,如姚汝能《安祿山事迹》雲“每(胡)商至,則祿山胡服坐重床,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羅拜于下,邀福于天。祿山盛陳牲牢,諸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引見諸賈,陳犧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一股中亞味道撲面而來。史思明,孫孝哲之流就更不必說了。
而在安史之亂前,河朔地區的胡化傾向已經十分明顯《舊唐書·地理志》記載:“自燕州以下十七州,皆東北諸蕃降胡散處幽州、營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無所役屬”結果,安祿山反叛後就“驅之為寇,遂擾中原。”即使是安史之亂之後,河朔地區仍然胡化傾向嚴重,唐文宗年間的大臣史孝章勸谏其父時說“大河之北号富強,然而挺亂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赀,非痛洗溉,竭節事上,恐吾踵不旋禍且至。”中晚唐時期,河朔居然被指為“若夷狄然”。
實際上,大多數古代王朝的邊境地區都是農耕與遊牧漁獵的雜處地區,而且局勢動蕩,中原王朝的邊民不但很容易被胡人擄掠而去,而且更容易受到胡人風氣的影響,也就是所謂的胡化,而河朔地區本來就散布着大量投降唐朝的胡人,再加上唐代天寶以後邊鎮的軍事實力日益強大,胡人、漢人都被吸收進這些不斷擴張的暴力軍閥集團之中,實際上就是當地軍民的胡化過程。最令人痛心的是,五代十國後,燕雲十六州淪入遼國之手,又加上金元兩代的統治,胡人之風益盛,直到明太祖朱元璋重新奪回幽燕之地。
現在我們可以給安史軍事集團下一個定義:一個起于中國東北(注意是中國的東北部地區,并不完全和現代意義上的東三省重合)的一個混亂的,頗具異域風格多民族軍事集團。而這樣一個軍事集團自然是野蠻的,而唐朝廷之惡,則在于其自身的虛弱,為了維護自身統治不擇手段,甚至不惜出賣百姓給回纥人劫掠,但總體來說,民心依舊在唐。
感謝您的閱讀,如果覺得本篇文章對你來說有幫助的話,别忘了點贊、評論、轉發和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