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地理的關系,是我國傳統地理文化的一大特色。今天的人們,面對美景,也常常萌生詩意,也會來上幾句。文化學者說,文化不是憑空存在,它的載體是人,在人的行為中,在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中。的确,好好想一想,所謂《詩經》的地理本質,其實源于人本身。”北京大學教授唐曉峰如是說。
近日,《三聯生活周刊》封面故事結集而成的《詩經地理》一書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全書主要講述與《詩經》相關的山、水、植物三個方面的話題,以《詩經》這部經典傳世文獻記載為線索,以其中提及的地理要素作為切入點,将先秦時代的曆史與文獻記載相結合,同時又不斷切換鏡頭,從曆史走進現實,從現實反觀曆史。各篇文章均來自周刊記者的采寫,既有記者的視角,也有受訪者的觀點,較為客觀生動地展現了“詩經地理”這一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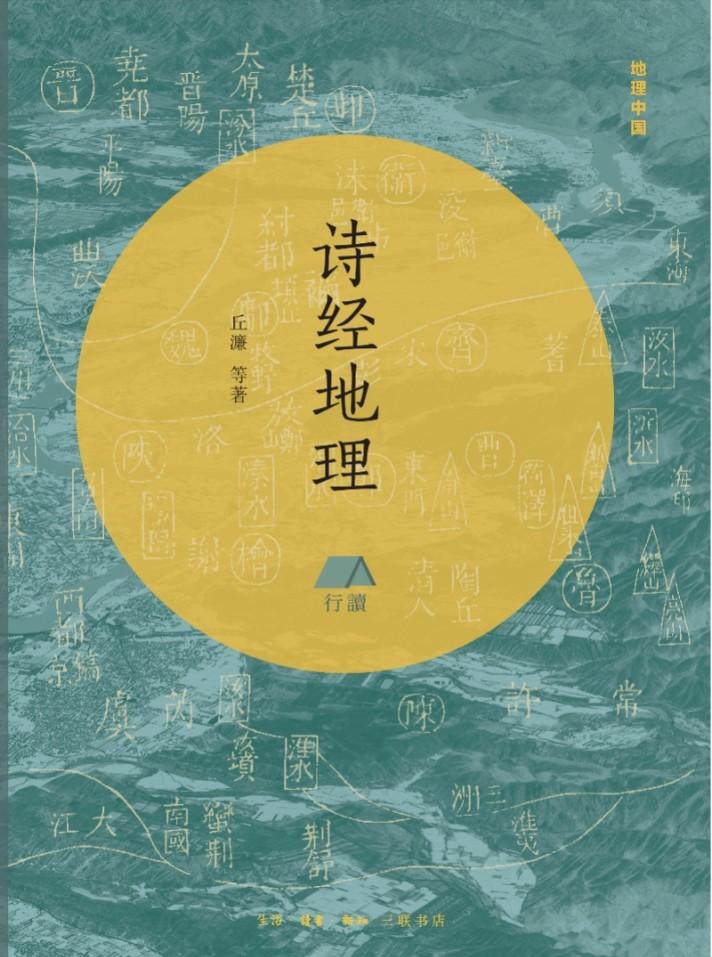
以空間寫時間的方法論
在《詩經地理》的正文前,收錄《三聯生活周刊》主編李鴻谷寫的一篇題為《地理作為方法論》的序言。在序言中,他提到了《三聯生活周刊》逸出新聞正常操作之外,自我意識開啟,始自封面故事“毛澤東地理”。他提出了“以空間寫時間”,把媒體人物報道的“通史”體例—用時間順序建構叙事邏輯的舊例打破,改由基于地理/空間人物活動的“斷代史”組合。
他進而提到:“在更長的時段裡觀察、思考空間尤其更大尺度地理的因素,是一種方法論。舉凡山川、河流、土壤、氣候、溫度、濕度、陽光向背、雨水多寡……種種生存條件與資源系統,既促進人之想象,也限制人的行為,它是核心要素。”讀者可以看到,李鴻谷此文并非專為《詩經地理》而寫,乃是針對一個文叢——地理中國,撰寫的總序,故其所謂方法論将貫穿于《詩經地理》之後、文叢所收的全部圖書。
回到《詩經地理》上來。這本書緣起于《三聯生活周刊》副主編曾焱在北京的一次觀展經曆。據曾焱在本書的《後記》裡回憶,在一個攝影展的入選作品中,她注意到一組黑白攝影,作品名叫《詩山河考》,介紹裡說,攝影師塔可用了4 年時間去尋訪《詩經》裡提到過的故地,以鏡頭來想象和再現一部分在《詩經》裡被吟詠過的畫面意境。“出于當記者的職業毛病,我們時刻都在為采訪找選題。當時我就想,攝影師希望呼應《詩經》的詩意,如果以采訪與記錄的報道方式,做一組文字尋訪的《詩經》地理,會不會是另外一種故事?記者可以通過行走,觀察,訪談,盡可能深入肌理去了解古中國的精神世界,同時,也能看見作為對照的當下中國更貼近現實的部分。”
曾焱的想法到了2019年終于實作。當年春天,《三聯生活周刊》5 位文字記者,加上5 位攝影記者,以涉足5 個省份的細密踏尋、深入采訪,完成了一組紮實的封面故事:2019 年第24 期,《詩意中國: 尋訪〈詩經〉的山、水、 植物》。這是以空間寫時間方法論的又一次嘗試,也是《詩經地理》一書的文本基礎。
尋找通往《詩經》時代的入口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錄的詩篇從西周初年,綿延到春秋中葉,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所描述的時代已太久遠,什麼才能讓我重回那個中國文化的純真年代呢?如果說《詩經》中描述過的物事至今仍有蹤迹、名目可作比照,很可能隻剩下了大山、大河與植物。它們既是相對恒定的自然物,塑造了一地的生活形态,也參與塑造了一地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核心。于是山、河、植物成為我們為《詩經》地理梳理出來的三條脈絡,像一副骨架,搭起了全書的主體結構。就像本書作者丘濂所說:“古今不變的,有人情,也有江河。”
全書依據的文本是《詩經》,選擇的對象是《詩經》中的山、水、植物,方法論支援的方式是踏訪。對踏訪地的選擇,創作團隊有一個重要标準,即并非單純的風景地理,必須在過去和現在都有人之生生息息。人的生存方式、經濟、地理,決定發現的範圍。
最終,在《詩經》描述的山地裡面,選擇了首陽山、泰山、宛丘、終南山和随棗走廊;而河流,選的是淇水、漢水、渭水、汶水和汾河。除了踏訪,記者們還做了大量曆史閱讀和學者采訪,但是,在文字中所呈現的山水格局和人情故事,其描述的起點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它來自記者以客觀視角進入的當下與現實環境,而不單純是文本及其演繹。曾焱寫道:“我們希望能夠在先民和自然的關系之中,在打開時間的無數層覆寫之後,去接近發現一點點中國文化的基因密碼;通過遺址辨析、史料發掘,更重要的是通過記者在現實中的實地踏訪,将圍繞山地、河流所發生的文化史、生活史,一層一層打開。”
用行走喚起這片國土的詩性
在12月11日舉行的“找尋通往先秦時代的入口——《詩經地理》新書分享會”上,《三聯生活周刊》的副主編、《地理中國》文叢的副主編曾焱談到,以前《三聯生活周刊》做過不少以《西遊記》《紅樓夢》等經典文本為出發的報道。但當時還是從文本到文本,以文本分析為采訪的主要方法。此次借用了社會報道的地理方法論,從文本出發,但是地理是架構,在中間加入記者的人文觀察和記錄。
“找尋通往先秦時代的入口——《詩經地理》新書分享會” 曾焱與董梅
由于《詩經地理》的部分探訪地與中國考古事業密切相關,曾焱認為,五組人馬、曆時近半個月的采訪,更像是一場“文化考古”。“我們希望記者同僚汲取考古的方法論。考古實際上也是有一個典籍和物質存在的兩相對照,而且它一定要找到中間可靠的聯系,而不僅僅是從文本出發得出結論。這就是我們在整個《詩經地理》踏訪過程中對記者最基本的要求:一定要有腳踏實地的方法,一定要有來自學者、來自典籍但同時也是來自當下記者觀察的内容,而不僅僅是一些想當然的推測,這也是我們文章的支撐所在。”
如今關于《詩經》的各類著作早已汗牛充棟,但曾焱認為,記者平實理性的視角,賦予了《詩經地理》獨特的價值。
中國古典文學學者、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董梅副教授也走在《詩經》的踏訪之路上。在《詩經地理》新書分享會上,她談到,幾年前,她在學校開設《詩經》課程,希望從器物、飲食、服飾、動植物等各種不同次元來對古老的詩經文本進行還原。但做到以上這些,董梅覺得還不夠。
“既然十五國風,國本身是地域,是以它是直接來源于土地,而每個諸侯國我們基本可以根據史料梳理出範圍和國史。是以那個時候我就開始有一種想法,我希望能夠到生成這些詩的土壤上去,到達那個空間,雖然我們無法傳回那個時間,但是到達那個空間之後,至少可以對國土有所了解。”
最初做這件事情,學術性還原文本是一個目的,同時她還帶有一個比較理想性目的。她在課堂上對學生說,“希望每一個人能夠通過自己的行走喚醒這片國土的詩性。我們每一天所寄身的尋常的土地,都是曾經孕育過詩的土地。”
2012年春天,清明節剛過的時候,以《詩經·國風》中《鄭風》為研究對象,董梅去到溱水、洧水兩條河流之間,進行了第一次對《詩經》的田野調查。她回憶說:“我的方法當然第一是文本,然後是史集,但是最重要的在這個前提的準備之下,到那片國土去,做一種再閱讀。但其實後來發現,它已經超越了閱讀,它帶給我的不僅僅是詩經本身,而是對這片國土的重新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