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諾曼·萊布雷希特/文 石晰颋/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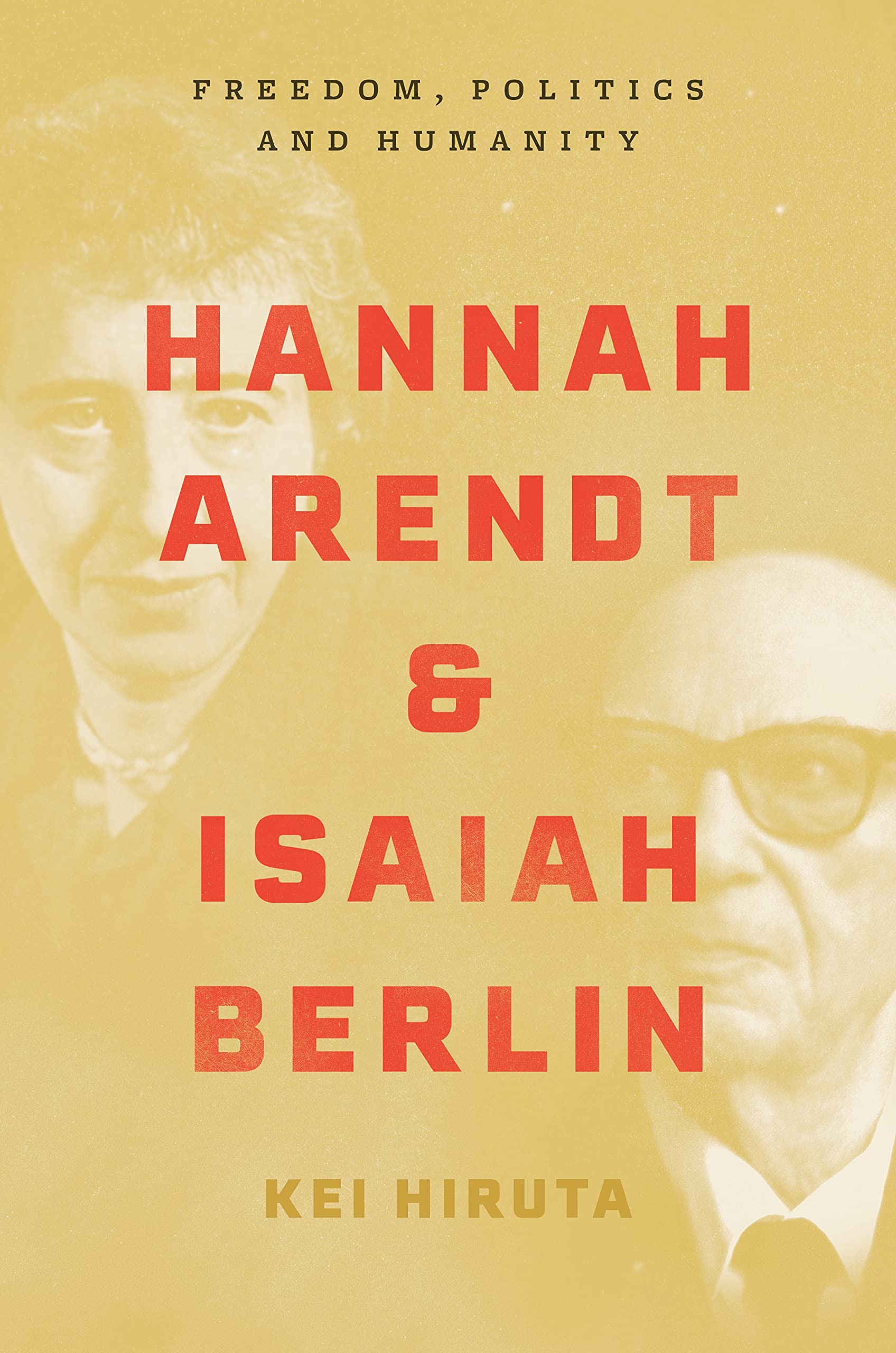
Hannah Arendt and Isaiah Berlin, Kei Hirut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ovember 2021, 288pp
Critical Lives: Hannah Arendt, Samantha Rose Hill, Reaktion Books, October 2021, 230pp
在新冠疫情之前的靜好時代,我曾經飛去一座德國小城看一部描繪兩位哲學家之間愛情的歌劇。這段愛情絕非柏拉圖式。漢娜·阿倫特當時十八歲,沒有父親,尚是處女。馬丁·海德格爾已經三十多歲,已婚并有兩個兒子,是他所在學科的領軍者。在現代話語中,這是一個發生于校園中的典型#MeToo場景,是對信任和責任的濫用。
阿倫特并未如此提及此事;實際上,她成功保證了讓這件事在她去世之前無人知曉。但這場老師對學生的性掠奪給她留下了終生的影響。現如今我們對她的生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是時候重新評估阿倫特了,在極權主義研究領域她是一位主要的哲學家,其影響力塑造了對這個領域的認識,她又堪稱一條出色的變色龍,會将自己轉變為納粹的智性辯護人。
海德格爾在生活和思想之間劃分了一條界線。他告訴學生,“亞裡士多德出生、工作、然後死去,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他的思想”。艾拉·舍裡弗的歌劇《平庸的愛》投射了他的一些觀點,即人類個體,哪怕是怪物,也是無趣的。
平庸是一個關鍵詞,這個名詞使阿倫特在國際上聲名狼藉。她為《紐約客》撰寫了記錄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的冗長報道,标題為“平庸的惡”。艾希曼是希特勒大屠殺的首席執行者,一個将數百萬男女兒童送入死亡集中營的官員。在漢娜·阿倫特看來,即使以希特勒時代逃離德國難民的角度進行觀察,艾希曼的形象,隻是一個無聊的官僚,一個無名小卒,“既非變态也不暴虐……正常得可怕”。她認為,根據法律和邏輯,他不值得被逮捕、審判或處決。
她的立場激怒了道德哲學家,使她暴露在一群前網際網路時代的抱持着不成熟觀念的私刑暴徒之前。阿倫特既沒有退縮,也沒有回避。她對她的摯友瑪麗·麥卡錫這麼說:“痛苦,隻是存活的另一種方式。”
薩曼莎·羅斯·希爾的新傳記将阿倫特重新定位為現代的女權主義英雄,“高标準、不退縮、有主見”,随時準備在她進入的領域中對抗男性的統治地位。從她在美國的學術生涯中期開始,她開始将自己描述為一名政治寫作者,而非哲學家。
她會說:“被人稱贊是件好事,但被人了解就更好了。”希爾博士是巴德學院漢娜·阿倫特中心的助理主任,她認為,“阿倫特的作品如今已經成為我們共有的文化遺産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在其中參考考證,以幫助我們達成了解”。不是所有人都會同意這樣的評價。
即使經曆了那麼長的時間——阿倫特于1975年去世——她所點燃的怒火仍然會燒着人的眉毛。一項新的哲學研究審視了她與文雅有禮的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爵士的關系,描述了他們1941年在紐約的第一次會面,可謂一見成仇。而這關系還會變得更糟。倫敦的費伯出版社在1958年詢問伯林,他們是否應該繼續推出新版的阿倫特著作《人的境況》,伯林的回答堪稱經典的拆解。“我不推薦任何出版商購入這本書的英國版權,”他如是答複,“對這本書有兩點意見:它不會暢銷,而且它也不是本好書”。而這僅僅是用來熱身的開場白。在将這本書的内容一一粉碎之後,在報告的最後,伯林又回到了對“好”的确切含義的沉思。他繼續寫道:“阿倫特博士在談到道義德行時寫道(第75頁),‘基督教對好的要求’是‘荒謬的’。那麼要求一本書是好的也同樣‘荒謬’嗎?讓我們希望她也這樣認為。那麼有人告訴她的這本書不好的時候她也不會在意了。”在由寫作者遭遇到的各種拒信組成的漫長而有趣的清單中,這封回信也堪稱是所有拒信中最為斬釘截鐵的一例。
這兩位創造性思維的巨人之間的關系迄今為止仍然少為人知,但十分令人着迷,這不僅是因為他們之間的激烈對立,還因為把他們對比來看,就能發現他們既相似又相悖。他們都來自于波羅的海之濱的猶太家庭,阿倫特在普魯士的柯尼斯堡(現在的俄羅斯加裡甯格勒),伯林來自拉脫維亞的裡加。阿倫特的父母對宗教漠不關心,而伯林則知道他祖上有參與路巴維茨運動的拉比。阿倫特的父親死于梅毒,随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兩件事打亂了她的少年生活,并使她遷往柏林。
伯林在聖彼得堡時目睹了窗外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并滿懷喜悅地漂流到倫敦的一所私立學校。阿倫特先後在馬爾堡和海德堡大學深造,隻講德語,流亡異國後努力學習英語。伯林除了作為母語的俄語,也純熟于拉脫維亞語、德語、意第緒語、希伯來語、法語、英語和意大利語。浮華使他愉悅,在出任科文特花園皇家歌劇院董事會一員時,他曾寫下關于威爾第歌劇的博學論述。阿倫特不曾有過這種瑣碎愛好,也不好閑言碎語。伯林是牛津大學的教授,而她是西北大學和瓦薩大學的講師,從未獲得過終身職位。他們幾乎在每一個方面都是天造地設,針鋒相對。
日裔丹麥學者蛭田圭對這兩位1941年的紐約相遇進行了出色的分析,阿倫特當時是一個身無分文的難民,從美國的猶太複國主義組織那裡領取津貼,與她沒有工作的丈夫和受撫養的母親住在租來的兩間房間裡。伯林在當時則是丘吉爾政府的特派代表,被派往華盛頓和紐約去施加影響力,并收集資訊。兩人在握手之後,阿倫特就針對伯林所謂的對猶太複國主義事業缺乏承諾的問題對他加以批判。身為哈伊姆·魏茨曼(以色列第一任總統,猶太複國主義的發起人之一)的長期朋友,伯林不屑一顧地說她太瘋了(“fanatical”)。
八年後,阿倫特的著述已經被廣泛閱讀,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也即将完稿。1949年春季的一次會議上,哈佛大學的曆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以他與肯尼迪的關系而聞名)促成她與伯林再度會面,這是一個災難性的誤判。施萊辛格總結說,她“對他來說太莊重,太有預示性,太過日耳曼,太過黑格爾”,伯林後來在《泰晤士封包學增刊》上把阿倫特列為本世紀最被高估的作家之一,小阿瑟·施萊辛格還為此恭賀伯林。伯林在第二次見面時震驚地發現,阿倫特反對新成立的猶太國家:“她批判了以色列。”
如果沒有對艾希曼的審判,這一切本應逐漸偃旗息鼓,隻剩在學術期刊上的零星交鋒。以色列情報部門(在聯邦德國的幫助下)追蹤艾希曼的足迹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并在那裡将他綁架,押上前往以色列的飛機,并指控他犯有種族滅絕罪。阿倫特在1933年曾經身陷蓋世太保的牢房,後來又險些沒能将她的母親從德國解救出來,面對“最後一次目睹納粹頭目真身的機會”,她就此采取行動。
漢娜·阿倫特
那場審判為時八個月,而她隻在1961年4月旁聽了一周多一點的時間。她将她所看到的大部分内容貶低為“廉價的把戲”,并質疑這一過程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整個事件是如此該死的平庸,難以描述地低級與令人厭惡”,她回家後對丈夫如是說。經過兩年的醞釀,她的報告于1963年2月和3月刊登在《紐約客》雜志上,不久後結內建書。由此引發的反應可謂爆炸性。兩位猶太文學活動家歐文·豪和萊昂内爾·阿貝爾在曼哈頓市中心的一家酒店組織的讨論會,被瑪麗·麥卡錫形容為“大屠殺”,詩人羅伯特·洛威爾将其比作“對家族中的一個被抛棄的成員施以石刑”。以色列負責起訴艾希曼小組的一名成員發表了長達四百頁的反駁意見。
在阿倫特的各項聲明中引起最大反感的是:她聲稱如果沒有猶太政要在各地提供協助,艾希曼無法屠戮如此多的人,這個根基不穩的主張忽略了艾希曼對那些人及其家屬的完全控制。
阿倫特一如故我,堅守自己的每字每句。她在十年後表示:“我對(艾希曼)身上明顯的淺薄感到震驚,這使得我們無法追溯他的行為的無可争議的邪惡,去發掘任何更深層次的根源或動機。這些行為是可怖的,但其執行者——至少是現在受審的那個卓有效率的執行者——是非常普通的、平凡的,既非惡魔也不可怖。”
我懷疑,在這樣的認識的背後,隐藏着别的東西——海德格爾的沉悶學說。希爾寫道,阿倫特曾經在1946年飛往德國去見她的老師,而為了在國際上尋求正名,海德格爾提出要離開元配妻子與她結婚。盡管阿倫特拒絕了,但仍在他的控制之下,無法承認她的那位傑出的施虐者曾為希特勒唱贊歌,并将優秀的同僚喂飼給納粹的狼群。她從未擺脫過他的魔咒,還為他八十歲生日發表過一篇洋溢贊美的文章。海德格爾的敗壞道德蒙蔽了她的思維,并在面對艾希曼審判時嚴重歪曲了她的判斷。
當那場風波爆發時,伯林并未批評阿倫特,他在給瑪麗·麥卡錫的信中還私下對她的想法表示了某些同情。但他也鼓勵《文彙》雜志發表了阿倫特與猶太神秘主義學者格朔姆·肖勒姆之間的尖銳筆戰,後者指責她對自己的人民缺乏愛。阿倫特的回答是,她永遠不可能愛某一群人民,隻能愛她的朋友。伯林最終同意了肖勒姆的觀點,認為她沒心沒肺,而她對艾希曼審判的記述“幾乎以譏諷和惡意的語氣”為特征。
我們在此可以見證阿倫特的非凡能力,男人因對她的憎恨團結在一起。在一組那些男人間的信件的新譯本中(Polity Press, Cambridge),肖勒姆和法蘭克福學派社會學家阿多諾通過他們對阿倫特共同的抵觸實作了完美的和諧,因為阿倫特曾寫過一篇關于這兩人的共同朋友本雅明的有趣文章,并希望被承認為研究本雅明的權威。阿多諾咆哮:“在漢娜·阿倫特的問題上,我是不會妥協的,不僅是因為我自己對這位女士不屑一顧,我覺得她就是個老洗衣婦,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本雅明如何看待她。”
在這裡我們是否能發現某些其它東西?在哲學的世界裡,阿倫特是一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來遏制的局外人,最好是被隔絕在外,而以賽亞·伯林以及他那些穿着長袍的快樂男同行們則在高桌邊笙歌暢飲。如此交流中的性别恐懼症有時相當令人窒息。
在一切都結束後,阿倫特将永遠因為那個可怕的詞“平庸”而被牢記,事實上她已經在所有的時代中改變了這個詞的含義,使之與邪惡一緻。就伯林而言,他留下了大量經久不衰的作品,從他作為基石的《卡爾·馬克思》到《自由論》。他的刺猬和狐狸的寓言會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晚餐聚會遊戲而經久不衰。他的低吟“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會萦繞不絕。盡管阿倫特是個刺頭,但她可能确有一大知——個人的自由必須超越意識形态,即使此人不可原諒。伯林盡管對猶太複國主義、英國和歌劇的忠誠毋庸置疑,在艾希曼的案件中,他還是準備以目的為手段張目。在這個故事裡,狐狸并不總會占上風。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