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至11月,法国当代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应邀访华。与他一生的知己和重要的法国思想家西蒙·波伏瓦(Simon Beauvois)一起加入。他们访问了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印象非常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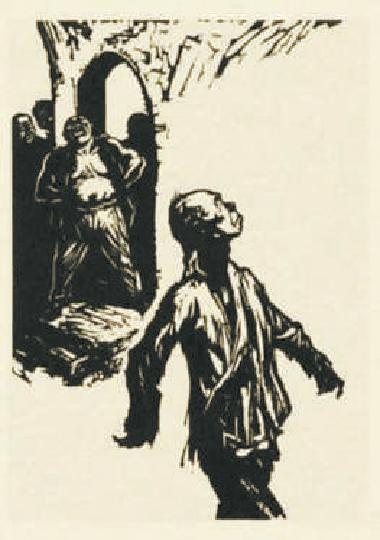
木刻 AQ
鲁迅的杂草
《长征》中文版
回国后,萨特在法国《观察家周刊》上发表了《我们看到的中国》,并表示他将写一本关于中国的特著。这个愿望后来没有实现。然而,在1957年,波瓦出版了她关于中国对中国的看法的专著《长征》,其中包括她对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的评论。
"他离契诃夫更近了。
鲁迅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最著名的作家。今天,他被视为中国的高尔基......"波沃斯对鲁迅的作品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文章中,她介绍了《呐喊》、《呐喊》、《新故事》、《拾花》等文学作品。不过,波波瓦并没有停留在一个简单的概括上,她也通过具体作品,鲁迅的意义得到了发掘。
"鲁迅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愚蠢的农民、沮丧的知识分子、吸烟者、乞丐——都像AQ一样迷茫迷茫,经济状况和传统道德让他们无处可逃:有的放弃了希望,有的人听神的话,几乎所有的斗争都无所作为,从虚假的想象中寻求安慰,或者诉诸于摧毁他们的迷信。波沃斯对AQ整体情况的描述是准确而深刻的——无论是在表面上还是在深处,都被她捕捉到,并在笔中清晰地呈现:"这些受害者的软弱,一半放纵,一半屈服于自己的不幸,这是鲁迅短篇小说中绝望的特征。"
波瓦还写道:"中国人把他比作高尔基,但我发现他更接近契诃夫。"说实话,鲁迅的新颖结构特征和人物选择确实更接近契诃夫。人们称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应该基于他对下眼界的关注,以及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支持,类似于高尔基的态度。
鲁迅的小说,和契诃夫的作品一样,注重小人物的生存,但鲁迅能让人感受到内心的情绪。这应该证明鲁迅受到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通过叙事来表现内心的心理特征。鲁迅将外来文化的吸收与中国传统的传承融为一体,正是波沃斯所指出的:"他(鲁迅)从不用分析词来挖掘人物的心理活动,而是消除了人物内心世界与外在渗出之间的所有距离。"
作为一名艺术家,波瓦的感知确实敏锐而丰富。
文学与革命之间
分析一个作家并解释他的作品的内容和艺术特征当然是不够的。作为思想家,波瓦在对鲁迅的评论中,更注重自己思想的演变。
首先,波瓦斯捕捉到了鲁迅的作品与他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在波沃斯看来,革命的挫折给了鲁迅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他变成了一个"顽固的悲观主义者"。"他认为,对更美好明天的幻想只不过是海市蜃楼,不值得谈论......"
然后,波沃斯引用了鲁迅《尖叫的自我秩序》中的一段话,即鲁迅说,他曾在小说《药业》中为革命"玉儿"的坟墓加了一个花圈;波瓦继续评论道:"的确,在他的两个故事中,鲁迅完全被注入了一种无法察觉的乐观情绪。但是,在他看来,他认为最轻微的事实发生了变化,这与文学的要求背道而驰:他认为艺术作品是真诚的绝对证明。他从未退出过这个职位,他仍然需要一场革命。"
这句话应该引起中国评论员的注意。一个作家可能有他的文学观点,但他的创作并不局限于自己的圈子,偶尔甚至经常逃避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矛盾在冲突的中间,不像写在纸上调解那么容易,他可能一辈子都在矛盾中。
波沃斯还认为,鲁迅的悲观主义不是无所作为的借口。鲁迅在北京任教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支持学生。在他看来:活着是错误的,因为它似乎活着,但正在死去。年轻人必须突破旧笼子。然而,学生有限的抗议活动遭到严重镇压,有些人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后来鲁迅发表文章批评政府,迫害,到广州最热心的革命,并遭遇蒋介石的兵变......这一切,让鲁迅从书本确立的概念中产生了最严重的影响。用波沃斯的话说:"鲁迅此时似乎完全绝望了。"
这种绝望,波沃斯,在《野草》等作品中随处可见。她引用鲁迅1927年的文章《杂草》后说:"对于鲁迅来说,怀疑青春的作用已经到了最深的失望,因为他都是青春的希望。"
Povois非常重视杂草的纯正收藏。卢迅的许多想法都是她从这些颇具感性的话语中挖掘出来的。通过《杂草》,她这样分析了鲁迅的想法:"至于当时的政治,鲁迅并没有放弃希望。然而,他对文学在革命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
在波沃斯看来,虽然作家不再幻想书籍是政治武器,但"他(鲁迅)并不鄙视文学的真正目的:真实地表达世界。事实上,作家只有通过揭示行动与行动分离,才能完成他们真正的使命。鲁迅不再支持逃避现实,他说,有些作家退出了生活的场景,热衷于养花草,谈鸟儿花。但在他看来,文学是人们对生活在他们周围的感受......简而言之,如果你对文学政治给予太多,你就会失去两者。你不能写一本好书,这无济于事。"
对于鲁迅晚期基本上只写散文这一点,波波瓦的理解是:在文学和革命之间,鲁迅最终选择了革命。她还了解到鲁迅晚年的焦点:从那以后,他只写了关于争议的文章,翻译了外国小说。他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普列汉诺夫、法捷耶夫、契诃夫、戈戈里和巴罗哈,他的译文很厚。然而,在波沃斯看来,这些小说和故事是"富有想象力的写作"。
波沃斯对鲁迅的研究不仅限于作家和作品本身,她还描述了鲁迅作品的背景,以及与其他类型作家的概念立场的冲突。早期鲁迅主张文学必须"参与",但鲁迅"对干预的性质和程度存有疑虑"。波瓦斯发现,鲁迅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文学必须有一定的独立性,"他的态度自讨论文学的使命以来就没有改变过。例如,他曾经认为,文学必须是整个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文学不能仅仅属于革命,但只要它所体现的社会受到反叛精神的启发,它就具有革命的印记。"
对波瓦的一些误读
从波沃斯的介绍到鲁迅,虽然比较笼统,但涉及面广;虽然Povois笔还涉及胡石、郭莫罗、于大福、毛敦、林玉堂、老舍等其他笔,但很多都是有限的段落甚至几行,而且大多是与鲁迅接触时提的。我们大概可以认为这是波沃斯自己阅读研究的观点,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鲁迅在现代作家中的特殊地位。
波波依斯特别关注鲁迅的介绍,应该与她的文艺理念颇为相关。和萨特一样,她强烈反对"以艺术换艺术"的主张,认为文学必须干预政治和生活,主张"干预文学"。这与鲁迅的文学观念相当一致。
波瓦写道:"1921年1月,由毛盾、鲁迅领导的文学研究会发表了宣言,肯定了文学的政治作用:'把文学艺术当作享乐游戏或挫折消遣的时代已经结束',倡导反映被压迫者的'血泪文学'。虽然这种说法存在误区,认为鲁迅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但认为鲁迅与这种观点接近或大致相同是现实的。
然而,由于收集信息的困难,Povois有时在使用上显得不那么平衡。一方面,她甚至寻找并引用了没有广泛传播的信息,例如"左翼联盟"的理论纲领和文学研究学会的声明;例如,她说:"1925年,他(鲁迅)发起了《语言丝绸》评论,当时的编辑包括讽刺作家和幽默家林玉堂和小说家老舍。据笔者查找相关信息,老舍表示,"语言丝"编辑系统有误。
此外,她还介绍鲁迅"在南京完成大学学业"。"其实,鲁迅是在南京读江南水利大师学校和矿铁学校,都不是大学。她说,鲁迅等人发起了"左翼作家工会"的组织,鲁迅当选主席,似乎存在误会。鲁迅是"左联盟"常委之一,只能说是领导,并没有担任"主席"一职......但考虑到当时在Povois中收集材料的困难以及文化差异,这些对主题的误读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Povois的介绍更多的是针对当时西方一些对中国有偏见的人,所以内容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并不陌生。但波瓦依斯毕竟是一位敏锐而深刻的思想家,她对鲁迅的评论,其中许多仍然对读者有启发性,也为我们提供了她观察问题方式的新视角。
(原标题:鲁迅在波沃斯眼中的作品)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杨建民
过程编辑: L061
版权声明:文字版权归新京报集团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