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至11月,法國當代著名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應邀訪華。與他一生的知己和重要的法國思想家西蒙·波伏瓦(Simon Beauvois)一起加入。他們通路了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廣州等地,印象非常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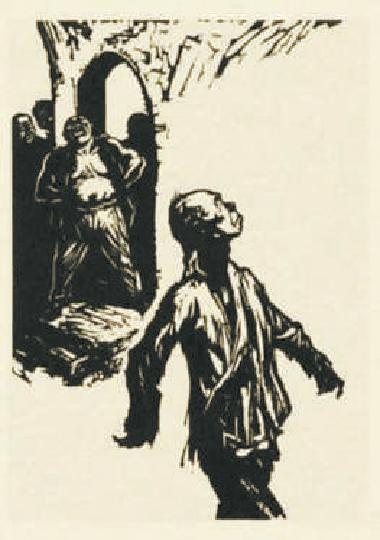
木刻 AQ
魯迅的雜草
《長征》中文版
回國後,薩特在法國《觀察家周刊》上發表了《我們看到的中國》,并表示他将寫一本關于中國的特著。這個願望後來沒有實作。然而,在1957年,波瓦出版了她關于中國對中國的看法的專著《長征》,其中包括她對中國著名作家魯迅的評論。
"他離契诃夫更近了。
魯迅是他那個時代最偉大、最著名的作家。今天,他被視為中國的高爾基......"波沃斯對魯迅的作品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在文章中,她介紹了《呐喊》、《呐喊》、《新故事》、《拾花》等文學作品。不過,波波瓦并沒有停留在一個簡單的概括上,她也通過具體作品,魯迅的意義得到了發掘。
"魯迅小說中幾乎所有的人物——愚蠢的農民、沮喪的知識分子、吸煙者、乞丐——都像AQ一樣迷茫迷茫,經濟狀況和傳統道德讓他們無處可逃:有的放棄了希望,有的人聽神的話,幾乎所有的鬥争都無所作為,從虛假的想象中尋求安慰,或者訴諸于摧毀他們的迷信。波沃斯對AQ整體情況的描述是準确而深刻的——無論是在表面上還是在深處,都被她捕捉到,并在筆中清晰地呈現:"這些受害者的軟弱,一半放縱,一半屈服于自己的不幸,這是魯迅短篇小說中絕望的特征。"
波瓦還寫道:"中國人把他比作高爾基,但我發現他更接近契诃夫。"說實話,魯迅的新穎結構特征和人物選擇确實更接近契诃夫。人們稱魯迅為中國的高爾基,應該基于他對下眼界的關注,以及對無産階級文學的支援,類似于高爾基的态度。
魯迅的小說,和契诃夫的作品一樣,注重小人物的生存,但魯迅能讓人感受到内心的情緒。這應該證明魯迅受到中國傳統小說的影響,通過叙事來表現内心的心理特征。魯迅将外來文化的吸收與中國傳統的傳承融為一體,正是波沃斯所指出的:"他(魯迅)從不用分析詞來挖掘人物的心理活動,而是消除了人物内心世界與外在滲出之間的所有距離。"
作為一名藝術家,波瓦的感覺确實敏銳而豐富。
文學與革命之間
分析一個作家并解釋他的作品的内容和藝術特征當然是不夠的。作為思想家,波瓦在對魯迅的評論中,更注重自己思想的演變。
首先,波瓦斯捕捉到了魯迅的作品與他的思想之間的沖突。在波沃斯看來,革命的挫折給了魯迅一個很大的打擊,是以他變成了一個"頑固的悲觀主義者"。"他認為,對更美好明天的幻想隻不過是海市蜃樓,不值得談論......"
然後,波沃斯引用了魯迅《尖叫的自我秩序》中的一段話,即魯迅說,他曾在小說《藥業》中為革命"玉兒"的墳墓加了一個花圈;波瓦繼續評論道:"的确,在他的兩個故事中,魯迅完全被注入了一種無法察覺的樂觀情緒。但是,在他看來,他認為最輕微的事實發生了變化,這與文學的要求背道而馳:他認為藝術作品是真誠的絕對證明。他從未退出過這個職位,他仍然需要一場革命。"
這句話應該引起中國評論員的注意。一個作家可能有他的文學觀點,但他的創作并不局限于自己的圈子,偶爾甚至經常逃避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沖突在沖突的中間,不像寫在紙上調解那麼容易,他可能一輩子都在沖突中。
波沃斯還認為,魯迅的悲觀主義不是無所作為的借口。魯迅在北京任教時,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支援學生。在他看來:活着是錯誤的,因為它似乎活着,但正在死去。年輕人必須突破舊籠子。然而,學生有限的抗議活動遭到嚴重鎮壓,有些人甚至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後來魯迅發表文章批評政府,迫害,到廣州最熱心的革命,并遭遇蔣介石的兵變......這一切,讓魯迅從書本确立的概念中産生了最嚴重的影響。用波沃斯的話說:"魯迅此時似乎完全絕望了。"
這種絕望,波沃斯,在《野草》等作品中随處可見。她引用魯迅1927年的文章《雜草》後說:"對于魯迅來說,懷疑青春的作用已經到了最深的失望,因為他都是青春的希望。"
Povois非常重視雜草的純正收藏。盧迅的許多想法都是她從這些頗具感性的話語中挖掘出來的。通過《雜草》,她這樣分析了魯迅的想法:"至于當時的政治,魯迅并沒有放棄希望。然而,他對文學在革命中的作用持懷疑态度。"
在波沃斯看來,雖然作家不再幻想書籍是政治武器,但"他(魯迅)并不鄙視文學的真正目的:真實地表達世界。事實上,作家隻有通過揭示行動與行動分離,才能完成他們真正的使命。魯迅不再支援逃避現實,他說,有些作家退出了生活的場景,熱衷于養花草,談鳥兒花。但在他看來,文學是人們對生活在他們周圍的感受......簡而言之,如果你對文學政治給予太多,你就會失去兩者。你不能寫一本好書,這無濟于事。"
對于魯迅晚期基本上隻寫散文這一點,波波瓦的了解是:在文學和革命之間,魯迅最終選擇了革命。她還了解到魯迅晚年的焦點:從那以後,他隻寫了關于争議的文章,翻譯了外國小說。他向中國讀者介紹了普列漢諾夫、法捷耶夫、契诃夫、戈戈裡和巴羅哈,他的譯文很厚。然而,在波沃斯看來,這些小說和故事是"富有想象力的寫作"。
波沃斯對魯迅的研究不僅限于作家和作品本身,她還描述了魯迅作品的背景,以及與其他類型作家的概念立場的沖突。早期魯迅主張文學必須"參與",但魯迅"對幹預的性質和程度存有疑慮"。波瓦斯發現,魯迅一直堅持自己的立場:文學必須有一定的獨立性,"他的态度自讨論文學的使命以來就沒有改變過。例如,他曾經認為,文學必須是整個社會的一種表現形式。雖然文學不能僅僅屬于革命,但隻要它所展現的社會受到反叛精神的啟發,它就具有革命的印記。"
對波瓦的一些誤讀
從波沃斯的介紹到魯迅,雖然比較籠統,但涉及面廣;雖然Povois筆還涉及胡石、郭莫羅、于大福、毛敦、林玉堂、老舍等其他筆,但很多都是有限的段落甚至幾行,而且大多是與魯迅接觸時提的。我們大概可以認為這是波沃斯自己閱讀研究的觀點,同時,我們也能感受到魯迅在現代作家中的特殊地位。
波波依斯特别關注魯迅的介紹,應該與她的文藝理念頗為相關。和薩特一樣,她強烈反對"以藝術換藝術"的主張,認為文學必須幹預政治和生活,主張"幹預文學"。這與魯迅的文學觀念相當一緻。
波瓦寫道:"1921年1月,由毛盾、魯迅上司的文學研究會發表了宣言,肯定了文學的政治作用:'把文學藝術當作享樂遊戲或挫折消遣的時代已經結束',倡導反映被壓迫者的'血淚文學'。雖然這種說法存在誤區,認為魯迅是文學研究會會員,但認為魯迅與這種觀點接近或大緻相同是現實的。
然而,由于收集資訊的困難,Povois有時在使用上顯得不那麼平衡。一方面,她甚至尋找并引用了沒有廣泛傳播的資訊,例如"左翼聯盟"的理論綱領和文學研究學會的聲明;例如,她說:"1925年,他(魯迅)發起了《語言絲綢》評論,當時的編輯包括諷刺作家和幽默家林玉堂和小說家老舍。據筆者查找相關資訊,老舍表示,"語言絲"編輯系統有誤。
此外,她還介紹魯迅"在南京完成大學學業"。"其實,魯迅是在南京讀江南水利大師學校和礦鐵學校,都不是大學。她說,魯迅等人發起了"左翼作家工會"的組織,魯迅當選主席,似乎存在誤會。魯迅是"左聯盟"常委之一,隻能說是上司,并沒有擔任"主席"一職......但考慮到當時在Povois中收集材料的困難以及文化差異,這些對主題的誤讀是可以了解的。
當時,Povois的介紹更多的是針對當時西方一些對中國有偏見的人,是以内容對中國讀者來說可能并不陌生。但波瓦依斯畢竟是一位敏銳而深刻的思想家,她對魯迅的評論,其中許多仍然對讀者有啟發性,也為我們提供了她觀察問題方式的新視角。
(原标題:魯迅在波沃斯眼中的作品)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楊建民
過程編輯: L061
版權聲明:文字版權歸新京報集團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或改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