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968年,川端康成因《雪國》、《千鶴》和《古都》等作品“以卓越的感受性,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現了日本人心靈的精髓”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這三部被瑞典文學院重點提到的小說也往往被視為“獲獎作品”及川端康成的代表作(其實并沒有所謂的獲獎作品,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整體成就),而《雪國》則是這三部作品中最受推崇的一部。
《雪國》在叙事上不如《千鶴》珠圓玉潤,在回歸傳統方面不如《古都》徹底,這些無疑都是顯而易見的。但《雪國》卻是川端康成作品中最唯美、最抒情的一部,有論者甚至發出“《雪國》之後再無《雪國》的”感歎。在《雪國》中,與唯美、抒情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徒勞和虛無,川端康成甚至是以被打上“虛無主義”的标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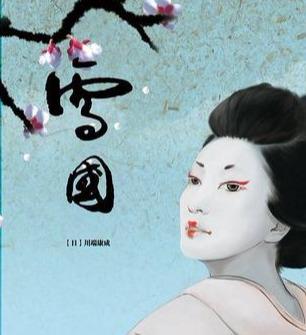
《雪國》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川端康成作品中的“虛無”跟西方的“虛無主義”有較大不同。川端康成在當年的獲獎演講中就曾指出:有的評論家說我的作品是虛無的,不過這不等于西方說的虛無主義;我覺得這在“心靈”上,根本是不同的。
筆者認為,川端康成作品中的“虛無”直接傳承于日本傳統文化中的“物哀”思想。這不僅展現在川端康成對“物哀”及《源氏物語》的推崇上,亦直接展現在《雪國》的文本中,下文即對這兩點展開論述。
1. 川端康成對《源氏物語》的推崇
在1968年的獲獎演說《我在美麗的日本》中,川端康成對以《源氏物語》為代表的平安朝文化作出了高度評價:
日本吸收了中國唐代的文化,爾後很好地融彙成日本的風采,大約在一千年前,就産生了燦爛的平安朝文化,形成了日本的美……特别是《源氏物語》,可以說自古至今,這是日本最優秀的一部小說……《源氏物語》是深深地滲透到我的内心底裡的。在《源氏物語》延續幾百年,日本的小說都是憧憬或悉心模仿這部名著的。
川端康成
在其他不同場合,川端康成更是多次強調“平安朝的物哀成為日本美的源流”、“悲哀與美是相通的”。在《追悼島木健作》中,川端康成甚至這樣寫道:從此以後,除了日本悲哀的美之外,一個字都不想寫了。透過這些言論,不難看出“物哀”、“悲哀”在川端康成那裡是極為重要的美學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物哀”并不等同于“悲哀”,它是一個比“悲哀”更廣的概念。川端康成格外着重于“悲哀”的一面,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因為“哀感”是“物哀”最突出的特質,二是因為受到了其自身“孤兒根性”的影響。川端康成兩歲喪母三歲喪父,七歲時失去祖母、十歲時失去姐姐,十五歲時又失去祖父這個唯一的親人,這些經曆使川端康成過早地感受到了生命的無常和短暫,使得“悲哀”的種子早早地在他心中生根發芽,以緻伴随一生。
川端康成和女友,兩人已訂婚,但女方毀掉婚約,這對川端康成亦造成極大打擊
2. 何為“物哀”?
在《源氏物語》中,“哀”出現了一千多次,“物哀”出現了十多次。不過“物哀”作為一種文學或美學思想,到了江戶時代才被确立。當時複古國學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長在分析日本傳統文學作品時指出:由神代至今,及至末世無窮,吟詠之和歌,不外乎物哀一詞;至于 《伊勢 》、 《源氏》等物語,若探尋其本意,則亦可以物哀一言蔽之。
在《紫文要領》中,本居宣長對“物哀”做了較為詳細的解釋:
世上萬事萬物的千姿百态,我們看在眼裡,聽在耳裡,身體力行的體驗,把這萬事萬物都放到心中來品味,内心裡把這些事情的情緻一一辨清,這就是懂得事物的情緻,就是懂得物之哀。
本居宣長畫像
也就是說,“物哀”是一種面對萬事萬物的千姿百态而産生的情感,它并不僅僅局限于“悲哀”,而是高興、欣慰、愉快、憂愁等所有可能産生的情感。受審美心理影響,日本人格外注重體驗及表達“悲哀”之情,《源氏物語》即是一部集中表達“物哀”中“悲哀”之情的著作。
整體而言,《源氏物語》的場景、人物和情節都鮮明地展現了“物哀”思想。《源氏物語》第一卷《桐壺》中即重點描寫了生死離别的場景,桐壺帝雖貴為天皇但卻留不住最心愛的更衣,源氏公子舉世無雙但卻不得不被降為臣籍。在後文中,離别的場景亦曾多次出現。
事實上,《源氏物語》中場景之哀并不僅僅展現在離别等悲傷的場景中,亦展現在諸多歡快的場景中,這主要是通過目睹景物之歡而思及内心之哀完成的。人物和情節之哀則主要展現在源氏和紫姬身上,源氏身世高貴才華橫溢但卻也把握不住身邊的一切;紫姬被養成了完美的女人但卻也不能完全得到源氏,最後更是早早失去了生命。
在描寫紫姬之死的《法事》中,《源氏物語》中的“物哀”之情可謂上升到了極緻。在這一回中,紫姬目睹良辰美景卻倍感凄涼,之後又于盛會之上“最後一次”觀察同輩諸夫人,最後悲賦“露在青萩上,分明不久長;偶然風乍起,消散證無常”,終于天明時分。
筆者稱《法事》一回中的“物哀”之情達到了一個極緻,這絕非誇大其詞。這一回其實展現紫姬“知物哀”的過程,第一步是從“櫻花盛開,天朗氣清”的良辰美景中體驗到“凄涼寂寞”;第二步是在觀察世間種種人相之後痛感自身将要永别人世——然而畢竟隻有我一人最先消滅得影迹全無;第三步是回到與源氏的感情之中,心想:自己死了,不知源氏主君将何等悲恸。
《源氏物語》劇照
這種“物哀”思想亦呈現在源氏及夕霧對紫姬的觀照中。紫姬曾想“出家為尼以遂夙願”,但源氏不肯放手。之後紫姬籌備了盛大的法會,但卻未能使自己“罪障消除”,而源氏亦未能留住紫姬。紫姬的私願“請僧人書寫《法華經》一千部”,這其實和《雪國》中駒子的諸多行為一樣是徒勞的。法會之景雖為盛大及肅穆,但卻并不能使得紫姬内心得到寬慰,這無疑和雪國之景無法救贖島村一樣。此外,《雪國》中虛無、悲哀的審美觀念,亦可在對紫姬死亡之美的描寫中找到源頭。
1. 紫姬的死亡之美和《雪國》的虛無之美
《雪國》虛無、悲哀的審美傾向主要展現在對葉子和駒子之美的描寫上。小說的開頭部分對葉子的描寫即浸透在空靈與虛幻之中:
人物是一種透明的幻像,景物則是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流,兩者消融在一起,描繪出一個超脫人世的象征的世界……燈火就這樣從她的臉上閃過,但并沒有把她的臉照亮。這是一束從遠方投來的寒光,模模糊糊地照亮了她眼睛的周圍。她的眼睛同燈火重疊的那一瞬間,就像在夕陽的餘晖裡飛舞的妖豔而美麗的夜光蟲。
《雪國》劇照
葉子之死則将這種虛無之美推到了極緻:
在葉子痙攣之前,島村首先看見的是她的臉和她的紅色箭翎花紋布和服。葉子是仰臉掉落下來的。衣服的下擺掀到一隻膝頭上。落到地面時,隻有腿肚子痙攣,整個人仍然處在昏迷狀态。不知為什麼,島村總覺得葉子并沒有死。她内在的生命在變形,變成另一種東西。
此時島村忽然想起了在火車上初見葉子時的情景,這頗似《源氏物語》中夕霧在紫姬死後回想起十五年前起大風時無意窺見她容顔時的情景。許多年來夕霧雖不對紫姬抱有非分之心,但亦始終對她念念不忘。在紫姬死後,夕霧竟從她身上發現一種死亡之美:
紫夫人的頭發随随便便地披散着,然而密密叢叢,全無半點紛亂,光彩豔豔,美不可言。燈光非常明亮,把紫夫人的顔面照得雪白。比較起生前塗朱抹粉的相貌來,這死後無知無覺地躺着時的容貌更見美麗。
夕霧沉浸在這種美中,以至于希望自己死去,把靈魂附着在紫姬身上。《雪國》中島村目睹葉子失去生命,卻也并不覺得該為此感到痛楚,而是想起了他和駒子共同度過的歲月,覺得其中充滿一種“說不出的苦痛和悲哀”。
島村、駒子影視形象
2. 源氏、紫姬的悲哀和島村、駒子的徒勞
川端康成曾經對《雪國》的創作心理做出過這樣的表述:《伊豆的舞女》也罷,《雪國》也罷,我都是抱着對愛情表示感謝的心情寫就,這種表現,在《伊豆的舞女》中純樸地表現了出來,在《雪國》中則稍微深入,作了痛苦地表現。
《雪國》中的幾段感情确實都極表現得極為痛苦,駒子傾心于島村但島村卻把她的愛視為一種徒勞;葉子悉心照料行男但行男最終還是早早病逝了;島村被葉子身上的虛幻空靈之美所吸引,但葉子卻終究如車窗裡的燈火一樣可望不可即。
駒子劇照
事實上,《雪國》中的徒勞并不僅僅展現在感情方面,而是展現在人物的種種行為之上。女主人公駒子為了給行男治病淪為藝伎,但她并沒有對生活喪失信心,她堅持記日記、讀小說以及練三弦琴,可是這些行為并沒有給她帶來一個更好的未來,行男之死以及島村對她愛情的漠視其實即已宣告了她種種行為實屬徒勞。島村的種種行為其實亦屬徒勞,他對一切都抱着無所謂的态度唯獨對葉子情有獨鐘,可是葉子卻在答應随他同去東京之後死去了。
《源氏物語》中的源氏和紫姬,他們的一生亦顯得格外徒勞與悲哀。紫姬被源氏撫養長大,被調教成了最完美的女人,紫姬生命的所有意義可謂都在源氏身上,可源氏身邊的女人卻不隻她一個。在源氏與三公主成婚之後,紫姬“多年以來不曾嘗過獨眠滋味,如今雖然竭力忍受,卻還是不勝孤寂之感”。
紫姬心生出家之意,但卻不被源氏許可,最終隻得退而求其次籌辦盛大的法會。櫻花盛開,天朗氣清,良辰美景簡直與佛菩薩居住之地相仿,可是紫姬卻并未因之得到慰藉,而是更覺凄涼寂寞,以緻萬念俱灰。
源氏影視形象
在紫姬死去之後,源氏這樣說道:她多年以來懷抱出家之志,到此臨終之時,不使遂其心願,實甚可憐。此時源氏方才作出決斷令紫姬出家,這不僅展現出源氏的自私,更展現出他的悲哀。紫姬其實并不僅僅是紫姬,源氏還将對藤壺的情感傾注在了紫姬身上,而對藤壺的情感中其實又包含着戀母情結。源氏拼命想要牢牢拴着紫姬,但卻敵不過命運。
命運的無常可謂是《源氏物語》中悲哀的根源,亦是《雪國》中悲哀的根源,正如紫姬臨終所賦的那首詩:
露在青萩上,分明不久長。 偶然風乍起,消散證無常。
參考文獻:
胡稹 《本居宣長“物哀”思想新探》
紫式部 《源氏物語》
葉渭渠 《川端康成評傳》
川端康成 《雪國》
川端康成 《我在美麗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