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1913—2002),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勳,筆名有孫犁、芸夫、孫芸夫、耕堂等,河北安平人,現代著名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的創始人。正像他的筆名一樣,孫犁就像一名“芸夫”一樣,一生筆耕不辍。如果從他19歲的時候開始在校刊《育德月刊》上發表文章計起,到1995年開始卧病,他大約度過了六十多年的創作生涯。其間,他以充滿詩情畫意的獨特創作,給人們留下了無窮的美感享受。一般人憑據作家作品中多所表現的濃郁的冀中風情,都能想到作家是河北人氏。至于作家與山西所有的關系,大概就是鮮為人知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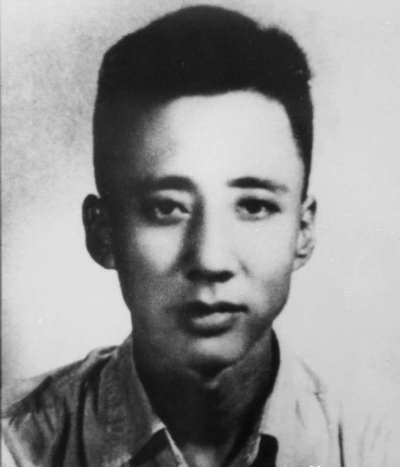
青年孫犁
在《童年漫憶》這篇散文中,孫犁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的故鄉的原始住戶,據說是山西的移民,我幼小的時候,曾在去過山西的人家,見過那個移民舊址的照片,上面有一株老槐樹,這就是我們祖先最早的住處。”作家所說,想必是洪洞無疑了。據此“尋根”,我們可以說,作家已經把自己劃入了實際上的山西人的行列。
也是在“幼小的時候”,在他家住的那一條街上,有好幾戶人家,以長年去山西做小生意,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一直傳下好幾輩。他們多是挑貨郎擔。這些人在每年夏秋忙季回到家後,“總是讓他們的女人挨戶送些小玩意或是蠶豆給孩子們”。作家自然也是這些“孩子們”中的一個了。多少年後,作家對此還是記憶猶新,并仍然把它寫進了《童年漫憶》這篇散文中。在這篇散文中,作家把他由來自山西的“小玩意或是蠶豆”而對山西建立起來的美好印象,充滿情意地抒寫了出來。
孫犁故居
作家童年時候還曾經發生過一件事,對作家的創作生活和作品風格的形成起了極大作用,那就是“聽說書”。主要一位說書的,正是村裡一位“長年累月去山西做小生意”的人,孫犁叫他“德勝大伯”。德勝大伯每次從山西做小生意回來,在夏秋之間農活稍閑的時候,便利用晚間乘涼的機會,給村裡人說起了他在山西做生意時學來的《七俠五義》等評書。有一年秋後,村裡還從山西來了擀面條的哥兒仨,他們在村裡住了三四個月,白天做生意,晚上說評書《呼家将》,用說書來招徕生意。在那種年月,地處冀中農村的孫犁的家鄉,文化生活是相當貧乏的,“聽說書”在這裡成為人們難得的文化享受。這對日後成為作家的孫犁來說,可想而知就更是如此了。
每逢人們放下粥碗,走向說書場去的時候,孫犁這個小書迷也便跑去,陪着老書迷們,靜靜地坐那裡,直到散場。正是在“聽說書”的激發下,稍大些後,孫犁就不再滿足于僅僅是坐在地上聽人家說,而是自己找來古代小說閱讀。就在這閱讀中,作家培養了自己的文學興趣,乃至以後竟走上創作道路。這一切又是和山西聯系在一起的。山西在不知不覺中給作家孫犁進行了文學上最早的啟蒙教育。
參加革命工作後的孫犁
參加革命工作之後,孫犁曾先後四次來山西。第一次是在1939年冬天,孫犁作為晉察冀通訊社的記者到雁北随軍采訪。采訪期間,雁北這一“大雁也不往那兒飛的地方”,使這時雖穿着“一身粗布棉褲襖”,卻因“身材高,腳腕和手腕,都有很大部位暴露在外面”的作家吃盡了“寒風凜冽”、“冰天雪地”的苦頭。正是由此孫犁“第一次感到了戰鬥夥伴的關懷和溫暖”。當時,和他一同采訪的董逸峰同志,看到他那難堪的情狀,在一天随部隊出發時,便把自己從冀中帶來的一件日本軍大衣在風地中脫下,給孫犁穿上。這戰争年代的革命情誼、同志間的濃厚的愛,使孫犁大為感動,直到晚年還念念不忘。這次采訪一直延續到年末,孫犁才回到地處河北阜平的駐地。這使得孫犁第一次離開家鄉過了個春節。除夕之夜,見不到父母妻子的思念與惆怅,山區人民的樸實與熱忱的招待,都給孫犁留下了深切的感受。作家後來把他的這段經曆寫到了《在阜平》和《服裝的故事》兩篇文章中。
孫犁第二次來山西是在1943年,也是冬季。時值日寇正大舉進攻晉察冀邊區。在反“掃蕩”的鬥争中,孫犁同華北聯大高中班的師生輾轉來到山西繁峙一帶的一個深山小村。由于旅途勞累,他突然病倒,整日高燒,脖頸及背部出了許多水痘。受醫療條件所限,當時唯一的方法,就是找一個安全僻靜之所,慢慢療養。于是,作家在一名姓劉的護士和一位姓趙的學生的陪同下,來到了兀立于五台山頂的一個小村蒿兒梁。在這山頂貧瘠的小村,孫犁住了整整一個冬天。期間,一同來的戰友們的關心、群衆的照顧,給作家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尤其是那個當過童養媳的小護士“劉蘭”樸實誠懇,任勞任怨,對作家更是進行了耐心細緻的護理;而本村的那位活潑開朗,熱情潑辣的婦女主任,則對孫犁一行的安全、衣食問題做了更多的艱辛的工作。正是以這兩個人為模特兒,作家後來把這段山區養病的生活,寫成了兩個短篇小說《看護》和《蒿兒梁》。
孫犁作品
孫犁第三次來山西是在1944年春末。當時作家剛從繁峙病愈回到阜平,隻歇了一夜,便按照上級的指令,和同志們一起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程。隊伍途經山西忻縣,正好趕上附近發生了戰争。中午,他們進入了一個鄉親們已經分散轉移了的山間小村。等到在一個農家院落匆忙吃過飯,孫犁到鍋中刷碗時,忽然“嗡”的一聲,鍋飛了起來。原來是竈下預先埋藏的一顆手榴彈發生了爆炸。孫犁頓時變得滿臉血污,額上似乎還翻着兩寸來長的一片肉。當孫犁用手一抹,他臉上那些可怕的東西竟是些污水和一片菜葉,不得不到村外的小河裡去把臉洗一下。在洗臉的時候,他和一個在下遊洗菜的婦女争吵了起來。孫犁受了驚吓,轉眼又遇上這樣一件事情,他當時心情糟糕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這場洗臉、洗菜的小糾紛,日後卻促成作家寫出了《山地回憶》這篇名作。在《關于〈山地回憶〉的回憶》這篇文章中,作家就對此作了揭示,他說:“小說裡的那個女孩子,絕不是這次遇到的這個婦女,這個婦女很刁潑,并不可愛。而這種人,在現實生活中間,占大多數,她們在我的記憶裡是數不清的。洗臉洗菜的糾紛,不過是引起這段美好的回憶的楔子而已。也是在《關于〈山地回憶〉的回憶》中,作家對一件事卻是給予了肯定的,他說:“如果不是山西的鍋鑄得堅固,竈口壘得嚴實,則我一定魂飛天外了。”
孫犁最後一次來山西,是在1945年。當時日寇已經投降,按組織決定,孫犁離開生活了一年的延安,随艾青上司的華北文藝工作隊向晉察冀邊區進發。由于孫犁是從敵後來的,他便被派作前站,同時兼顧給女同志趕毛驢的任務。十月間,孫犁一行到達山西渾源,在這裡休息了一些日子。與以往來山西不同的是,盡管面臨着内戰的危險,但孫犁與剛剛奪取抗戰勝利的同志們一樣,心情是輕松愉快的。用他本人的話說“這真是勝利歸來,洋洋灑灑”。後來,作家在《某村舊事》《服裝故事》兩篇散文中都提到了這件事。
晚年孫犁
孫犁原本就是山西移民的後裔,童年時代他通過“說書的買賣人”最早受到了山西的浸染,在以後的歲月裡他又多次來山西進行革命活動,這些無疑都豐富了他的創作生活,使他以山西人物風情為素材,充實了他琳琅滿目的著作畫苑。在現代文學史上,曾經涉足過山西并在作品中留下深刻印記的作家不在少數,但像孫犁這樣以其創作與山西建立如此密切久遠關系的人,實不多見。山西為作家孫犁赢得文壇盛名所作的貢獻,是不應該被人忘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