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上海翻譯》2006年第1期
轉自:上海美國研究、明德史館
19世紀60年代之後,随着洋務運動的鋪開,作為通商口岸之一的上海不斷吸引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參與傳播西學的文化活動。這一時期,美國傳教士紛紛湧入上海,形成一股潮流。他們在科技翻譯領域銳意進取,形成了一支中國近代科技翻譯的主力軍,在美國翻譯史和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寫下熠熠生輝的一頁。
嶄露頭角
在幾乎由英國來華傳教士一統上海翻譯出版天下的19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初來乍到的美國傳教士多半以個人身份參與其中的科技翻譯。晚清最早在華開辦的傳教士翻譯機構墨海書館(The London Mission Press)1843年由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成立于上海。雖然該翻譯館主要譯員為英國教士,出版的譯著以宗教類為主,但美國傳教士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1821-1902)還是以别出心裁的手法編譯了《科學手冊》(上海方言,1856年版,共1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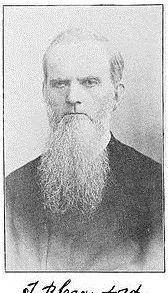
美國傳教士高第丕19世紀50年代來到上海,他基于上海“土音”,發明了一種音節文字
美國長老會開辦的花華聖經書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 Book Establishment) 1844年初始創于澳門,後來發展為美華書館,1860年遷址上海。之後美華書館在上海取代了墨海書館成為西學翻譯傳播中心。在該館從事科技翻譯的譯者中,頗為知名的美國傳教士是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1850-1924),他和謝洪赉合作了多部科技譯著包括《格物質學》(自然科學常識課本)、《代形合參》(微積分教科書)、《八線備旨》 (三角教科書)。同期,高第丕夫人為美華書館編譯了《造洋飯書》(1866年版,共29頁),該書介紹了268種西菜、西點的做法,是晚清為數不多的介紹西餐的書籍。
挑起大梁
從19世紀60年代末起,一些美國人不甘于在上海譯界扮演次要角色,而是挑起在滬翻譯出版機構的大粱,甚至自己創辦刊物登載科技譯文,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世紀末。
1868年創立于上海的江南制造局翻譯館成為美國傳教士進行科技翻譯的主戰場,在國史政史方面譯著甚豐的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在科技方面也偶有所為,他的科技譯著《格緻啟蒙》分化學、地理、天文、博物四卷。
林樂知和瑪高溫
其他在科技翻譯領域值得一提的譯著包括瑪高溫(Daniel Jerome Macgowan, 1814-1893)和華蘅芳合作的《金石識别》(1871年版)、《地學淺釋》(1873年版);金楷理(Carl T. Kreyer, 1839-1914)的《臨陣管見》《克虜伯炮說》《光學》(趙元益筆述,沙英和曹鐘秀繪圖,沈善蒸校對,1876年版)、《測候叢談》(華蘅芳筆述);衛理的兩種農學書《農務土質論》《農學津梁》,三種科學書《取濾火油法》《照相镂版印圖法》《無線電報》(範熙庸筆述)。
林樂知在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的同時,于1868年9月5日出版了美國人在上海的第一份中文周刊《中國教會新報》(Chinese Church News),該刊為美國傳教士開辟了另一個科技翻譯的陣地。雖然此刊以“教會”為名,卻行傳播西學之實,短短三年後刊載的教會内容就減少到不足五分之一。
丁韪良和嘉約翰
同時,該報為當時在滬的其他美國傳教士登載科技譯文提供了便利,其中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的《格物入門》(從第4期連載至43期,原書由京師同文館出版,所刊出的内容為化學部分)和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編譯的《化學初階》(連載,該書是19世紀70年代中國翻譯西方化學書籍的代表作之一)及其《内科闡微書自序》。
1876年2月于上海正式面世、由格緻彙編社主辦的《格緻彙編》(月刊)是一份地道地道的科普雜志,後來成為晚清知識分子了解西學的較理想的入門讀物。為該刊的科技翻譯撰稿的美國傳教士有:瑪高溫、蔔舫濟(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1864-1947)等人。蔔氏的譯著《地理初桄》介紹了地球的形成、地質構造、地形地貌、火山地震等。
蔔舫濟、狄考文和赫士
1877年,另一大翻譯機構益智書會(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成立于上海。該書會使得美國傳教士在科技翻譯方面有了用武之地,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以其較高的威望擔任了數任書會下屬的委員會主席。益智書會出版重要的美國傳教士的科技譯作有:《筆算數學》及《形學備旨》均由狄考文口譯,鄒立文筆述;《聲學揭要》《光學揭要》《天文揭要》都為美國長老會傳教士赫士(Watson McMillan Hayes,1857-1944)口譯,朱葆琛筆述。
英美傳教士在華最大的翻譯出版機構廣學會(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of China)于1887年創辦于上海,學會推舉林樂知為協理,并決定将停刊五年有餘的《萬國公報》作為廣學會的機關刊物恢複出版。包括林樂知在内的美國傳教士在廣學會的翻譯幾乎是清一色的政治類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複刊後的《萬國公報》變宗教性宣傳刊物為以時事為主的綜合性刊物,其專設的科學知識類為科技翻譯提供了展示的平台,除刊載過林樂知本人譯介的《格緻源流說》《論日蝕》等科技譯文外,還登載其他美國傳教士在科技、醫學等方面的譯介文章,包括丁韪良的《彗星論》、潘慎文的《彗星略論》、嘉約翰的《皮膚諸症論》等。
内外動因
美國傳教士之是以能夠長盛不衰地立足于上海從事西學翻譯,尤其是科技翻譯,并将他們的科技翻譯活動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甚至20世紀初,有其深刻的内外動因。
得天獨厚的區域人文優勢
在五口通商的城市中,上海并不是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城市,曆史卻最終選擇了上海,傳教士也選擇了上海。上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地處長江三角洲,幾乎坐落于中國中心地帶,交通四通八達,外國人在滬的經營風調雨順,再加上上海人的包容性等方面的特點,使得上海後來居上,超過其他四口,成為吸收越來越多外國人來此傳播西學的中心。
1928年的外灘
美國海外傳教運動方興未艾
1844年《望廈條約》簽訂後,作為美國對外擴張行動的先遣隊,美國基督教會更加積極向中國發展。到1855年,在上海的30個傳教士中,有美國人21個,英國人9個。1858年新教在中國的傳教士僅81人,到1889年增加為1296人,其中美國傳教士為513人,僅次于英國的724人。美國在華傳教士的數目盡管屈居第二位,但其本身增加的比例十分可觀。1890年前後,美國國内開始掀起了一波向海外宣傳宗教的狂潮,為在滬美國傳教士從事科技翻譯活動提供源源不斷的後備人才。
洋務運動持續深入
鴉片戰争後由中國有識之士發起的洋務運動顯然對傳教事業具有正面的推動作用。發展近代工業迫在眉睫,然而,中國人當時辦工業面臨白手起家的現實,極需網羅人才、翻譯西書,這樣開設翻譯館成了當務之急。另一方面,面對傳教遇到的種種困難,美國傳教士感到“間接布道”的形式,即新聞、出版、譯書的活動不失為上佳的政策。于是,上海成為美國傳教士在滬施展科技翻譯技能的熱土。
傑出貢獻
美國傳教士在上海的科技翻譯在晚清中國影響面之大,影響力之強,影響持續時間之長,足以和他國傳教士比肩。他們的翻譯進一步奠定了上海作為中國西學傳播中心和翻譯中心的基礎。
成就于上海、輻射向全國
美國在滬傳教士為上海科技翻譯的經久不衰奠定了堅實的客觀基礎。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陸續擔當起在滬翻譯出版機構的重任,并成為中流砥柱。二是吸收了越來越多的美國傳教士投身于上海科技翻譯事業。三是他們的科技翻譯著作不限在上海刊發,而且發行至全國各地,廣為采用。中國的有識之士對他們的經典科技譯著孜孜以求。
翻譯與政治結合的典範
傳教士在洋務運動的翻譯事業中所起的作用——從被動到主動、從無意識到有意識——在晚清上海譯界表現得格外明顯。美國傳教士客觀上翻譯出版了一批與洋務運動相呼應的西方自然科學書籍,為推動中國科學進步和中外科技文化交流起過作用。
中外譯者合影留念。左五為狄考文
開拓創新、填補空白
美國傳教士在滬的譯著在數個領域開科技應用之先。比如,狄考文編譯的《筆算數學》首先在中國采用阿拉伯數字、加減符号+-、分數線上下的分子和分母。嘉約翰在滬刊登的醫學譯著盡管為數甚少,可它們不但為其創辦的博濟醫局實施醫療實踐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且填補了中國西醫學史上的空白,對傳統中醫具有啟示性作用,為後來的中西醫結合提供了厚實的基礎。
豐富翻譯詞彙、奠定理論基礎
比如,狄考文在編譯教科書的同時,進行了大量名詞術語的梳理工作。他于1904年出版了自己編譯的《中英對照術語辭典》,旨在統一科技譯名翻譯标準。該辭典收入12000多詞條,其科技詞彙涵蓋力學、聲學、熱學、光學、電學、磁學、結晶學等方方面面。這大大避免了科技翻譯混亂不堪的局面。狄考文明确指出:科技術語的翻譯定名必須注意應簡短、便于使用、界定準确。這些都對後來從事翻譯理論研究的本土翻譯家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促進近代中國教育改革
清末民初不論是教會學校還是官辦學堂,都開設了有别于傳統學堂的科學課程。在沒有現成教材的情況下,翻譯西方的科技著作成了編譯教科書的最佳途徑。這些翻譯教材被新式學堂廣為采納,必然沖擊正常教學的傳統内容,打破傳統教材一統天下的舊格局,傳播近代西方先進的科技知識和人文觀念。許多有志青年學生從中汲取養分,擴大視野,學會了如何放眼世界。
助推自然科學的啟蒙和建立
有學者統計,從1860年到1900年的40年間,有555部西方著作被譯成中文出版,其中自然科學162種,包括數學、實體、化學、天文、地理、動物學、植物學、醫學等;應用科學225種,涵蓋工藝、礦務、船政等。在這些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的譯著中,在滬美國傳教士的科技翻譯占有一席之地。在西方科學譯介的啟蒙和催化下,各類自然科學相繼在中國出現,進而初步形成了中國近代自然科學的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