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前言</h1>
這一篇内容來自于《詩詞例話·寫作》部分的“線索”篇。
古人把詩比作一串銅錢,有的部分如同散落的銅錢,有的部分如同穿起銅錢的那條線。這條線,就是本文中所說的“線索”。
周振甫先生引用了江浩然(清朝乾隆時期學者生于1743年 )的一段話, 其實這段話在仇兆鳌(1638年-1717年)《杜詩詳注》中也存在。
因為他們二人都引用了黃生的《杜詩說》。黃生(1622——?),字生父,又字扶孟,号白山、冷翁、蓮花外史。黃生在明代為諸生,入清不仕,安徽歙縣人。《杜詩說》成書于康熙二十三年,研究杜甫的人經常會引用黃生的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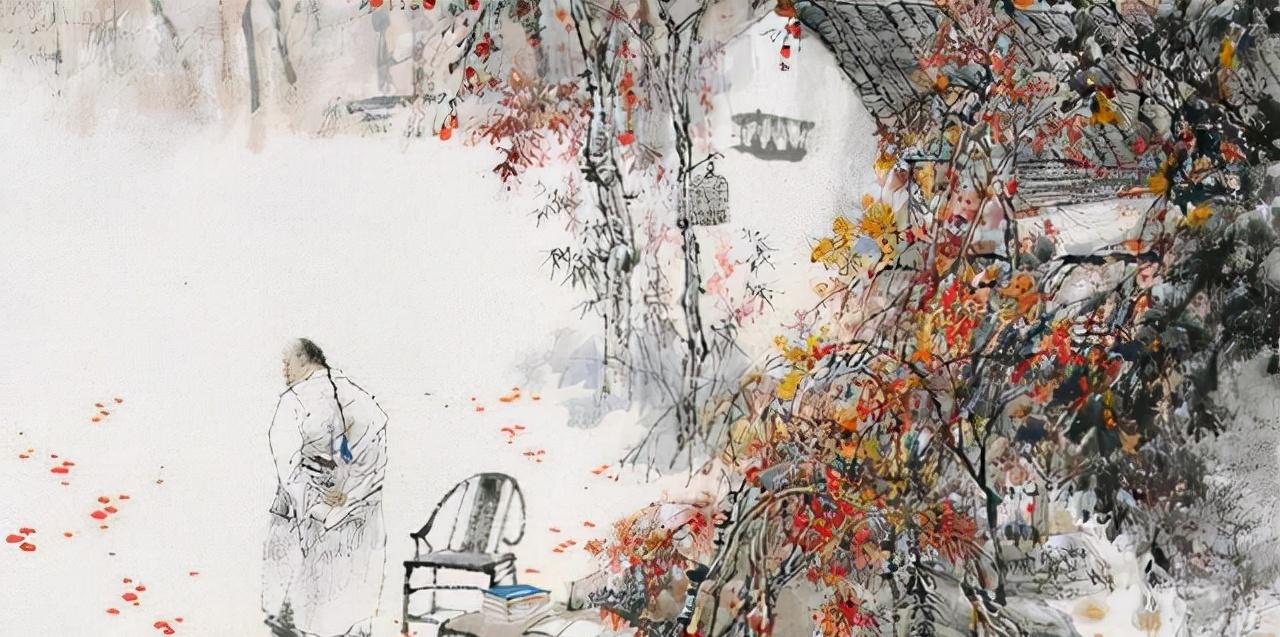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7">一、線索在結局</h1>
這段話分三個部分,分别舉例說明了線索在詩中的不同位置。第一種在結尾:
詩眼貴亮而用線貴藏,如何氏山林之五,“滄江”“碣石”,風筍雨梅,銀甲金魚,皆散錢也,而以一“興”字穿之,是線在結也。( 黃生《杜詩說》)
詩眼,有句中眼有篇中眼。句中眼是句中點睛之筆,是以說:詩眼貴亮。煉字煉的就是句中眼,大多是動詞,或者活用為動詞的形容詞、名字。
用線,詩中的線索并不那麼明顯,但是起到了串聯全篇的作用。這裡舉例的是杜甫的這首詩,《陪鄭廣文遊何将軍山林》之五: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
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
銀甲彈筝用,金魚換酒來。
興移無灑掃,随意坐莓苔。
興移無灑掃,随意坐莓苔。興,指遊樂之興,前面六句寫景,滄江、碣石、風筍、雨梅,銀甲、金魚,都是詩人與賓主眼中賞心悅目之景。
賓主之“興”發生了轉移,從前四句的山水花竹,轉為飲酒宴樂。是以說“以一“興”字穿之,是線在結也”。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5">二、線在起也</h1>
第二種,線索在詩的起句:
如秦州《遣懷》“霜露”菊花,“斷柳”“清笳”,水樓山日,“歸鳥”“栖鴉”,亦散錢也,而以“愁眼”二字聯之,是線在起也。( 黃生《杜詩說》)
這裡舉例的是杜甫另一首五律《遺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随斷柳,客淚堕清笳。
水淨樓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栖鹎。
這首詩的意象有:霜露,菊花,風柳,客淚、清笳、水樓、山日、歸鳥、啼鴉。
黃生說,這些獨立景物也像散錢,用“愁眼”做線索串聯起來。線索放在一首詩的前面。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3">三、線在起結</h1>
第三種,線索在一首詩的發端和結尾都出現:
此詩“地日”“山雲”,“雷殷”“水文”,亦散錢也,而以“陰晴”二字冠之,“雨來”二字收之,是線在起結也。(江浩然《杜詩集說》引黃生說)
這裡又引用了杜甫的一首詩,為什麼總是引用杜甫呢?因為黃生這部書就是專門研究杜甫呀。
杜甫《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南紀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
層閣憑雷殷,長空面水文。雨來銅柱北,應洗伏波軍。
前有陰晴,後有雨來,中間四句是散錢,被前後串起。
詩中的線索,很像一條藤蔓植物的莖。花葉生長于莖上,而這條莖或隐或現,藏身于花葉之間。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2">結束語</h1>
關于線索,周振甫先生總結道:
從上面三例看來,三首詩的線索,一首在結尾點明,一首在開頭點明,一首在頭尾點明,靠這些點明的字眼,把詩中所寫的景物貫串起來,構成了詩的線索。
線索肯定是貫穿始終的,神龍見首不見尾,雖然有的部分看不見,但是自有全龍存在。詩有明線,有暗線,無論明線還是暗線,其目的都是将“散錢”串聯起來,令整首詩渾然一體,一氣貫通。
@老街味道
境界全出是啥意思?詩人筆下的石頭裡,住着一個孫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