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自然科學家的科研活動與宗教信仰無關;科學與宗教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是有本質差別的</h1>
科學知識是對客觀世界規律性的認識,可以接受實踐的檢驗;宗教神學觀念宣揚的則是超自然、超物質的力量,是不能接受實踐檢驗的;追求科學知識所展現的科學精神是理性的批判精神,宗教神學宣揚的則是順從、虔誠的心理;科學知識的擷取是以通過實踐了解的科學事實作為認識的基礎,運用科學抽象和科學思維的方法,上升得到的理性認識成果;而宗教神學卻否定科學的方法,認為如果沒有“神的啟示”,我們是無力認識宇宙的。
從科學與宗教神學上述方面的具體關系來考察,它們本質上顯然是對立的。既然對立,宗教信仰對自然科學研究也就不會有正面的積極作用。
可以肯定地說:
<h1>研究自然科學與宗教信仰無關。事實上,自然科學家一般是成為宗教信徒在先,研究自然科學在後;一位宗教信徒是否能成為自然科學家與其宗教信仰無關。近代也隻有微乎其微的自然科學家信仰宗教。</h1>
有人曾問過法國微生物學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你如何能是個科學家又是個信徒?”他大緻這樣問答:“我在實驗室做科學。我的家庭與我的宗教則在另一處。”
有這樣一種說法:“科學家是懷着對宗教的虔誠去從事科學研究的”,此言差矣。有些極少數科學家可能是虔誠的宗教信徒,但在他們從事科學研究的時候卻把宗教信仰放到一邊去了。倒是研究成果的獲得常常伴随着對宗教信條的懷疑。比如,相關的研究已經表明,哥白尼取得的天文學成就,并沒有得益于他笃信的天主教,而毋甯是他懷疑上帝旨意、擺脫神權統治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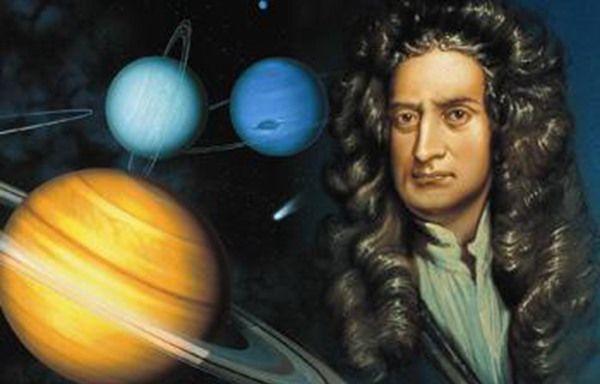
牛頓不信三位一體
<h1>牛頓是自然神論者</h1>
自然神論者認為上帝在創造世界和自然規律以後就不再進行幹預,而由自然規律自行支配一切。
對于這部分科學家來說,他們實質上也否定宗教神學信仰對自然科學研究有正面積極作用,因為“自然神論至少對唯物主義者來說不過是擺脫宗教的一種簡便易行的方法罷了。”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牛頓等都是這樣的科學家。在近代西方,由于宗教勢力影響還很強,不少科學家都屬于這種情況。以下僅舉牛頓為例來具體說明。
牛頓(1642-1727)不僅是偉大的科學家,也是了不起的哲學家,還是虔誠的宗教徒。他是這樣認識上帝的:我們“不能對上帝的實質是什麼會有任何概念。我們隻是通過上帝對萬物的最聰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終的原因,才對上帝有所認識” 。“從事物的表象來論說上帝,無疑是自然哲學分内的事。”
這種通過上帝的“安排”,“表象”來“認識”上帝以及将“萬物”的最終原因歸于上帝的提法,實質上是在消解上帝。
他還寫道:“一切事物都包容于上帝之中,并在其中運動,但并不彼此發生幹擾;上帝并不因為物體的運動而受到什麼損害,物體也并不因為上帝無所不在而受到阻礙。所有人都承認至高無上的上帝是必然存在的,而由于這同一個必然性,他又是時時、處處存在的。是以,他也就到處相似,渾身是眼,渾身是耳,渾身是腦,渾身是臂,并有全能進行感覺、了解和活動;但其方式絕不和人類的一樣,絕不和物體一樣,而是我們所完全不知道的。……上帝根本沒有身體,也沒有一個體形,是以既不能看到,也不能聽到或者摸到他;也不應以任何有形物體作為他的代表而加以膜拜。”
這是牛頓關于“上帝”的十分有代表性的一段描述。這段話看似宗教味十足,然而,明眼人不難看出,牛頓心目中的上帝和傳統有神論的上帝是不一樣的。在後者看來,上帝是人格化了的神,是神化了的人;而在牛頓看來,上帝“渾身是眼,渾身是耳,渾身是腦,渾身是臂,并有全能進行感覺、了解和活動;但其方式絕不和人類的一樣,……上帝根本沒有身體,也沒有一個體形,是以既不能看到,也不能聽到或者摸到他;也不應以任何有形物體作為他的代表”,“是我們所完全不知道的”。可見,“人格化的上帝”在牛頓的科學活動中是完全沒有地位的。牛頓要想在探索自然界奧秘中取得進展,就必須抛棄人格化的上帝。他雖然也承認上帝的存在,但卻認為上帝在創世以後,就停止對其進行幹涉,而讓世界按照其自身的規律運作。他竭力彰顯自然規律的作用,而把上帝的作用推到幕後。這讓我們看到了科學家的自然神論的又一種語言表述。通過上帝的“安排”,“表象”來“認識”上帝,以科學研究來證明上帝的存在,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自然規律就是上帝,這裡,唯物主義的傾向相當明顯。
愛因斯坦在親筆信裡面否認一切超自然信仰
對此,愛因斯坦說得好:宗教領域同科學領域之間的沖突的主要來源在于人格化了的上帝這個概念;人格化了的上帝這個概念是不足取的,凡是徹底深信因果律的普遍作用的人,對那些由神來幹預事件程序的觀念,是片刻也不能忍受的。
恩格斯曾經中肯地指出:“上帝在信仰他的自然科學家那裡所得到的待遇,比在任何地方所得到的都壞。唯物主義者隻管說明事物,是不理睬這種名詞的。隻有當那些咄咄逼人的善男信女們把上帝強加于他們的時候,他們才加以考慮……”
我們來考察一下牛頓出版《原理》的經過,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實際上,牛頓在建構他的力學體系和天體系統時,根本就沒有考慮過上帝的作用,是以1687年7月《原理》以拉丁文初版問世時,僅在第三卷中有一次以虛詞的形式提及了“上帝”。
由此可見,認為有了宗教信仰,牛頓才可能做出偉大的科學發現,這種看法無疑是錯誤的,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相反,卻是因為他努力擺脫傳統宗教的羁絆,敢于尊重科學事實,得益于自己深厚的科學素養,才能在科學上取得突破和偉大發現。如果牛頓死守宗教信條不能自拔,那倒可能錯誤地引導他走上歧路,得出一些荒唐的結論。他晚年的境況則可以說明這一點。
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h1>牛頓傾注前半生心血,于1687年出版了他的劃時代自然科學著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之後就再沒有多少重大的科學創見了</h1>
他開始進入政界,當選過國會議員,1699年開始擔任皇家造币廠廠長,直到去世。1705年被安妮女王封爵。1703年當選為皇家學會會長,連選連任,直到離開人世。牛頓的後半生在科學界和社會上雖然仍享有很高的威望,但其科學創新精神已經大為失色了。他反而埋頭于煉金術的研究,熱衷于《聖經》經文的考證與诠釋,這些徒勞無益的事情無謂地耗費了他後半生的精力,使他淪為神學的奴仆。這不能不說是一幕、讓人扼腕歎息的宗教“促進”科學的悲劇吧。
主要作者/于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