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尺素清芬——百年畫苑書劄叢考》新書分享會,26日在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召開。本書作者朱萬章,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常務副館長杜鵬飛,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中國書法國際傳播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天曙,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美術分社總編輯張明等人參加了分享會。
此次分享會的主題為“從書劄看晚清以來藝術大家的朋友圈”,即力圖通過書中信劄裡的一個個看似散亂的場景,串聯起晚清民國以來學界和畫苑的逸事,也為讀者勾勒出一個個朋友圈,再現每一封信劄背後不為外人所知的文化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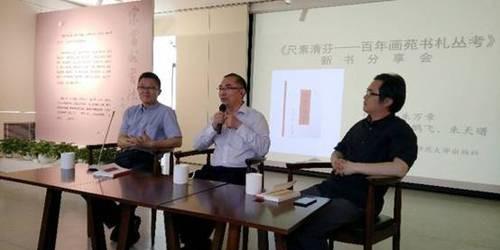
據作者朱萬章介紹,書中不僅整理了居廉、陳師曾、徐邦達、謝稚柳、于省吾、趙少昂等藝術大家的來往信件,而且旁涉啟功、傅斯年等老一輩鑒定家與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的故事。這些信件的内容囊括了書畫、遊玩、收藏、賞鑒及日常生活,看似散亂,但将之串聯起來,整理成書,則讀者可以略窺20世紀以來的書畫鑒藏與學術史嬗變。作者認為,将這些珠玉般的資訊串聯起來,可為将來更深入的研究做參考。所謂藏寶于民,将潛心收藏的信劄提供給相關的研究者,對作者而言,是一種“獨樂樂不如衆樂樂”的樂趣所在。
魏晉以來,手劄的形式便開始大量出現,很多書法家的書法作品如王羲之寫給親人的《快雪時晴帖》、顔真卿的《争座位帖》、王獻之的《中秋帖》等,是書法作品,也是手劄。手劄可以說是中國書法呈現在今人眼中的最直接、最生動、最鮮活的一種方式。此次參加分享會的朱天曙教授對書法與書畫鑒藏十分熟悉,他便從這個角度,為我們梳理了魏晉以來的信劄發展脈絡,也總結了書劄的重要價值。他認為,信劄是一種即時的書稿,最能展現寫信人的真性情,讀者從中能看到寫信人更加真實的生活,從這一點上說信劄的史料研究價值是非常高的。另外信劄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如顔真卿、王獻之,一封小小的手劄也就變成一幅書法作品、一件藝術品,它同寫信人的其他藝術作品一樣,甚至能更為真實地展現其思想态度和學術觀點。
具體到本書,陳師曾與梁鼎芬、居廉與楊永衍的信件,無一不展現出用紙的考究,以及書法的飄逸,不僅對研究陳師曾、居廉等人的交遊網絡有借鑒的價值,更直覺地展現了他們的書法。
古人在日常交往中,往往以“自謙而敬人”為原則。杜鵬飛先生為我們舉例說明,書稿中提到的薛永年為中國著名史學家,他在緻朱萬章的信中,稱其“萬章先生”;梁鼎芬稱陳師曾為“世丈”,“世”是幾代人的交情,“丈”則是前輩;又如馬國權先生,在信中也稱呼作為晚輩的朱萬章“萬章兄”。所謂的稱兄道弟,什麼時候該稱兄,什麼時候該稱弟,是十分講究的。而受信人的名字出現在信劄的結尾,在今天則已經十分少見了,這也導緻了很多信劄被單純地當成了書法作品。是以手劄傳達出來的資訊是十分豐富的,它展現出中國古代書信來往的禮儀,也展現出學界前輩們治學的胸懷與氣度。
也正因為如此,信劄本身以一個很小的物件存在,但把信劄内容變成學術研究,便是本書的價值所在。
針對現場對信劄收藏興趣濃厚的讀者的提問,作者認為,很多海外收藏家十分熱衷于收藏中國古代的手劄,這是中西方文化不斷交流碰撞的結果。這些文化現象與往來都需要“物”來承載,這便是文物的價值。但人的生命有限,是以無論是信劄收藏抑或是其他的收藏,都要求人必須有自己的明确的主題和計劃。個人的信劄收藏不是博物館館藏,無論是用作學術研究還是展覽,信劄收藏的目的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在于有明确的主題,在于在浩如煙海的”物“中找到一條主線,對真理和價值進行判定,進而使得自己的收藏更具有價值。
杜鵬飛在活動的最後為本書做了總結發言。他認為,此次分享會讓我們對近現代中國書畫鑒定的專家往來有了更多的了解。在這個少有人寫信的年代,書信似乎已經成了一種遠離我們日常生活的交流方式,正因為如此,朱萬章對這些信劄的收藏和研究就顯得更為重要,《尺素清芬——百年畫苑書劄叢考》一書的價值也顯而易見。“尺素”不僅散發着“清芬”,也散發着獨特的魅力和光彩。
(光明日報全媒體記者劉彬、通訊員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