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尺素清芬——百年画苑书札丛考》新书分享会,26日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召开。本书作者朱万章,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天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美术分社总编辑张明等人参加了分享会。
此次分享会的主题为“从书札看晚清以来艺术大家的朋友圈”,即力图通过书中信札里的一个个看似散乱的场景,串联起晚清民国以来学界和画苑的逸事,也为读者勾勒出一个个朋友圈,再现每一封信札背后不为外人所知的文化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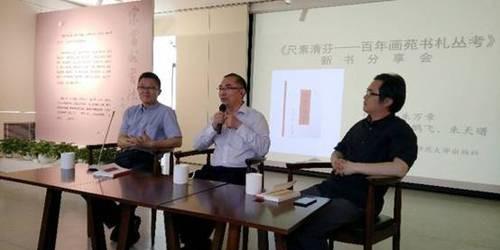
据作者朱万章介绍,书中不仅整理了居廉、陈师曾、徐邦达、谢稚柳、于省吾、赵少昂等艺术大家的来往信件,而且旁涉启功、傅斯年等老一辈鉴定家与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的故事。这些信件的内容囊括了书画、游玩、收藏、赏鉴及日常生活,看似散乱,但将之串联起来,整理成书,则读者可以略窥20世纪以来的书画鉴藏与学术史嬗变。作者认为,将这些珠玉般的信息串联起来,可为将来更深入的研究做参考。所谓藏宝于民,将潜心收藏的信札提供给相关的研究者,对作者而言,是一种“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乐趣所在。
魏晋以来,手札的形式便开始大量出现,很多书法家的书法作品如王羲之写给亲人的《快雪时晴帖》、颜真卿的《争座位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等,是书法作品,也是手札。手札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呈现在今人眼中的最直接、最生动、最鲜活的一种方式。此次参加分享会的朱天曙教授对书法与书画鉴藏十分熟悉,他便从这个角度,为我们梳理了魏晋以来的信札发展脉络,也总结了书札的重要价值。他认为,信札是一种即时的书稿,最能体现写信人的真性情,读者从中能看到写信人更加真实的生活,从这一点上说信札的史料研究价值是非常高的。另外信札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如颜真卿、王献之,一封小小的手札也就变成一幅书法作品、一件艺术品,它同写信人的其他艺术作品一样,甚至能更为真实地展现其思想态度和学术观点。
具体到本书,陈师曾与梁鼎芬、居廉与杨永衍的信件,无一不体现出用纸的考究,以及书法的飘逸,不仅对研究陈师曾、居廉等人的交游网络有借鉴的价值,更直观地展现了他们的书法。
古人在日常交往中,往往以“自谦而敬人”为原则。杜鹏飞先生为我们举例说明,书稿中提到的薛永年为中国著名史学家,他在致朱万章的信中,称其“万章先生”;梁鼎芬称陈师曾为“世丈”,“世”是几代人的交情,“丈”则是前辈;又如马国权先生,在信中也称呼作为晚辈的朱万章“万章兄”。所谓的称兄道弟,什么时候该称兄,什么时候该称弟,是十分讲究的。而受信人的名字出现在信札的结尾,在今天则已经十分少见了,这也导致了很多信札被单纯地当成了书法作品。因此手札传达出来的信息是十分丰富的,它体现出中国古代书信来往的礼仪,也体现出学界前辈们治学的胸怀与气度。
也正因为如此,信札本身以一个很小的物件存在,但把信札内容变成学术研究,便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针对现场对信札收藏兴趣浓厚的读者的提问,作者认为,很多海外收藏家十分热衷于收藏中国古代的手札,这是中西方文化不断交流碰撞的结果。这些文化现象与往来都需要“物”来承载,这便是文物的价值。但人的生命有限,因此无论是信札收藏抑或是其他的收藏,都要求人必须有自己的明确的主题和计划。个人的信札收藏不是博物馆馆藏,无论是用作学术研究还是展览,信札收藏的目的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在于有明确的主题,在于在浩如烟海的”物“中找到一条主线,对真理和价值进行判定,从而使得自己的收藏更具有价值。
杜鹏飞在活动的最后为本书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此次分享会让我们对近现代中国书画鉴定的专家往来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这个少有人写信的年代,书信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交流方式,正因为如此,朱万章对这些信札的收藏和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尺素清芬——百年画苑书札丛考》一书的价值也显而易见。“尺素”不仅散发着“清芬”,也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和光彩。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刘彬、通讯员刘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