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9年之前,真正可以被稱為"作家"的導演,奧森·威爾斯,希區柯克,黑澤爾明,都是少數。
因為電影掌握在制片廠手中。為了獲得更好的票房,大牌明星,具體的劇情編排,精美的布景道具,是一部作品的基本要素。
沒有合格的董事,絕大部分隻能淪為整個工業體系的齒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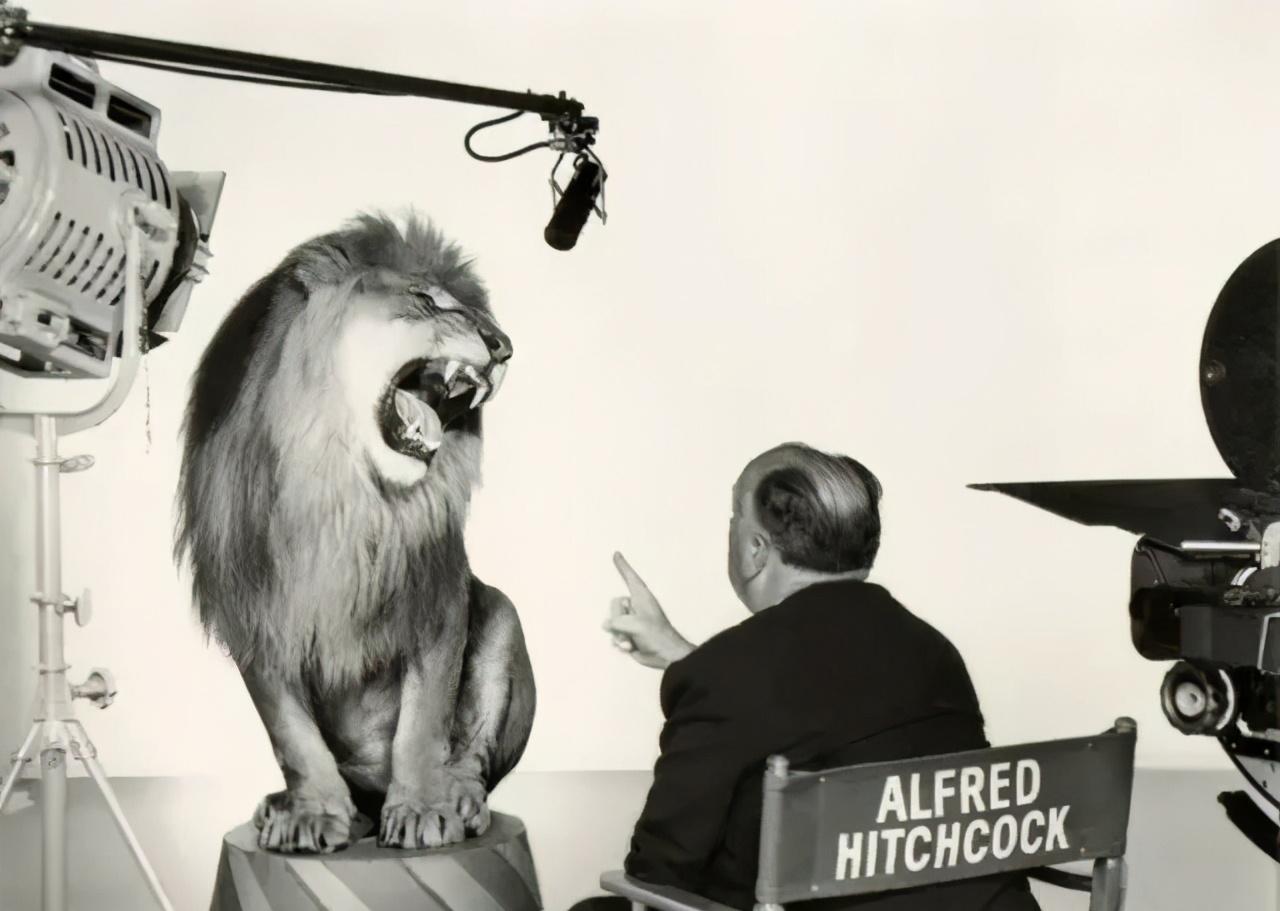
一位名叫安德烈·巴贊(Andre Bazan)的法國影評人,對這部電影成為賺錢工具感到不滿,于是創辦了《電影手冊》雜志,與一群年輕人一起,為激烈的電影評論撰寫了各種文章。
但很難相信你不能練習。
是以他的一個下屬決定自己開槍!
弗朗索瓦·特呂弗(Francois Truffaut)是速度最快的電影之一,在1959年第12屆戛納電影節上獲得了"四百次罷工",并在27歲時赢得了戛納最佳導演獎杯。
影片一開始,安德烈·巴贊就病去世了,是以《四百出擊》是對巴贊作品的特别緻敬。
在巴贊的上司下,他是一個堅強的人,他在1950年代中期的著作廣受好評。其中之一,"法國電影的某種趨勢",成為當時的"10W plus"爆炸,在電影界引起轟動。有人認為他純粹是想打仗,有人支援他的觀點。
在看了大約3000部電影後,他對電影制作有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其中一個重要的理論是作者專用理論。
如果一部電影有作者,它隻能是導演。
導演決定故事,決定角度,決定攝影,決定風格。
作者的情感需要融入其中。
真正的電影,就是這樣。
《四百次打擊》以特雷弗自己的童年經曆為基礎,講述了一個13歲男孩如何走上犯罪之路的故事。
他親自挑選演員,并發掘了才華橫溢的演員讓-皮埃爾·萊奧德(Jean-Pierre Leod)。後者在1966年赢得了柏林電影節。
扮演繼父的演員阿爾伯特·雷米(Albert Remy)看起來非常像特雷弗真正的繼父。
由于影片傾向于批評父母的不當教育,有人說他抹黑了家人。
據說壓力重重的繼父和母親在電影上映後就離婚了。
為了将他與普通的商業電影區分開來,特雷弗還實踐了另一個重要的理論,将相機帶入現實生活。
法國新浪潮對傳統電影的批評之一是攝影總是笨拙而薄弱。
在"四百次罷工"的序幕中,随後是主題配樂,鏡頭在巴黎的街道上漂移,移動而自由。運動圖像在電影開始時被廣泛使用。
觀衆通過鏡頭看到的是真實而自然的環境。
如果一切都是人為的幻覺,那麼這部電影畢竟是一個虛幻的夢。
特雷弗的目标很明确:他想把電影帶回現實生活。
将電影與人類生活和情感聯系起來,讓它們成為現實的鏡子,而不是麻醉劑或興奮劑。
要做到這一點,僅僅從工作室"儲存"錄影機是不夠的,特雷弗需要一個移動的腳本。
《四百次打擊》的影響力從法國蔓延到美國,英格瑪·伯格曼的《野草莓》和希區柯克的《西北》在1960年提名了第3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創劇本,特雷弗證明了他并不孤單。
他最大的成功之一是,觀衆看到的不僅是大師Towan的經曆,還有一個13歲男孩的内心世界。
人們普遍認為安托萬是特雷弗童年的反映的原因之一是,特雷弗說導演的電影是他一生的編年史。他電影中的主要角色通常被稱為安托萬。
《四百次罷工》中的"安托萬"讓-皮埃爾·利奧德(Jean-Pierre Leord)出演了特雷弗的幾部作品,兩人合作過"安托萬宇宙"。
這顯然是安托萬本人的縮影。
隻是為了四百次罷工,特雷弗并沒有說這都是他的個人電影自傳。
他融入了朋友的經曆,他在報紙上讀到的新聞,甚至一些虛構的情節。據推測,這被稱為"來自生命,高于生命"。
是以未來的人不會把這類電影拍成"自傳片",而是拍成"半自傳片"。
特雷弗的成功不僅在法國電影新浪潮中打了第一槍,也為新導演迅速登上巅峰開辟了一條捷徑。
也就是長片處女,拍半自傳電影!
以中國為例,江文的《晴天》、賈樟柯的《小武》、蔣玉麗的《我們在天上看》都是對《四百出擊》的高水準模仿。
就算不是處女作,侯孝賢《童年往事》、羅啟瑞《歲月神偷》、周星馳《喜劇之王》,隻要電影基本紮實,把自己的真實感受、高知名度的作品都簡單攜手。
國外的例子更多,1959年以後,有了這條捷徑,導演開始大放異彩。
回到四百次罷工。
這不是一部特别"好看"的電影。
如果你對電影藝術不是特别感興趣,就沒有必要專門來崇拜。
就像不是必修課,找它的課本,真的有點無聊。
如果你把電影作為專業,它将是一本必讀的教科書。
作為一種精神食糧,這可以引導你掙脫原生家庭和社會束縛,喚醒年輕哀悼之歌的純真。
标題的含義相當明确,意味着熊孩子必須達到400才能成為一個好孩子。
在很多人眼裡,安托萬是個熊孩子。
他上傳了班上美女的照片,在牆上寫下了關于老師的壞話,僞造了缺勤的請假紙條,以免讓老師懲罰自己,還謊稱母親批評......
由于特雷弗選擇跟随安托萬的視角,觀衆很容易看出安托萬實際上并沒有那麼可恨。
美女圖檔很多學生都有手,他隻是替罪羊;
在學校不開心,總是被老師責備,那麼他自然不想上學,隻有在巴黎的大街上,他才能擁有自由和幸福;
母親對他一直很不好,連幹淨的自愛都沒有,他出于無助,出于仇恨,隻說了不該說的話。
安托萬确實犯過錯誤,但所謂的孩子的話并不是禁忌,隻要教育得當,他絕對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誰知道他的繼父相信教育的"四百打擊",一個字就是兩個沉重的耳光。
任何犯了稍微嚴重一點錯誤的人總是處于恐怖狀态。
"你太老了,我沒有做任何像樣的事情!"
這句話應該是很多人都熟悉的。
在學校老師樹立自己的威嚴,家裡的父母就像自己的氣瓶一樣,固執的安托萬不願意被這些大人欺負,他想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建設自己的生活。
他渴望成為一個成年人,這樣他就可以犯錯誤而不受懲罰。
好琪喲桌蕾妮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兩人讨論了各種"無稽之談"的計劃。
桌勒的家家已經成為兩人的革命基地,但兩人出去玩錢,一直從父母那裡偷東西是不行的。
為了發财,他們決定偷走安托萬繼父所在機關的打字機。
特雷弗沒有誇大安托萬内心的憤怒,而是展示了他應對暴力的方式。
如果電影落入制片廠手中,導演很可能會被要求進一步加劇安托萬與老師和父母之間的沖突,把安托萬寫得更差,以換取觀衆的同情。
偷一段打字機,采取偷膠片的模式,加上配樂烘烤氣氛的緊張感,營造出強烈的懸念感。
這樣做可以使影片更加"好看",但也容易失去冷靜和客觀,導緻觀衆失去應有的判斷力。
特呂弗不希望觀衆成為上當傻瓜的印鈔機,他想用紀錄片風格的意象來還原隐藏的現實,讓觀衆去發現和思考。
離家出走,偷打字機,去養老院,安托萬的經曆,都來自他的真實經曆。
他所要做的就是提煉出這些碎片化的記憶,沒有太多的修改,以提醒觀衆,日常生活中不被重視的東西,可能是一個人生活的影子。
《四百出擊》講述了安托萬在成長道路上揮之不去的陰霾,偶爾還有一些令人頭疼的陽光,也有很多人的過去,深埋在過去。
看到安托萬童年的悲劇,那些一閃而過的,也許還有一些錯誤,在未來是可以避免的。
或者告訴自己,給每個孩子更多的善意,少一擊,少一霧;
或者,像安托萬一樣,在影片的結尾,逃離家門,逃離家庭,逃離社會,奔向自由之海。
雖然特雷弗本人并不認為這是一部傑作,但《時代》已經将《四百次打擊》定義為一個裡程碑。
電影于1959年6月上映後,法國電影的新浪潮正式啟動。
從那時起,制作電影和看電影的問題在本質上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