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梅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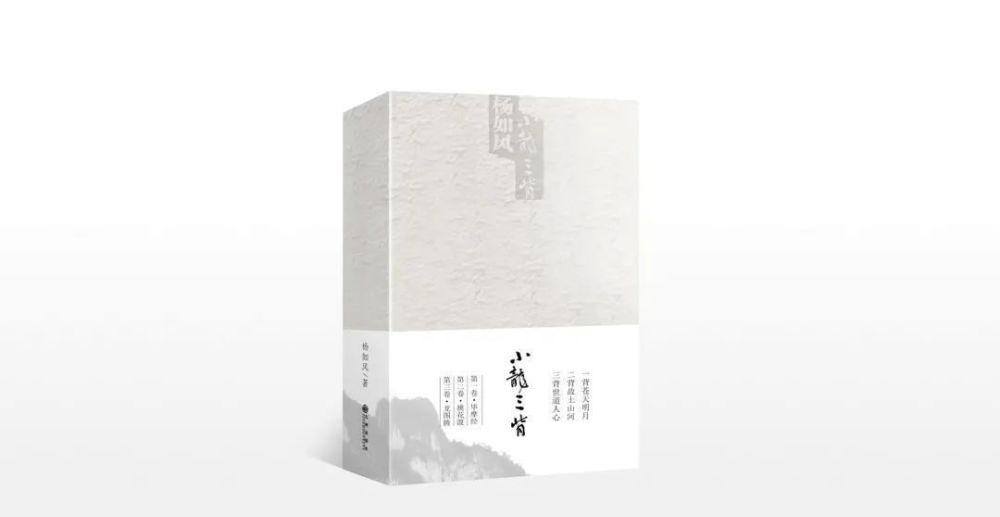
在都市為王的衡量标準下,西部山區是湖北最窮的旮旯;在GDP老大的時代,鄉村是最被遺忘的角落。
一想起來,滿是無奈又無助的老少光棍,青年女子進城了,老實的當女工,漂亮又不安分的混社會。
總之,一地雞毛,快快逃,遺下孤苦老人和留守兒童。
近幾十年來,這大概已成為國人心目中定格的中西部農村畫面。
讀罷《小龍三背》,才知道山村有另外一種寫法,見過桃花渡,不再提桃花源。祖祖輩輩們的鄉音,亦如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産,是我們該膜拜追憶的。每一個辛勤勞作的父老鄉親,都用雙手在田地裡作詩,都用愛心滋養孩子的成長,都用善良的品格在世間留下傳奇……
感謝世間還有楊如風這類人,用最優美的筆描繪山村美景;用最有力的刀刻畫鄉音民俗;用最深情的歌唱出依依不舍;用最動人的夢,回到夢開始的地方……
最重要的,他生于1979年,講的就是我們眼前的事,《平凡的世界》故事太老了。
中國人的國際形象提升遠不如經濟地位的上升來得迅猛,原因多多,一條是沒有信仰或者叫金錢崇拜。舉例:歧視用詞“鳳凰男”,醜化從農村到城市奮鬥的男青年。廣義上講,這個群體應該占了城市青年的一半,應該是奮起反駁,結果在城市的高房價和丈母娘刻薄的殺人目光下,敢啰嗦的都沒幾個。
世俗一點也沒錯,錯的是隻知道世俗這一種活法。
按全世界的發展規律看,人民溫飽和城市化基本完成後,人的精神追求會更加豐富,對美好生活的了解會更加多元。
我原以為楊如風寫家鄉是“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看完之後才知道自己錯了。家鄉的山山水水,故土的趣事轶聞,本來就是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富礦。
由此想到祖國近千萬平方公裡山河,我們的好地方太多了!我們的日子太美了!
我怎麼愛得過來?
書評一 镖師楊如風
文/彭四平
舞文弄墨與舞槍弄棒沒啥兩樣,都是靠本事吃飯。《今古傳奇》就像一個镖局,早年憑《玉嬌龍》這趟镖,聲名鵲起,家喻戶曉。四十年來走镖無數,影響幾代人。楊如風乃傳奇镖師。每遇躲閃藏遮之文,拔劍施呈,化腐朽為神奇;啰唆繁缛之處,使出獨孤九劍,有進無退,立馬峥嵘軒峻。閑暇之餘,苦修秘笈,遍訪名師,習得天下獨門武功,卻龍蟄蠖屈,不求聞達。壬寅年,集二十年之功力,《小龍三背》,镖行天下。一腔熱血深情,恐怕隻有天知,地知,己知。
序文能幫我們掂量這書的輕重、深淺與價值。“楊如風的文字極簡而獨具風格,辨識度很高,既察賦古老民族的血液和氣質,意蘊深沉,又具有當代大家的目光和胸襟,視域宏闊,煥發出最為本真的魅力。”“在他身上,我們能感受到鮮明的中國傳統詩學的審美志趣,同時又很容易辨識出,他不斷開拓和創新的精神。他在吸收和改造中并進,建立自身的美學價值和精神體系。”有些書之序,像韓愈給人寫的墓志銘,雖然不乏名篇佳作,卻多吹捧之作。《小龍三背》的序,評詩論文,有磅礴的胸襟和氣勢,寫得客觀平實,沒有拔高之筆、溢美之詞,見解新穎,文字精準,似一把打開楊如風作品密碼的鑰匙,讓人醍醐灌頂,如飲醇醪,如沐春風。
總镖頭鄢元平,手持古劍贈英雄。他說:“我為詩為文,自認為是自帶雅香的人,但之後把詩寫得過媚,故而為詩的嘴臉上總有粉黛和油彩,像花季已過的頭牌,那粉牆的詩文,總會掉下一些敷得不結實的殘粉。如風的詩文,很少搽脂抹粉,清新脫俗中藏着傲骨。他的詩外洩了他清雅背後所隐藏的硬度。”
鄢元平的雅量,讓我想起作家丁玲。1984年,丁玲坦誠地說:“史鐵生寫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如果作者沒有到過陝北,便寫不出來。我到過陝北,對他寫的高原我能感覺到,他寫的破老漢我也很熟悉,我看這篇作品可能比沒有到過陝北的人更感到親切一些。但是,我寫不出那樣的生活來。因為史鐵生在陝北插隊,和老鄉相處的時間長,和老百姓一起過日子。我在陝北是住在機關的窯洞裡,腦子裡有人物、有地點、有情景,但是不如他深入熟悉。”那一年,丁玲80歲,她坦陳不如33歲的史鐵生。鄢元平愛才心切,不惜調侃自己,這種扶持年輕人的榜樣力量值得尊敬。
《小龍三背》共三卷,分别為:《畢摩經》《桃花渡》《龍圖騰》。書名風清月白,劈面驚豔。它們各自為陣,如險要之地,先發一軍據之。裝幀别具風格,采用鎖線空背裝,書脊與印品呈空背狀,打開每一頁像綻開的雪蓮,冰清玉潔容顔,橫卧天地之間。
第一卷《畢摩經》為詩集,錄詩歌九組。融寫實、寓言、象征于一體,其功力似《天龍八部》中的六脈神劍,以無形劍氣立足江湖,内力深厚,招數神奇。那格調古樸的語調,讀之,即有登山賞景途中至一涼亭歇足飲茶之快,閉目之間,又仿若“女人們唇齒間吐放的火焰”,“喚醒血液裡那些死去的日月星辰”。他那振羽淩空的氣勢和豐富多彩的想象,看是日常一次細微的觀察、一場平凡的所見、一次感悟的提升,實則是連續性的感覺不停地閃現,組成了石片在水面一連串飛漂的文字,像一幅精緻的油畫,能夠引起一種實體與心理的摩擦,為崇高的心靈與純淨的藝術,樹立了一個典範。
《月光下的查姆湖》寫得俏皮自然,跳躍有趣。“有多少魚像我們這樣/雲山蒼蒼,湖水泱泱/又此去一别,山高水長”。雲是雲南,湖是湖北,雲也是湖北的白雲,湖也是雲南的查姆湖。這句化自範仲淹《嚴先生祠堂記》:“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我被這神奇的“化骨綿掌”擊中,滿臉捧着甜蜜的淚珠。最後一句,12個字,卻描繪了臨别動人的圖景,讀來宛如千萬聲珍重:“你問,歸期何期/我說,此魚何魚”。物我相容,大膽深刻。
第二卷《桃花渡》為散文集,錄散文十章,卻寫出了很多平常人難于言說的真實。在細微處,他觸探大時代;在大格局,他注意小人物。每一道轉折,每一陣波瀾,都是一個艱苦生命的強烈暗示,也是一個浩蕩時代的重要象征。捧之,不禁以淚句讀、低回不已。那些人,你若為其命運流過淚,就不能說不認識;那些事,你若為其遭遇歎息過,也不能說不知道。讀到會心處,真是靈犀一點,妙不可言。《讀書》中有這樣一個細節:“國小時,周末在家夜讀《水浒》,不小心睡着了,失手将枕邊的油燈打翻,燒毀了蚊帳被單,差點兒釀成火災。雖未遭父母過多的責罵,卻自知罪孽很深,數日不敢語”。
這讓我想起1981年諾貝爾獲得者戴維·休伯爾,小時候在地下室裡用砂糖和其他化學藥品造“炸彈”。為了不把地下室裡的瓶瓶罐罐炸飛,特意到院子裡進行試驗,沒想到“炸彈”的威力超出了他的想象,把地下炸了一坑,房屋毀損。小休伯爾害怕極了,不知道父母會怎樣懲罰自己。令他沒想到的是,父母并沒有處罰和責罵,而是告訴他:既然做科學實驗,就必須講究科學、嚴謹,容不得半點的僥幸和魯莽,更不能想當然地行事。
批評孩子的過錯展現了家長的嚴格。但在特定的條件下,寬容也是一種有效的教育方法。這次“爆炸”事件,給休伯爾一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記住了父母的話:“以後不論做什麼事,都要講究嚴謹的科學方法。”
我們知道,作品一旦成為社會的公開出版物,作品的初衷并不一定就是作品真正的價值所在,而許多認識功能、審美功能都是讀者重新發現的,一部書的作用是作者和讀者共同創造的。楊如風寫父母的寬厚的胸襟,好比從飛沙、麥浪、波紋裡看出風的姿态。讓我讀出,一個能寬容他人的人,比較容易擺脫不良的情感的束縛,也容易和睦地與人相處。這點在楊如風身上已經佐證。
楊如風散文視野并不寬闊,多以反映童年生活和親人朋友間的情感為題材。我驚歎于他寫得如此跳脫、如此雅緻,讓筆下的風景慢慢鋪成絢麗的圖畫,似一座秀麗的、盛開着鮮花的花園,徜徉其中,感覺到滿滿的愛意。就像武俠小說中最厲害的武功,最後也敵不過一個“俠”,最經典的文學,無非是傳遞愛。“愛”不是一兩人的事,而是一種超越塵俗和悲憫同情的愛,讓人心中充滿美好的向往,像對俠客替天行道一樣期待。
第三卷《龍圖騰》集創刊詞、卷首語、傳奇隐括、序文等。與前兩卷相較,這一卷的獨特之處,在于配以發表在報刊上的作品插圖,堪與董橋的《小風景》媲美。《小風景》開本厚闊,幾乎每篇都配有董橋自藏多年的書畫精品,美文佳圖,似才子佳人,天造一雙。而本書的插圖出自于多位國内頂級連環畫家之手,風姿多變,所幸月圓花好,終究琴瑟相調。
“傳奇隐括”雖為稻梁謀的命題作文,卻有如白玉蘭一般,灑下閑閑淡淡的一剪疏影,有一絲懷舊,有幾縷感傷,無邊的月色終于将冰心釀成了清香甘醇的酒,給人以繼續前行的信念和力量。掩卷之餘,傳遞給我的,不僅是工作中的專注精神,更多的是在想那些诙諧風趣、莊重典雅的卷首語,我不知道他那些怪念頭從哪兒來,其切入的角度、行文的詭谲以及彌漫的一層神氣,讓人望塵莫及。
镖師楊如風的職責在這卷顯得淋漓盡緻。“金鳳凰榜新時代文庫總序”“今古傳奇告全國讀者書”等重要文告以及《中國報告》《中國榜樣》等書出版,他都要奉命護镖,小到字詞句,大到政治導向、價值取向,不得有半點閃失。總镖頭鄢元平說他“像一頭不知疲倦的驢,不斷把《今古傳奇》這個大磨推出些動人的聲響”。
在護镖之餘,楊如風還要與其他“镖師”叙舊,吹牛,切磋技藝,探讨心法。譬如他在池的《挽斷衣袖留不住》一書推薦語中寫道:
大約是在十六年前的夏日,楚地突然現出一位年輕人。他瘦削,白皙,安靜,似乎并非什麼厲害人物。卻隻是數日,江湖就不平靜了。是年武林大會,沒有任何年輕人敵得過他一招《一路呻吟》。這位叫做池的的年輕人迤迤然拔得頭籌,封為孝感君。後入傳奇,掌門書局,兼中華文學副統領,名動天下。庚子春,孝感君去職還鄉,閉關丁憂,旋有《挽斷衣袖留不住》。斯是孝子,可歌可泣可歎;實屬奇書,至真至性至情。
這段文字,像燒出來的瓷器,出窯後不宜妄改。從中可以看出,楊如風對文字有種近乎執拗的潔癖。
《小龍三背》從廣義上來說,都是詩,亦是優美的散文。他修辭考究,氣度高貴,有人說他以敏銳的觸角,攝取土家族地域風物,傳承中國傳統的審美志趣。他善用“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的手法,把叙事拔高到抒情的境地,悠然作結,令人神馳。
以一種抑制不住的感動和激情,反複閱讀這套書,終于不得不承認,這是時間之書。那不是抽象的時間,而是以感覺、以情緒、以澎湃的力量,記載着時間的味道、承載着時間的重量。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像一顆發光的卵石,在激流中翻滾,為的是創造更寬更廣的流域。
合上書卷,一句句鋒铓飛劍戟,一段段霹靂卷風沙,我腦海中浮想聯翩。這部作品似乎激活了我的慧根。讀書似探險,必須有很強的好奇心,我是帶着無比的快樂去讀的。賈平凹說:“時下的人,尤其是也稍要弄些文的人,已經有了毛病,讀作品不是浸淫作品,不是學人家的精華,啟迪自家的智慧,而是讀賣石灰就見不得賣面粉,還沒看原著,隻聽别人說着好了,就來氣,帶氣入讀,就隻能橫挑鼻子豎挑眼。這無損于天才,卻害了自家。”楊如風的書可以收藏了常讀。常讀就要學會聯想,要舉一反三,這種聯想是有趣的,好似跑野馬,如果記得自己的紮營之處,跑了,看了,也許明白了,自己會心滿意足地回營。
荷爾德林說,在躊躇的時域裡……存在一些持久的東西。在傳奇镖局,镖師楊如風永遠連着“今”和“古”,其武功秘笈“無多語,隻有銷魂與斷腸”。
也許,他無意埋下的種子,會豐盈一個盛放的季節。
書評二 漢語山河
彭四平
天下誰敢這樣取名,恐怕隻有楊如風。
帶着好奇走進詩集《畢摩經》,首先就被第一首《土》征服。那些看似平淡的陳述句型,被有意識地在一個個名詞那裡截斷,鑄成詩行。瞬間,名詞的張力突然擢升。這些孤立的句子,既有口語式的松和,又有箴言般的緊緻,渲染着一種由靜而動的美的意境,讓原本尋常叙述的場景變得光芒四射。
楊如風的《金木水火土》組詩,有天地萬象皆為我的豪邁,傾蕩磊落。全詩由物及人,字裡行間勃發出無盡的清風烈概,令人肅然起敬。我尤喜歡《木》中的一節:“我說的是塵封曆史的古籍/遊俠腰上的劍柄/老情人溫存過的手杖/紅瓦青磚之間的/百年棟梁”。這抓住靈魂的詩句,像山中的雲霧,慢慢往上升騰,像雲間的仙子,讓我浮想聯翩。是做棟梁還是做手杖,這不是木頭所能決定的。決定做什麼,适合做什麼,是材質,是人。人,難道不也是如此嗎?詩歌的偉大之處也許就在這裡,它在塑造意象的同時,也為我們塑造一個頓悟的空間,一個未知的精神世界,讓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彼此接納,有所啟發。
一首好詩像行駛的船,是需要動力來源的。而推動一首好詩的動力來源是不同的,有時是一組意象,有時是内容或節奏。以鄉愁開端的《三背河九首》,在民俗、民族的視野裡,呈現生命的意義和生活的内容。其中《山頂的老人》,寫得行雲流水無拘無束。從近處可觸摸的大雪,到遠在山上的神仙,從山上到山下,從生到死,寥寥數筆,把時間拉長,把空間拓寬。詩中一句“我行路難/你望斷群山”的特寫,就讓濃濃愛意破門而出,讓人深深感動。《母親的嫁奁》和《兩條木魚》,傳遞一個人無法超越他的時代,唯一能做的是為他所生活的時代作證。讀《小名兒》,似寶玉初見黛玉:“雖然沒有見過,心裡倒像是舊相認識,恍若遠别重逢的一般。”讓人觌面傾心,一見如故。《小兒回鄉》,則是一首沖擊靈魂的歌謠:
小風,我帶你回到桃花渡/就是要帶你回到大樹根部//族譜上/那些發黃的名字/你并不認識/但這裡的一草一木/每個苕和洋芋/都會指引你/找到血脈之親
西方哲學接近生命的是文學與生物學。文學的進路是感性的、浪漫的,生物學的進路是科學的、自然主義的,都沒有進入生命問題的中心。中國鄉村接近生命的,是族譜、家乘。那些發黃的名字,小時候,我們雖然不認識,卻像一根蔓藤,遲早要攀爬上去。這就是詩眼所說的“帶你回到大樹根部”。詩人把主題藏在靜靜的叙述中,不靠抒情而是靠語言内部的生命力打動讀者,有“清風徐來,水波不興”之妙。
文無第一。說誰的詩歌寫得好是有風險的。文學作品的欣賞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從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道理。就拿唐代詩人賈島“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這兩句為例。詩人寫好後,發現“推”不如“敲”,又感到“推”字有它的妙處,猶豫不決,無法定奪。巧遇韓愈,判定:“敲字佳矣!”從此,《題李凝幽居》的詩,一“敲”定音。“推敲”二字也成為文壇佳話,傳誦千古。哪想到了近代,楊樹達、郭沫若、朱光潛開始論戰“推”和“敲”。楊樹達認為“‘敲’字響,‘推’字啞,故敲字優也”。郭沫若認可“敲”,他說:“寺門掩閉,恐怕敲的可能性多些。”楊樹達是文字學家,他從語言角度考察;郭沫若是作家,他從情理上分析;朱光潛是美學家,他深入地探究原詩特定的境界:
他需自掩自推,足見寺裡隻有他孤孤零零的一個和尚。比較起來,敲沒有推的那樣冷寂。就上句來看,“推”似乎比“敲”要調合些。“推”可以無聲,“敲”就不免剝啄有聲,驚動了宿鳥,打破了沉寂,也似乎平添了攪擾。是以問題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個比較恰當,而是在于哪一種境界是當時所要說的而且與全詩調和的。
詩歌上的字義,是極其細微的創造活動。這推敲兩個字從賈島、韓愈、楊樹達、郭沫若、朱光潛曆經一千多年,仍有異議,看來每個人的學養、境界、見識不一樣,對作品了解的認識也不相同。
我崇尚文章無義,讀來無趣。佛羅貝說:“思想與形式分開,全無意義。譬如物體,去其顔色形模,所餘不過一場空。”楊如風的《歲月》将深邃的意境和哲理高度統一。其思想境界,比蘇轼的《定風波》、秦觀的《踏莎行》都要高。
大地空空如也/所有的記憶都已覆寫積雪//我平生不會等待/害怕一夜之間白了頭發/害怕歲月帶我去的是墓地/不是花開//知道嗎/愛你,我有朝聖一樣的信念
“大地空空如也/所有的記憶都已覆寫積雪。”詩人在這裡表達的是遺憾。《踏莎行》作于秦少遊晚年被貶到郴州時,寫得哀苦凄厲。“驿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潇湘去”。“砌成此恨無重數”,他把恨一點一點地“砌”成,如同圍牆磚一塊一塊地壘在一起,這種重重疊疊悲憤,是數不清也說不盡的。《定風波》是蘇轼于“烏台詩案”幸免于難後,被貶黃州所作。寫的是一種曠達,“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歲月》寫的是一種進取,“我平生不會等待/害怕一夜之間白了頭發”。
古來不知有多少英雄歎息無用武之地。辛棄疾在《水龍吟》中感歎“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郞才盡”。“劉郞”這裡指劉備,語出《三國志 陳登傳》,說許汜向劉備責備抱怨陳登怠慢他,劉備聽了卻責備許汜在天下大亂之際,隻求物質享受,整天買田地、置房産,胸無大志。辛棄疾用這個典故,是說自己要是在江南買田置地過一輩子,如果遇到像劉備這樣有大志的人,難道不應該感到羞恥嗎?忠憤之情溢于言表。
談唯美,蘇轼、秦觀寫得好。談意義,楊如風更勝一籌,“知道嗎/愛你,我有朝聖一樣的信念”。文學是什麼?文學是給人希望和力量。如果得不到善的教益、美的滋養,這個世道和人心可能回到原始社會。詩的好和壞,就像推和敲,哪一個字比較恰當,在于哪一種境界。
有時候,閱讀并不改變我們生活的本質,卻讓我們收獲意外的驚喜。《畢摩經組詩》讓我知道彜族文化瑰寶《彜族畢摩經》,與甲骨文、蘇美爾文、埃及文、瑪雅文、哈拉般文相并列,代表着世界文字一個重要起源。詩人受此啟發,懷着激越之情,創作的《畢摩經組詩》,跟音樂一樣,是看不見欲望的記錄,是靈魂的神秘造就的音符,似彜族文化靈性“附體”。其中《小豹子笙》是神來之筆!“噓!遠方獸/深山木/讓我為你跳一支舞/小豹子笙。”讓人流連忘返,一唱三歎。
《月光下的查姆湖》,寫得俏皮自然,跳躍有趣。這首詩有兩個意象:水和魚。“水”和“魚”有着可說與不可說的差別,而詩歌寫作的困境,正是要用可以言說之水,表達不可言說之魚。
此時,我們在岸上的樣子/應該就是魚在水裡的樣子
這跟拟人法不同,拟人法是以物拟人,是一種比拟。這是從水中看到詩人的性情,這個性情是景物本身所具有,不是詩人外加進去的。《文心雕龍 物色》曰:“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其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意思是從風景和草木中探索情貌,即近乎于山水中見性情。
有多少魚像我們這樣/雲山蒼蒼,湖水泱泱/又此去一别/山高水長
“有多少魚像我們這樣”,看似平淡,卻彰顯詩人的語言經驗和意象光譜。有如《齊物論》講“蝶夢”中的蝴蝶栩栩自得,是蝴蝶的栩栩,不是外人加上去的,有“身卻山水而取之”的快意與灑脫。“雲山蒼蒼,湖水泱泱/又此去一别,山高水長。”這句化自範仲淹《嚴先生祠堂記》:“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我被這神奇的“化骨綿掌”擊中,滿臉捧着甜蜜的淚珠。最後一句短短12個字,卻生動描繪了臨别動人的圖景,讀來宛如千萬聲珍重:“你問,歸期何期/我說,此魚何魚”。物我相容,大膽深刻。
用王國維的标準來說,此詩不隔。何謂不隔?物我渾然一體也。
楊如風的詩看似徐緩、輕柔、平靜,卻特别注重創構意象呈現詩之美,将天地自然之象融進他的詩學,給人意象新奇、生動深刻之感。但我更喜歡其對語言的掌控能力,如西門吹雪舞劍,一會兒輕盈如燕,一會兒驟如閃電,穩當貼切,沒有瑕疵。譬如詩人十幾歲時寫的《山裡春秋》:“老牛一聲哞叫/犁開沉睡的黑土地/樸素的季節/在輕揚的竹鞭上/綻開了流動的陽光/沉甸甸的希望/鼓鼓脹痛/春天的夜晚”。詩人用寥寥數筆勾勒出一幅聲色兼具的畫卷。此外,《我用春天來擡你》,用自然界中最淺顯的道理來說明人類情感中相對複雜的内容。《愛情地圖》,看似平常的一首小詩,卻産生了永恒的魅力。“因為你的眷戀的純淨的心/就是我幅員遼闊愛的祖國。”
詩人的風雲之氣,在《中國,我為你舉杯》表現得淋漓盡緻。“斟滿 秦嶺的煙霞/斟滿 五嶽的巍峨/斟滿 竹簡詩經的白露清霜/斟滿 線裝唐風的明月光輝/斟滿 九曲黃河長江萬裡的濤聲/斟滿 一百年的鮮花與淚水。”這組排比,不斷重複,把自然美景和五千年的文化,加以羅列:天上地下,白晝黑夜,春夏秋冬,苦難與鮮花。描寫生動,意象豐富,有變化,有起伏,把嚴肅的政治内容,寓于優美的詩句中,形成強大的精神咬合力,讓人讀後,心中充滿雄渾的壯闊的浩然之氣。
培根說:“讀書不是為着要辯駁,也不是為着要輕信和盲從,而是要去思考和權衡。”中國新詩自五四崛起,經過一些曲折或螺旋式的發展,有些詩像古詩詞一樣,擁有經得起解釋的堅定的秩序,字字句句不可随意替換,構成一個完美的整體;有些詩則在逐字逐句解釋的重壓下,成為時代的灰塵。楊如風的《畢摩經》以字為劍,将那沉睡的母語,賦予煥麗炳蔚之色,在自然陳述和适當的倒裝錯落中虎嘯龍吟,建構漢語山河。那美妙的,細小的,漢語的花朵,如同山中雲霧,沖懷罥袖,掩苒不脫。
他那一勺明鏡的文字,像一葉輕舟駛出江河,激起我五味雜陳之感;他那文本探索的詩行,沉浮、依附着人生的浪濤,如千軍萬馬在我體内洶湧奔騰。而他的文字,依然和大海一樣平靜。此等神功,正如《小龍三背》總序所說:“在他身上,我們能感受到鮮明的中國傳統詩學的審美志趣,同時又很容易辨識出,他不斷開拓和創新的精神。他在吸收與改造中并進,建立起自身的美學價值和精神體系。”
也許,我們從楊如風詩歌中傾聽到的,正是詩歌本身的聲音,清淨、醇正而又充滿力量。
附:編輯手記
《小龍三背》“出窯”記
我們總在尋找自由自在的生活,在紛紛擾擾的世界裡體驗新鮮感;我們總忘不了回家的路,在陌生的城市思念着莺飛草長的故鄉;我們沉溺在時間的海裡,與美麗邂逅,感受生活的洶湧。這些生活的道理、故鄉的回憶、人生的意義往往在一卷書中,便可見端倪。
2022年1月,《小龍三背》沾着些新年的喜氣,一背蒼天明月、二背故土山河、三背世道人心,動身來見你。
版式設計活用留白藝術美
關于設計,玉嬌龍傳媒美術總監李曉玲是核心。她似乎做什麼都是興趣使然,然後極盡努力,做到專業。早在十多年前,《小龍三背》還沒創作完成之際,她就期待着:如果作者出版,自己一定要争取來做整體的設計。你不知道吧?她特意收集整理了作者曾編輯過的作品插圖,為來日的設計做足了準備。
對于圖書設計的熱情與向往,始終是她的源動力。
基于《小龍三背》“簡約大氣,展現韻味”的設計方向,她用大面積的留白,給予設計呼吸的空間。留白區域的環繞與陪襯,極好地襯托出文本的核心内容。這樣的留白充分凸顯了設計的極簡風格,在保證設計感的同時也将内斂、沉靜深藏其中。
三卷書的設計各有特色。
第一卷《畢摩經》為詩集,每組詩的名稱即為章首。這本作者回望故鄉的詩集,将進入回憶的通道藏在書頁之中。淡淡的書香,在翻開封面的那一刻起就開始為記憶鋪墊小時候的味道。
第二卷《桃花渡》為散文集,插圖和題字裝置在每篇散文裡。插圖簡約秀朗的線條,使靜物“活化”,栩栩如生。十幅題字為書的文化氣息增色不少,筆墨嚴謹而不失靈動,顯示出書法的韻律之美。
第三卷《龍圖騰》收錄了作者從業二十年以來起草的創刊詞、卷首語、傳奇隐括、序文等。與前兩卷相較,這一卷的獨特之處在于傳奇隐括欄目,配以發表在報刊上的作品插圖。這些插圖出自于多位國内頂級連環畫家之手,風格多變,妙筆生花,不由得讓人停下翻書的動作,聚精會神地欣賞它的一筆一畫。
慢下來的時光,适合讀書,讀一位少年收集的故事,讀他驚豔、溫柔的詩句。他在冬天儲存浪漫,好在春天饋贈給你。
封面設計演繹簡約進階感
一個令人心動的封面,是讀者選擇和翻開這本書的第一要素。看慣了印着花花綠綠圖案的圖書,《小龍三背》簡約大氣、古樸醇厚的風格反而更加亮眼。
書名《畢摩經》《桃花渡》《龍圖騰》以清刻簡體的模樣端坐在右上角。書名附近緊挨着作者家門口奇峰貓兒岩的剪影圖形,給淡雅摻進了一點俏皮的味道。三本書的書脊和封面左側分别用金棕色、草綠色、中國紅譜出自己的“主旋律”。根據不同的文體,顔色也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
《畢摩經》的金棕來自大地的堅定、自然的和諧、旺盛的生命,一反尋常棕色落寞、蕭索的刻闆印象,留下一片希望與活力;《桃花渡》的草綠帶着春天的氣息,穿過花草蟲鳴,在心頭灑下陽光;《龍圖騰》的中國紅傳承着紅色血脈,蘊藏獨具東方特色的古典氣質,散發傳統的魅力。
這樣的封面集視覺和創意為一體,用極簡主義為《小龍三背》抹上了進階與神秘之色,放大了一份自由随性。隻需一眼,你便知道這套書有點兒東西。
印刷工藝埋下設計小巧思
一本好書在印刷工藝的“武裝”下,總能搖身一變,成為實用與美感并存的藝術品。
在《小龍三背》的印制過程中,顔沫印刷的胡必煌先生作為印刷方面的行家,一定具備了某種眼光毒辣的行業捕手氣質。在探讨印制工藝時,他不時來個電話:“玲子,你那個貓兒岩圖案和書名的字啊,還是做個UV,最好還是做鐳射UV,這個工藝是現在最時尚的,但絕對有低調的進階感,印刷之後書在陽光下會帶點兒彩色……”隻言片語中,滿是一個行家的專業自信。
你可能不知道,出版故事中有不少意料之外的小插曲。
三分鐘走完半個小時的路程,确定好封面手揉紙的品種;加一些巧思,解決封面紙張較薄的問題;裝幀方式從鎖線膠裝改為鎖線空背裝……
塗一鳴、胡必煌兩位先生作為這些故事的主角,總是以認真負責的态度,在不經意間給我們帶來滿滿的感動。
樣書印刷出來後,就可以開始制作函套了。這一環确實是《小龍三背》最藏心思的一項。
函套僅有“楊如風小龍三背”七字,做成壓痕凹凸工藝,讓整套書更大氣、有品質。值得一提的是,壓痕全銅模具還是從廣東專門定制而成。這就是對細節的極緻追求。腰封上蒼茫的貓兒岩,與封面半圓形的貓兒岩圖案遙相對應。腰封“小龍三背”黑色書法字型,用的是UV過油工藝。三卷書名與《小龍三背》的簡介相對稱。函套用紙與封面一緻,腰封用紙與環襯一緻。
每一個地方都藏着設計的小心思,環環相扣、相輔相成。把整體和系列相融合,結成了多因素完美集合的“果”。
以意為先,大道至簡。
在簡約中,創作出最特别作品,這是《小龍三背》給讀者們的驚喜與浪漫!
裝幀工藝:
1、封面:157g手揉紙四色印刷,貓兒岩小圖及每卷書名做鐳射UV過油工藝;
書脊及封面左側處色塊專色印刷;前後單環200g白卡紙,前後單環襯(雙彙特種紙120g色纖維紙)。
2、裝訂方式:鎖線空背裝
3、内心:120g華碩紙,單色印刷。
4、函套:157g手揉紙裱工業紙闆,封面“小龍三背楊如風”處壓痕工藝;絲帶抽取式設計
5、腰封:雙彙特種紙120g色纖維紙四色印刷,書名《小龍三背》UV過油工藝
封面設計:
封面用紙采用手揉紙,其韌性、質感、紋理俱佳,契合《小龍三背》古樸、厚重的韻味。書名《小龍三背》采用宋體字,各分卷書名《畢摩經》《桃花渡》《龍圖騰》采用清刻簡體,古樸厚重。半圓形圖案為作者的故鄉門口貓兒岩的簡影圖形,與書名《小龍三背》呼應,展現作者“一背蒼天明月,二背故土山河,三背世道人心”的使命擔當。
三本書的書脊和封面左側分别用金棕色、草綠色、中國紅色塊,展現每卷書的文學屬性。《畢摩經》:金棕色常被聯想到大地、自然、簡樸;《桃花渡》:草綠色代表清新、生命、和平、自然、生機;《龍圖騰》:中國紅則寓意驕傲自豪、積極熱情,也是傳統的中國紅。
版式設計:
《小龍三背》三卷書的内文版式設計注重留白,考慮到讓讀者閱讀起來輕松。翻開版權頁之後,映入眼簾的是一句“小龍三背,一背蒼天明月,二背故土山河,三背世道人心”,這是對《小龍三背》書名的诠釋。用灰色8磅宋體字,加上50%灰階的作者簽名,低調、内斂。三卷書的每個章首,僅為這卷書書名的英文+此欄目名,均為8磅字,簡約設計,突出文學性。
三卷書的設計各有特色。第一卷《畢摩經》為詩集,錄詩歌九組。每組詩的名稱即為章首。設計處理依然是留白較多。詩集中的每一個标點符号都是一個字元的空距,這是每個标點逐字手動調整,保持詩句整齊一緻。
第二卷《桃花渡》為散文集,錄散文十章。此卷裝幀獨特之處在每篇散文均配有插圖和題字。插圖是向著名插畫家段明先生約稿。段明先生表示:“隻有領悟了文章的精髓,才能畫出文章的風骨,這需要作者有敏銳的捕捉力和洞察文章精神核心的思想。”簡約秀朗的線條,将每篇散文表達得淋漓盡緻、栩栩如生。十幅題字是作者分别向十位書法名家約稿題寫,古樸厚重,彰顯韻味。
第三卷《龍圖騰》為從業二十年以來,因工作需要而起草的創刊詞、卷首語、傳奇隐括、序文。此卷書的版式設計依然呈系列性,字型字号版心與前兩卷保持一緻。與前兩卷相較而言,獨特之處在于傳奇隐括欄目,配以已發表在報刊上的作品插圖,這些插圖均出自于多位國内頂級連環畫家之手,風格及表現手法各有不同,極具韻味,亦是紀念。
鎖線空背裝:
《小龍三背》采用鎖線空背裝訂方式。常見傳統的裝訂工藝為膠裝。鎖線空背裝是用線将各頁穿在一起後,書脊與印品的各頁并不采用膠水粘合在一起,呈空背狀。這樣,圖書更容易翻閱,因為每一頁都可以攤平,帶來更好的閱讀體驗,不用擔心書頁之間開裂。而膠裝往往是無法把書全部展開的。
同時,鎖線空背裝的設計也是一種創新,但其過程繁瑣,須将紙張折頁,并用針線穿孔縫制,鎖線後成書。成本也比較高,這種裝幀工藝比較少見。在友善閱讀的同時又最大限度地展現《小龍三背》古樸、自然的特色。
函套工藝:
函套的設計是從功能性和實用性角度出發對圖書進行保護和美化。
《小龍三背》函套采用與封面一緻的手揉紙,呈系列性。函套設計僅有“小龍三背楊如風”七字,字型采用書法字加大标宋字型,做凹凸壓痕工藝,立體感更強,整套書更顯大氣有品質。凹凸壓印,又稱壓凸紋印刷,是印刷品表面裝飾加工中一種特殊的加工技術,它使用凹凸模具,在一定的壓力作用下,使印刷品基材發生塑性變形,進而對印刷品表面進行藝術加工。壓印的圖案,顯示出深淺不同的紋樣,具有明顯的浮雕感,增強了《小龍三背》的立體感和藝術感染力。
為了友善讀者抽取圖書,函套特采用絲帶抽取式設計,較之于傳統的在函套半圓形孔的抽取方式,更實用美觀。
設計的腰封上以蒼茫的貓兒岩作背景,與封面半圓形貓兒岩圖案遙相呼應,展現作者對故鄉的赤子之心。腰封“小龍三背”黑色書法字型,作UV過油工藝,進而使文字更加突出。“小龍三背”書法字兩邊,三卷書名與小龍三背的诠釋做對稱處理。腰封采用纖維紙與環襯用紙保持一緻,更是展現整體性和系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