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筆集《喊山應》和王躍文的“真”
雷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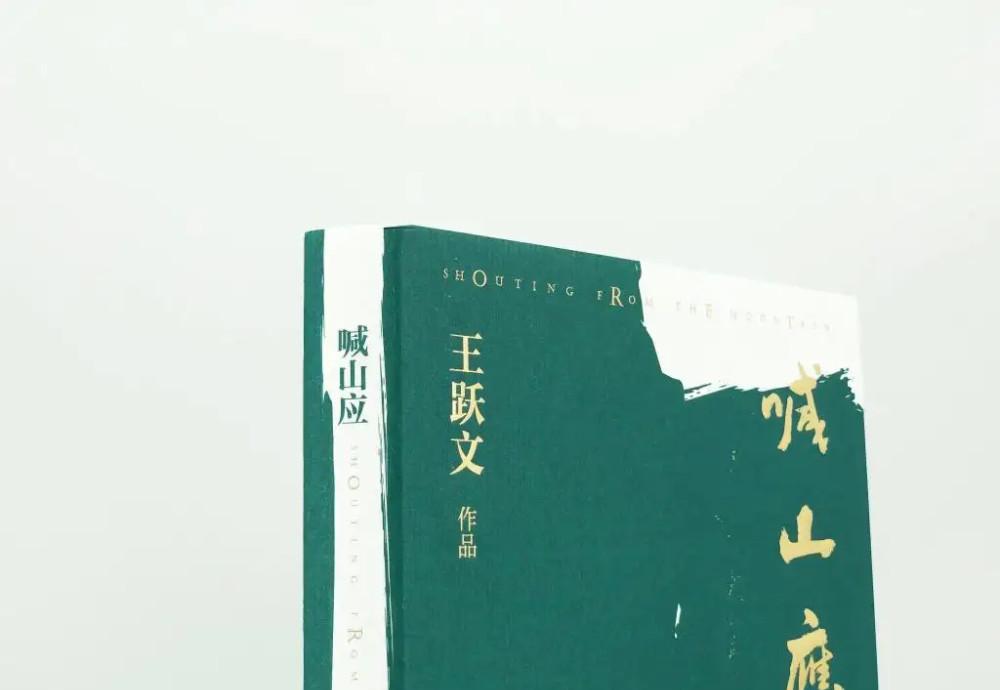
2021年9月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随筆集《喊山應》是王躍文的最新作品,這本集子分三個部分“我的文學原鄉”“我的文學創作”“我的文學檢讨”,書中作者對自己文學曆程的回顧與檢省同之前發表的《王躍文文學回憶錄》《無違》等構成事實的互文關系。不同的是後者基本都是在與他人的對話中展開,而《喊山應》呈現的是獨語,“喊山”這一行為本身就是喊山人對自我的追索,大山回應的既有山的模樣,更有人的模樣。是以作者在《喊山應》集子中有關文學及創作的細緻入裡的爬梳,使世人更深切地領悟了王躍文其人與其文的關聯,一個作家的來處、現處與去處在絲絲縷縷的叙述中明晰,閃閃爍爍光明不滅。
記得以前看《無違》,作者談到自己童年孤獨時與土蜂的對話,這個細節令人印象深刻。由于家庭出身與其他兒童在心理情感上的疏離,即便遊戲都無法治愈,因為遊戲中的角色配置設定也是這疏離中的一部分。與土蜂對話是作為兒童的王躍文治療自己的方式,成年後,文學替代了土蜂。在王躍文不同的談話場合,也在最新的《喊山應》裡,他一次次傳回到人生初始的這個階段,在由父母際遇所牽扯的人事糾葛與生活艱困中去打撈浮光塵影。這種有意重複的意義在哪裡呢?概言之,它們是王躍文創作中距離(或時間)美學的生成起點,這種美學的核心就像作者小時候鄉人對他的評價“不太愛說話,悶在心裡想事情”,即把自己變成旁觀者并去揣摩他人的心思,對此王躍文了然于心,他說“在我自己的内心裡,這是一雙冷眼,敏銳洞察一切”。這雙“眼睛”的獲得是作為右派兒子的王躍文童年與他人的身份區隔所産生的必然結果,也是以他的自我意識裡天然具有距離感或時間感,并将之融于筆下的故事與人物中。
這裡的時間感接近于日本學者丸山升的了解,其認為時間感是連接配接思想和現實的中間項,是個體與時代之間最具主體性的結合方式。這裡的距離與中間項都指向作家在社會中的位置,作家位置的獲得既被作家的現實處境所決定,更是作家主觀心理的自覺選擇。在王躍文那裡,他努力去尋找并企圖去貼近曆史的中間物,在善與惡、是與非、美麗與醜陋、崇高與卑下、真誠與虛僞、熱情與冷漠、聰明與狡詐、沉淪與救贖……中建構一種不對稱的對稱,不平衡的平衡,進而開拓出較廣闊的灰色地帶,讓世情與人性在撲面的風沙中去接受來自于生命的質詢與考驗,最終構成王躍文作品獨有的“真”。
“真”在王躍文所有論及創作的文字中反複出現,并在《喊山應》中做了更深入的發揮,他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學就是一種承擔,應該呈現一種真實的東西,或者說是真理,不管以什麼形式來呈現。我認為哪怕是最離奇的幻想,也必然是來源于現實,呈現出真實”。在此基礎上王躍文差別了生活之真與文本之真。前者指的是人物、具象以及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它是一連串豐滿細節的組成。後者的意義趨于抽象,與想象、人性、生命本質、無形的關系等相關。兩者共同指向人類的已然與應然,指向對生活無限可能性的尋求,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說“小說是存在的勘探者”,勘探的工具就是此“真”。
不過在《喊山應》裡,王躍文将“真”與自然主義差別開來,賦予其适當的虛構性質,他寫道:“不必把生活的真實全部示之于人,生活中的某些人壞得吓人,但寫小說卻大可不必弄得那麼吓人,凡事留有餘地好些,我們隻把真實的事件當模特兒,然後加入些藝術成分弄得含蓄些”,在他這裡,“真”是有度的,需要節制和裁剪。這似乎違背傳統現實主義的典型塑造論,也與現代以來中西方借助于荒誕、扭曲等各種手法去深描生活的小說形式變革分道揚镳。那麼為什麼會是這樣一種“真”呢?這自然跟前面提到的王躍文創作中的距離(時間)美學有關。因為有限度的真實和帶節制的叙述最終昭示的是事物的中間狀态,含而不露,隐而不彰,處在曆史與現實的中間項上,呈現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之間的距離,讓作家和讀者同時獲得一種曆史感或時間感。但這不是王躍文的最終目的,他要做的是想以這種有意收斂的“真”去抵達人性的最幽秘處,表達他對人性的了解,而這種了解自然也是充滿中間性的。
王躍文說:“我筆下沒有絕對的黑色人物,也沒有絕對的紅色人物,大多人物處于灰色狀态。有些人物是灰色偏于白色,這已經是讀者感覺中的正面形象,比如朱懷鏡和關隐達。有些人物是灰色和灰黑色,比如孟維周和張兆林,他們都是現實中很真實的人物,人性裡本來就有許多灰黑色的東西,隻是平日裡沒有給予亮相的機會和條件”,這種人性觀已超越了簡單的道德審美意義。在《喊山應》中,作者非常細緻地描述了創作《大清相國》的過程,對康熙和陳廷敬的個性做了諸多說明和史料印證,這在一般的作家創作回憶錄中很少見。其良苦用心還是在于表明作家自身的道德态度與倫理立場,即不願意輕易對人和人性做出價值評判,好人或是壞人,清官、貪官或是庸官,在人置身的錯綜複雜的社會關系中,本不隻是單一的角色,何況還有私欲這種主導性的力量。如《桂爺》中的桂爺,一輩子活得硬氣,不麻煩人不貪便宜,老年卻病倒在床要人服侍,并在與四喜的五保戶之争中,因暗地裡盼望四喜在他之前死去最終羞愧自殺。然而王躍文倫理道德立場的中間性并不意味着他忽視和接納了惡,恰恰相反,他對人性的黑暗處與世事的荒唐處洞若觀火,“不能閉目塞聽,有時難免嗔目發指”“我對中國文化中的醜惡是絕不認同的”,在《喊山應》中,他再度表達了對惡和惡趣味的拒絕。是以王躍文在倫理道德态度上的節制展現的是他對個體生命悲劇性的同情與悲憫,也是以作者反複強調自己的作品“态度是批判,底色是溫暖”,他無法接受張愛玲《小團圓》中那種陰冷的調子。
隻有了解了王躍文的“真”和後面的倫理道德立場,我們才能真正懂得為什麼在他的作品中主人公一面在不斷地向現實妥協,一面又在不斷地進行道德檢討,最終與自己、與他人實作了各種形式的和解,走向了倫理意義的回歸,《梅次故事》《蒼黃》《朝夕之間》《亡魂鳥》《冬日美麗》《愛曆元年》等皆如是。雖然也許有人質疑這種和解的可能性與有效性,但對王躍文來說,“我在作品中想做的,隻是用我這盞燈,照亮我所了解的這一小塊地方,燭照這一小塊真實,提問思考,僅此而已”,“以真實來發問,而不是以真實來給出答案”,他是沒有野心的。沒有野心也符合這充滿相對性的世界,昆德拉說:“在小說的相對性世界中沒有仇恨的位子”,因為“在這巨大的相對性的狂歡節中,沒有人有理,也沒有人完全無理”,是以王躍文的“真”是為這個動蕩沖突的世界做的一個小小的注腳,一個作家搖頭看書,熱眼觀世,去探索人們行動的意義以及他們所處環境的意義就已經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