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穎緩慢意識到自己對技術的依賴,如同溫水裡煮的那隻青蛙。
兒時,她喜歡記路和公交路線圖:老家的九路車開往老城區,穿過童年的遊樂場;八路車開往縣城,一路上塵土飛揚,運輸動物的卡車往返于城縣之間……
但現在,“任何時候隻要輸入起點和終點,我就不用再動腦了。”同時,她曾經敏銳的方向感正逐漸退化。
丢失實體坐标僅僅是開始。在2021年建立的“反技術依賴”豆瓣小組内,成員有兩萬餘人,他們擁抱技術帶來的便利,也不同程度地遭遇着“技進人退”:難以集中注意力、沒有真實可感的社交、大面積精神焦慮、被算法精準投喂商品、被同質化的資訊裹挾等。
他們正付諸行動,有人實體隔絕,把手機鎖進可以定時的盒子、打卡放下手機30天;有人用老技術制造“不便”,換成老年機、水墨屏;有人關掉了推送、朋友圈以及個性化推薦功能;還有人依然在苦苦探尋自己依賴技術的成因究竟是什麼。
讓技術退回工具的位置,是多位受訪者的共同心願。那回到美好故事的最初,那些技術給他們帶來的自由與快感是鏡花水月嗎,他們後來如何淪陷,又如何抵禦與反思技術對生活的入侵?
“很多人像是活在了手機裡”
“我好像處于一個四面都圍攏的地方,好像這個世界隻有我一個人。所有的連接配接都是從線上來的,我見不到那個人真實的樣子。”27歲的王雁北目前在上海居家辦公,她也隻消維護那一塊螢幕裡的形象,開視訊會前“換一個上身(衣服),妝也不想化,戴口罩畫個眉毛”。
用了一天電子裝置,她眼睛很疼,覺得困倦,但晚上躺到床上精神又很足,“為什麼我睡不着呢?”她很困惑。
在此之前,王雁北嘗試用多曬太陽、增加運動量的方式緩解睡眠問題,卻難免失眠。通過複盤自己一天天都做了什麼,她發現一個問題,“我怎麼随時都在看手機,做瑜伽(間歇)也在看手機?”
王雁北還對手機遊戲上瘾。機關上班時,有次遇到項目壓力大,她專門跑到衛生間裡玩了一局,玩完愧疚感襲來。居家辦公時,周圍無人監督,一個人處理繁重事務感到焦慮,她心想:這怎麼這麼難啊,去玩一局再回來寫吧。處理壓力的方式仿佛隻剩下了遊戲,“如果不玩我不知道這事怎麼辦,不想去查一些新的資料。”
她這才意識到,手機已經讓她的生活變得繁重、失序。
在北京一家周刊做記者的楊璐沒有手機成瘾,但她的難處在于手機時常“甩不掉”。
記者的工作需要她大量浏覽社交平台上最新的熱點、觀察大衆的反應。“從微網誌看到公衆号,自媒體,在差不多的話題上反反複複提,角度都差不多。”楊璐覺得有些苦惱,“好占用時間。”
寫稿時有人發消息來會打亂工作程序,為此她常給手機調靜音,任務完成再檢視。但她知道,商業公司裡的很多采訪對象經常一個人有十幾個工作群,接連不斷地被艾特,“他們相較于我而言,才是完全沒有時間。”
前一陣,她因出差采訪去到一處有名的石窟。那天下了小雨,空氣濕漉漉的,出行的遊客不多。走在石窟之中,她感覺自己正身處一個安靜的時空。
沿路往前走,她看到身邊的遊客少有人欣賞風景,紛紛下意識地舉起手機記錄眼前的畫面。楊璐開始覺得奇怪,“大家都在拍照,拍石窟,互相給對方拍照。可是網上專業的照片很多啊,都能看到,但你在當下氛圍中的體驗感隻能是本人到場所獲得的。”
“很多人像是活在了手機裡。”楊璐說。
相似的場面,宋宇幾個月前也碰到過。北京的冬夜,十點,一輛公共汽車穿梭在街頭,載着八名疲憊晚歸的乘客。窗外的夜色混沌,醫學博士在讀的宋宇擡頭看了看車内的情況,“那時我發現,除了我以外的7個人都埋頭刷着眼前的小小螢幕。”像是工廠流水線工作的勞工,沒有人下統一的指令,但每個人的動作驚人趨同,“不知道為什麼,我那時候覺得大家好像都被控制了一樣。”
下車前,宋宇注意到一位年紀比她大的女士脖子向前伸,不斷地在刷抖音視訊,一個接一個,似無止息。
“我們的社交軟體沒有‘底線’”
關蕊的記憶裡,以前的網頁是有“底線”的,即浏覽完目前頁需要點選下一頁,“給使用者精神和心理上的休息思考時間。”而現在“社交軟體沒有‘底線’”,“你一直滑它就會一直出現”,永無盡頭。
最誇張的一天,關蕊發現自己的螢幕使用時間長達13個小時,那就意味着,她除了睡覺都捧着手機。她隻身在英國讀碩士,生病或者學業壓力大的時候,看手機頻率非常高,但長時間的使用讓她感覺“被壓垮”。
無窮的資訊把人網住,綿密的算法勾勒出人的行為畫像,精準誘惑着人的注意力,人們想要逃離或抵禦并非易事。
華為消費者管理教育訓練生許柯發現市面上免費連wifi的軟體都會給使用者推送小視訊,他覺得這背離了人本身使用App的需求,将使用者強行和軟體綁定增加浏覽時長。
據他觀察,在傳統商學院的教學裡,産品設計往往以使用者需求為開始,以獲得利潤為目的,很多商學院的課程不讨論商業倫理。“使用者的注意力和時間就是經濟效益,軟體永遠有新的刺激點吸引你停留在其中。”
一個顯見的例子是,每一次在微信朋友圈給朋友點贊,就會收到接連不斷的共同好友點贊、評論資訊,那些紅色數字标記反複提醒使用者前去檢視。在廣州一家航空公司工作3年的李醒讨厭這個設計,“技術層面是想讓人更多地點進朋友圈,增加你的點選次數後進一步加強你的肌肉記憶。”
關蕊看過紀錄片《監視資本主義》,有一句話她印象深刻,“如果你沒有花錢買産品,那你就是被出售的産品。”片中,一些從美國網際網路公司離開的員工,抨擊看似免費的社交平台将使用者的大資料販賣給廣告商,而廣告商也樂于“購買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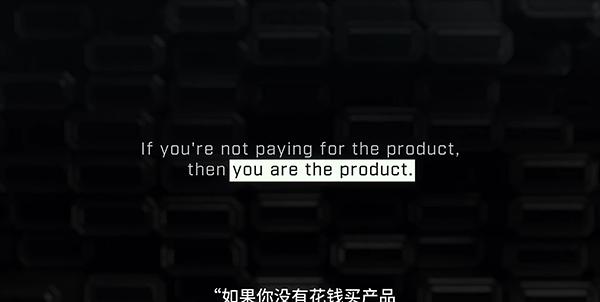
圖源:紀錄片《監視資本主義》(Social Dilemma)
2021年,UP主“老師好我叫何同學”問卷統計了5289名使用者使用手機的時間,每日平均8小時4分鐘,基本等同于在手機裡上了一天班。
論文《數字媒介技術依賴的多學科析因及整合性闡釋》中談到媒介技術的成瘾機制:媒介技術呈現的新異刺激會誘導多巴胺釋放并激活獎賞系統,進而使使用者大腦神經中樞系統保持興奮……不斷延長使用時間。
“一睜眼就需要手機提供的多巴胺”
王雁北專門去查了論文,說手機的藍光會影響人的褪黑素(促進睡眠的激素)分泌,增加人的警覺度。她聯想到自己整天抱着手機,“一直想各種各樣的東西,特别嗨,一嗨就睡不着。”
論文中,“影響視力”、“眼部疲勞”、“失眠”這些冷冰冰的研究結論對應着她現實生活中的狀态,讓她想要卸下過度依賴帶來的沉重負擔。
她有意識地給手機和ipad定時關機,通過寫日記回顧自己一天做了些什麼。她發現自己查資料時容易被網頁其他内容吸引,有一次專門記錄了查資料和無所事事浏覽的實際用時。前者半小時,後者兩小時——螢幕上的資料讓王雁北有所警惕,開始限制自己對App的使用時長。
她給ipad裡的軟體設定停用時間,10-19點打開ipad,應用會變成灰色,點開顯示“今日使用已到限額”。她想通過減少電子裝置依賴一點點奪回對生活、睡眠的掌控力。
在做“拯救睡眠”主題的報道時,楊璐采訪了不少睡眠臨床醫學的醫生,了解到過度使用智能手機會與焦慮和失眠相關聯(伊利諾伊大學研究發現,頻繁使用技術産品患上焦慮和抑郁的風險更大),她更關注自己的手機使用時長了。
楊璐早年讀過《淺薄,網際網路如何毒化了我們的大腦》,書中提到網際網路的推送與呈現方式會分散人的注意力,人的大腦長期養成碎片接收資訊的模式,有意識地思維中斷,之後想要深度思考也會困難。這些年來,她觀察到身邊很多人時刻抱着手機,或頻繁掏出手機浏覽,與書中的内容呼應。楊璐是以把智能手機看成“吸收智力和注意力的黑洞”。
朋友在聊天中和她提及Kitchen Safe(用來鎖手機的盒子),還沒把這事介紹完,楊璐就從淘寶上搜了一家海淘店,下單買了一個。
Kitchen Safe很快寄到了。它最貴的地方是盒蓋,上面有個圓形大按鈕,旋轉它的時候,顯示屏上就告訴使用者上鎖的時間,調好後往下一按,盒子就鎖上了。在美國,有消費者用這個盒子戒甜食、戒酒、戒除藥物依賴。晚上11點,楊璐把手機扔進盒子裡,設定上鎖10小時,按下按鈕,立刻就覺得内心安甯了。
Kitchen Safe 網絡圖
宋宇覺得手機會讓自己“脆弱”、被同質化的資訊包圍,“你的思考模式是在資訊的裹挾下趨同的,而非自發趨同。”
她直接在豆瓣“反技術依賴”小組裡開了一個“不玩手機30天”的記錄貼。開始的三天内,起床後、上廁所時,宋宇都有強烈的刷手機欲望,“多可怕以及多奇怪啊,在每天一睜眼的時候,我就需要手機提供的多巴胺。”
她喝着咖啡,想起剛看到的多肉植物,迫不及待要打開淘寶購買花盆、多肉和土。她轉念一想:可以用家裡廢棄的杯子,樓下花壇的一點土,以及室友多肉掉下來的葉子。想到這兒,她伸出去的手停下來了。
每天多出了四五個小時,從小螢幕前抽身的宋宇發現——家裡沙發已經堆滿衣服了,很多東西閑置可以賣掉……“那是我第一次,着手審視我的家,并開始動手改造、營造一個我想要的生活。”
宋宇收拾好的沙發
三十天裡,宋宇将每日的手機使用時長控制在了半小時左右。她有塊蘋果表,用來看時間和接電話,早中晚各三次檢視微信回複消息。
她所在的豆瓣小組有不少人像她一樣實踐打卡:跨專業考研的黎冉嘗試用卡頓的水墨屏手機減少自己的沉迷;關蕊買了一部諾基亞過上極簡電子生活;許柯使用軟體前,會将其中涉及個性化推薦的功能關掉,“我很害怕它隻給我推薦我喜歡看的。”
關蕊的諾基亞手機
“适度反連接配接”與社交平台減負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彭蘭在論文中寫道,當今人們面臨着過度連接配接的重負,例如強互動下的倦怠與壓迫感、圈層化對個體的限制及對社會的割裂、線上過度連接配接對線下連接配接的擠占、人與内容過度連接配接的重壓、對“外存”的過度依賴等。過度連接配接的背景下,适度的反連接配接或許将成為網際網路的一種新法則。
去年11月,李醒關閉了朋友圈入口,作出這個決定有多方面的考量。
之前他經常會點進朋友圈,肌肉記憶般手指向下滑動重新整理;更新狀态後十分期待有沒有更多的人給自己點贊、互動,“我并不喜歡這種心理狀态。”出于工作原因,兩三年内,他的微信好友數從300漲到了1000,但是其中大部分的朋友僅是工作關系,現實中不熟,這讓他釋出朋友圈前對内容有些遲疑。
在徹底關閉前,他也做過幾次同樣的嘗試,逐漸發現自己對朋友圈的内容關注度下降了。他看重内容帶來的資訊增量,但是朋友圈裡的每一條動态,自己真的要“事事關心”嗎?
關閉後他在一檔播客的早間新聞節目中聽說了EDG獲勝的消息,當時他慶幸自己關了朋友圈,“看朋友圈刷屏的感覺一點都不好。我本身不關心這事,精力和注意力又有限,不想在朋友圈刷屏的時候被動地注意力分散。”
他将更多的在意放在自己的親人好友身上,偶爾會點進好友首頁關心近況。“我的朋友也知道我不怎麼用朋友圈,減少網絡社互動動不會影響我們現實中的關系。”他自己想要分享動态時,會先設定私密,三天後“解封”,避免實時頻繁互動,但同時也有記錄作用,朋友想要了解能夠看到。
“如果你的現實社交很充實,你可能也不那麼在意多少人給你點贊評論了。”李醒說。
黎冉上大學的時候曾經熱衷于網絡社交,用網絡流行語來說是“營造人設”。每每釋出朋友圈,要思考文案怎麼寫,圖檔怎麼拍好看,誰可見誰不可見,這些附加的事項混入了她最初的快樂分享狀态。分享完後,她會在意朋友的互動點贊,一整個流程下來,感覺有些“内耗”。
專門研究了傳播理論,黎冉覺得“朋友圈像一個流動的舞台,你不清楚你的閱聽人是誰,是以你經常會想做一個面面俱到的人,可是沒有人真的可以做到。”在網絡虛拟光環的籠罩下,人們像是戴上了面具,有些丢失真實的自我和實體的社交。
黎冉覺得長期被社交平台的資訊流喂食,會喪失自己自由選擇和專注的心流能力。備考期間,她删除了以往關注的公衆号,隻留下備考相關号。“我們研友之間也會互相交流,不會遺漏重要資訊的。”
“人到底是需要資訊還是需要空白,我目前覺得人更需要空白。”經曆了30天計劃,宋宇這麼想。
她在進行醫學博士的攻讀,希望自己在醫學以及寫作、金融、運動領域深耕,而非将注意力鋪滿。她了解時下風靡的比如冰雪運動、漢服都是積極文化,但從商品屬性來說,那也是一種“被創造的需求”。她會先區分内驅的興趣和外界的灌輸。
網絡上的碎片化資訊十分冗雜,宋宇覺得它們不如書籍中經過時間檢驗的理論内容那樣可靠,“而且,一個錯誤的觀點帶給人的傷害,高于正确的觀點帶給人的收益。”她喜歡30天計劃後更清淨的資訊環境和更充裕的時間,如果自己的大腦被有用無用資訊都填充了,“我會沒法自由。”
“在局部戰場取得勝利”
即便左穎選擇更“在地”的生活,也很難做一個全然脫離技術依賴的個體。臨近畢業季,帶着資訊焦慮浏覽招聘資訊、公司就職體驗時,左穎會被網頁推送的公司内部八卦吸引,看得津津有味,看完又懊悔浪費了時間;她在生活的省會城市裡帶着現金去購物常常無法獲得找零,最後還是改用移動支付。
“但在城中村、三線城市及更小的地方,現金使用率尚可,存在很多交談的空間,哪怕是講價。”左穎形容下,和手機相處“就像是一個掰手腕的過程。有時候掰不過隻好認輸,但在某些局部小戰場我還是可以獲得小勝利的。”
許柯在反依賴嘗試中也有過來回拉扯,在他的比喻中,那個過程就像“聰明的蜘蛛織出一張結實的網友善前行,行為卻又永遠困在了這張網上”。
大三時他做過一周“無智能裝置+使用現金”實踐,好處在于“解放了時間和注意力”。當時他列印了兩篇在知乎資料庫裡收藏已久卻沒有仔細閱讀過的文章,反複閱讀後收獲良多,記憶猶新。
他把此前在智能裝置裡“收藏”好文章的習慣打了個比方,“我像一個漁夫……打上的魚炖了吃兩口放進冰箱趕緊重回海邊,生怕錯過打撈下一條魚的機會……可是這片海的魚實在太多了,打魚也是有成本的。”
許柯記得,《社會心理學》裡講過多的選擇造成人的滿意度下降。在離開智能裝置的一周裡,至少他的選擇變少了,心情“簡單和舒暢了不少”。
難辦的在于:他用現金支付,平日網購2分鐘能買到的電影票,線下選座購買要花10分鐘,享受不了優惠。期末前的課堂,大家拿着平闆對電子資料圈圈畫畫一邊搜尋,他隻能拿着一本書咬文嚼字。現代生活、聯絡深度依賴智能裝置,他每晚“特赦”自己用手機處理社團資訊對接、同學交流的相關事項。
一周體驗結束,他拾起智能裝置借助網際網路學習、補充筆記。于他而言,技術改善生活、提供便利的部分不需要被強制舍棄,他在日記本上寫下,“無論網絡還是生活,要找到自己的節奏。”這是他實驗後更大的收獲。
許柯的日記
黎冉也是這樣想的,她認為技術一體兩面、利弊各半,“沒必要非得做一個生活家,什麼都不用,住在山頂上。”在她抵抗“手機沉迷”的過程中,會借助辦公效率App,用能改善人生活的技術抵抗讓人沉迷的技術。
“進入生活”
嘗試戒除數字依賴後,王雁北空出了時間推門外出,感覺所有的感官都被調動起來了,“進入生活讓我看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東西。”
她家附近有梧桐樹,慢慢散步,她聽到車開過馬路的馬達聲、風吹拂樹葉的“沙沙”聲、上海的爺爺奶奶在交談。中間的小道會很安靜,仔細觀察能看到周圍人各異的狀态。購物時,她和進出口折扣店的老闆、菜攤老闆愉快地聊天。
她嘗試走了一條以前沒走過的街,沿途看着一幢幢特色建築的介紹,感受到“原來這個地方以前曾經有過這些人、這些事情”。
左穎也會有意識地與住宅附近的餐飲店、電器維修店、廢品資源回收筒人員接觸交談,和一家零食雜貨店的老闆成了熟人。有時需要購買商品她會直接給老闆打電話,老闆轉行後還幫着周邊老客戶低價進一些生活物資。“我覺得這樣的購物形式更有溫度有人情味。”她說。
做攜帶諾基亞實驗的關蕊如今将手機使用日時長控制在了2小時内,留下了更多時間進行深度閱讀。楊璐和同僚一起寫下了“網際網路消失的40件事”,例如問路、CD光牒、放空、耐心、長相真實的照片,紀念這些正在消隐的美好。在廣州的李醒發現看紙質地圖能讓自己在腦海中“點亮城市中的地理坐标”,地方與地方之間有了聯系,不再是數字中的一個個端點。
放下手機30天,宋宇覺得“内心更輕松了”。
為了改掉睡前睡醒下意識刷電子裝置的習慣,宋宇把手機放在了家裡的進門處充電,不帶進卧室。相替代地,她放了一本書在床頭,晚上習慣性地翻幾頁。
她以前常打網約車、訂外賣,實施計劃中,她選擇乘公共汽車,自己做飯或者吃食堂,一個月省下了3000元。一些外賣軟體會在飯點提醒使用者可以點餐了,宋宇覺得,“有些需求可以被替代,或者本來不存在。”
去年的平安夜,她邀請朋友來家吃火鍋。她喜歡這種面對面的交流,線下近距離的分享,“網絡社交無法替代現實社交,網絡上你可以遲疑回複,現實生活中的交流需要察言觀色,人們的反應都是即時的。”
在去實驗室路上,她單純地走路而非将目光時刻聚焦在手機上。她更加關注頭頂的天空、沿途的風景、周邊一顆顆長得茂盛的樹,那種感覺像是兒時熟悉的時光,需要自己尋找樂趣度過空白時間。她撿了一些樹枝回家插在瓶子裡,在家裡種菜種花,“我真的在玩,不是在手機上玩。”
宋宇種的花
“其實我覺得藥物和技術之間是有些相似的。”宋宇讀博前在一家醫院工作過一年,她舉例道,如高血壓藥物更多緩解症狀、調節血壓,而非治療根本。
她覺得技術也是類似。人們借遊戲逃離現實生活,通過看短視訊轉移注意力,試圖用技術緩解焦慮或不确定感。“但技術很多時候可能治标不治本,它并非有何動力讓我們開心,我們的開心還是需要自己去獲得的,是一個主動的東西。”
在“不玩手機30天”計劃的末尾,宋宇在文章中寫下:“我和手機的關系:它是我的工具,但它不是我人生的全部。”
(應受訪者要求,王雁北、宋宇、黎冉、關蕊、許柯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