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親情的疏離與交融
——關于弋舟短篇《瀑布守門人》
文丨王春林
我的摯友,優秀的70後小說家,曾經被我谑稱為“西毒”的弋舟,這些年來一直緻力于短篇小說這一文體的精心鍛造,成績斐然。依照他的自述,他這一次《瀑布守門人》(載《收獲》雜志2022年第1期)的寫作,與另一位同為70後小說家的田耳緊密相關。那是在2021年的5月份,弋舟、田耳、黃德海他們三位相聚在遙遠的海口,黃德海建議,他們三位分别以對方的舊作名為題,各寫一篇新的小說。具體來說,就是弋舟寫田耳的,田耳寫德海的,德海寫弋舟的。在當時,弋舟主動認領的,就是田耳的《瀑布守門人》。田耳的同名短篇小說,不僅發表在很有影響的《作家》雜志,而且也還登上過2020年的收獲文學排行榜。這一次,弋舟之是以要給自己的短篇小說專門加上副标題“本文緻敬老田”,這個老田不是别人,正是田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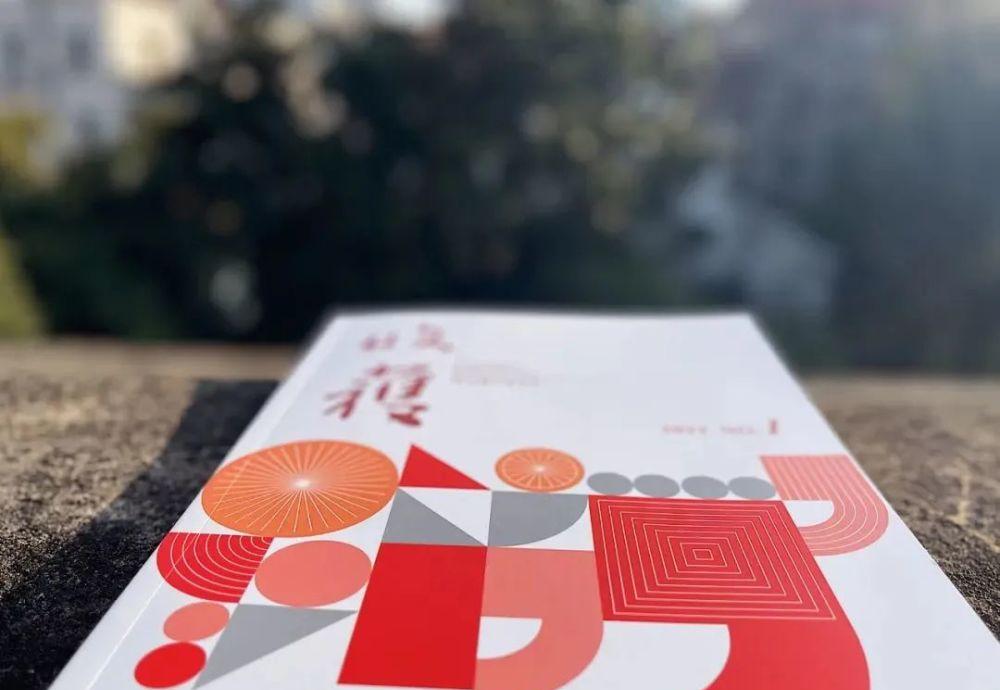
弋舟短篇《瀑布守門人》刊載于2022-1《收獲》
除此之外,弋舟這個短篇小說的寫作,也還與《小說月報》雜志組織的一個《麗江故事集》的寫作計劃有關。故事之是以一定要發生在麗江,乃因為寫作計劃要求寫出的作品必須包含“有麗江元素”。由以上可見,弋舟《瀑布守門人》的寫作,其實帶有某種“命題作文”的性質,雖然說這樣的一種“命題”,無論如何都不可能限制影響弋舟才情的發揮。不管怎麼說,這一篇《瀑布守門人》,也都是弋舟認真細緻地打量思考現實生活,了解認識生命親情的一種必然結果。
同樣應該引起我們關注的,是貌似充分地展現了弋舟寫作随機性的小說開頭:“當我寫下‘在麗江古城一家略顯冷清——其實就是寒碜——的客棧,我見到了郭老師’這個開頭的時候,我還沒有确定‘郭老師’的性别;直到寫出‘郭老師說客棧的男主人來自玉門油田,算是與她有着鄉誼’,‘她’才出現了,令郭老師成為了一名女性;我要承認,這麼寫過一千五百字之後,我終于決定,讓小說裡的‘我’,與‘郭老師’成為一對母女。”
如果我們相信弋舟表述的真實性(他其實也完全沒有必要在創作談裡和我們玩兒什麼障眼法),那麼,《瀑布守門人》的寫作,确實有着相當突出的随機性。然而,也正如同弋舟自己所明确意識到的那樣,當他寫完小說開頭部分的一千五百字的時候,他的寫作自由,寫作随機性,也就随之而縮小了許多。到這裡,開始在不期然間發生作用的,就是随機性的反面,也即寫作的規定性了。無論如何,小說寫作都有着隻合乎人性邏輯和藝術邏輯,不以作者的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寫作規定性。
事實上,首先值得注意的,正是第一人稱叙述者“我”和郭老師之間頗為令人稱奇的不正常母女關系。讓我們來看她們倆在麗江客棧見面時的情形:“昨天黃昏卻是另一番情形。我出現在客棧門口時,她是飛奔着從三樓沖下來的。她在憑欄眺望,等待着我的到來。就在我們擁抱前的一瞬,她克制住了自己,隻是好像有些不情願似地跟我淺擁了一下。”不止如此,一直到“我”和郭老師出場之後好久,我們才搞清楚,卻原來,“我”和郭老師,竟然是母女關系。明明是自己的母親,但“我”卻一直口口聲聲地把她叫做“郭老師”。這樣的一種稱呼本身,再加上她們倆見面時一點親熱意味都顯示不出來的那個場景,所充分凸顯出的,正是她們之間一種生命親情的冷漠與疏離。
依照小說中的描寫,導緻她們母女倆彼此親情疏離的根本原因,或許是因為母親離異後相對混亂的男女關系:“我跟朋友們說,我的母親觀念非常開放,但僅限于說明她對我擇偶的态度,實際上,無法啟齒的是,她對自己的欲望也從不避諱。她幾乎沒有斷過異性伴侶,很早就把身體的需要與精神的需要分别看待了。”很大程度上,正因為離異後的郭老師身邊總有異性存在,是以,“我”才會在事後做如此一種檢討:“我忍不住竊笑,認為這是郭老師在借機聲讨我妨礙了她的幸福。是啊,至少有三個男人是被我從她身邊趕走的,一個女孩子對于圍在自己母親身邊的男人,殺伐決斷,會煥發出魔鬼一般的破壞力。”
唯其因為母女間親情的淡泊,是以,即使是“我”這次千裡迢迢地從西安飛到麗江的旅程,也是非常不情願的:“我的情緒不高。我奔波得很辛苦,從西安飛來麗江,不能算是一件輕松的事;還有,候機時接到的一個消息也令人不快——一位卧底的同僚告訴我,我在公司一個重要的考核中落敗了,上級部門的理由是:同樣的榮譽我已經得過三次了。”
與弋舟此前的小說大緻類似,出現在他筆端的家庭和婚姻,往往處于支離破碎的殘缺狀态。這篇《瀑布守門人》裡的“我”和郭老師母女倆的情形,也都同樣如此。出生于祁連山下的戈壁腹地,有着濃厚“玉門油田情結”的郭老師的中年離異,自不必說。身兼第一人稱叙述者功能的女兒“我”,也同樣處于離異後的單身狀态。正因為“我”一個人帶着兒子過活,是以,當“我”必須從西安飛赴麗江的時候,才必須首先把兒子安頓給前夫,而且還要憂心忡忡地懸心兒子到底能不能和前夫再婚後生下的那個名叫安貝的小女孩相處融洽。對了,作為小說标題的“瀑布守門人”,其實也和“我”的兒子有關。當“我”在登機前打電話給兒子,詢問他們在幹什麼的時候,兒子給出的回答,說是正在玩兒一個被叫做“瀑布守門人”的遊戲。雖然說一直到文本結束,作家都沒有告訴我們這個名叫“瀑布守門人”的遊戲到底是怎麼回事,但這一細節卻毫無疑問已經在暗中指向了小說行将結束時那個被臨時命名為“瀑布守門人”的客棧主人。
雖然從表面上看,郭老師不管不顧地把“我”緊急“征召”到麗江古城的理由,是因為自己的手機被搞丢,陷入到了舉步維艱的地步,但實際的情況卻并非如此。隻有等“我”急匆匆地趕到麗江之後,方才發現,母親真實的想法,先是要和“我”一起去泸沽湖邊看一場“壯觀得像漫天的瀑布”的流星雨,後來才徹底攤牌。卻原來,郭老師已經被診斷罹患了子宮癌。也隻有到這個時候,郭老師緊急征召“我”到麗江的真正意圖,其實是因為感覺到了生命短促的緣故。這樣一來,“我”這次看似有點無厘頭,有點不情不願的麗江之旅,實際上也就變成了一次帶有突出和解色彩的親情之旅。
正是在這次旅程中,“我”對家庭和自己有了新的了解與認識:“我也曾不斷地琢磨過這兩個人複合的可能性,當然,也不斷地否定掉了,直到最終再也不作此想。離婚後,父親也走馬燈一般地換着女人,最小的女朋友,年齡恐怕比我還要小一些。我的父親母親,這兩個都有着不懈激情的人,為了無可阻遏的自救的沖動,不惜挑戰既有的生活秩序。”“我是他們的女兒,是一個人間的事實和鐵律,以此宣示了責任和義務,甚或還有人倫和道德。于是,在漫長的成長中,他們的激情,就是我不得不與之激戰的敵人。但我不怨恨,至少如今不怨恨了。因為我也面對過自己的激情了,知道這激情,确乎也是自己與自己的憔悴的激戰。”毫無疑問,隻有自己親身也體驗過了,才可能真正地了解父親母親他們的根本心境。從這個角度來說,所謂設身處地,正可以被看作是“我”與母親郭老師,或者說弋舟與現實生活實作和解的一個基本前提。
無庸諱言,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對生活的了解和認識,有了與現實生活的和解,也才進一步有了“我”與客棧的主人,也即那位“瀑布守門人”之間的生命交融。由于“我”忘了關閉水龍頭,比在客棧内人為地制造了一個人工瀑布,而那個客棧的主人,也就成了“瀑布守門人”:“從我所在的位置看過去,他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瀑布守門人’。”接下來,就是他們倆在互相撩水嬉戲之後的彼此生命交融:“一切結束得飛快,我們都自覺地在和某種緊迫的事物競争。不,不完全是因為時間,也不完全是因為環境,是更為深層的、跌宕的情緒令我們深感時不我待。我從未像這般徹底地自由,大朵大朵紮染一般人造的白雲在我腦子裡争相怒放。天空倒垂,萬物都是平行的了。這是一場單純而極緻的遊戲,名字不妨就叫做‘瀑布守門人’。”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意識到,小說即将結尾處這一個“瀑布守門人”細節象征性意味的存在。在表現“我”與“瀑布守門人”生命交融的同時,它更是在一種象征的意義上,隐喻表現着郭老師和“我”母女倆之間的生命交融,或者說是弋舟與現實生活之間的一種和解。從這個角度來說,那個在小說結尾處出現的父親的形象,就的确令人充滿了對未來或者說對生命親情交融的一種期待。
《收獲》長篇小說2021冬卷
不管怎麼說,從若幹年前那個曾經引起過強烈反響的短篇小說《随園》,到現在我們所集中談論的《瀑布守門人》,弋舟的小說寫作的确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方面,就是由《随園》中作家與現實生活對峙式的緊張關系,而走向了《瀑布守門人》中與現實生活之間某種程度上的和解。既如此,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就是,對于弋舟的這種和解傾向,我們到底該怎麼看。在我個人的了解中,由和解這樣一個起點,弋舟的未來寫作或許存在着兩種可能。一種是走向對現實生活的粉飾,另一種,則是走向對生命存在更為開闊,也更為深邃的開掘與了解。當然,我所寄希望于摯友弋舟兄弟的,無論如何都隻能是後者。
【作者簡介】
王春林,1966年出生,山西文水人。《小說評論》主編。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西安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特聘教授。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第八、九屆茅盾文學獎評委,第五、六、七屆魯迅文學獎評委,中國小說排行榜評委,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曾先後在《文藝研究》《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南方文壇》《文藝争鳴》《當代文壇》《揚子江評論》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四百餘萬字。出版有個人專著及批評文集《話語、曆史與意識形态》《思想在人生邊上》《新世紀長篇小說研究》《多聲部的文學交響》《新世紀長篇小說風景》《新世紀長篇小說地圖》《賈平凹〈古爐〉論》《鄉村書寫與區域文學經驗》《不知天集》《中國當代文學現場(2013—2014)》《新世紀長篇小說觀察》《中國當代文學現場(2015一2016)》《文化人格與當代文學人物形象》《王蒙論》《文學對話錄》《中國當代文學現場(2017一2018)》《賈平凹長篇小說論》《新世紀長篇小說叙事經驗研究》等。曾先後獲得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第9、15屆優秀成果獎,山西新世紀文學獎,趙樹理文學獎,山西省人文社科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