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裡輝光向人間——評徐劍《天曉》
文丨李雲龍
《天曉》是重大題材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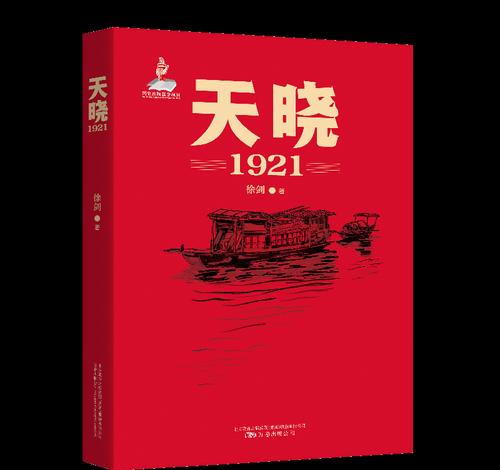
這種煙霞潤色的曆史成像,有顯而易見的好處,那就是筆墨未動,即可光焰鑒人。
不過對于作家而言,得天獨厚的此類條件不一定能夠帶來真正便利。緣其核心事實,家喻戶曉,時代更替,經緯萬端,各方期待,陡增壓力;該書主旨嚴肅,人物光譜參差,把握困難,拿捏不易;兼且年深日久,細節流失,河升月降,泥塵滲漉,其行止斟酌,負擔沉重。
不妨再作深入一點的考察——這原就關乎作家的書寫品性。
本來《天曉》涉及的時間線就荏苒百年,已覆寫無量的世情紛擾,而且把春秋改節、永夜悲歌,彙聚到了跨越幾個世紀的内陸場域——就算國族命運,由始到末,都沒能揮别哲學缺憾、擺脫宗教贅餘,甚至是以原初想定與終極拟态彼此沖突的方式,實作最出人意表的變遷——即便如此,它也沒能阻攔住九天驚雷的瞬間炸響。幅員遼闊而又曾四分五裂的華夏大地,由是遭遇了全向度的深刻沖擊,曾經異常沉寂的社會,也領略了廣度、密度均前所未見的變革。
就此而言,《天曉》的成書,理應毫無障礙。譬如“東方主義的想象”的先後形成及分别落地,全部涵括了文化景觀、思維模式、話語系統等豐富邏輯,譬如靈魂層面“熄滅天上的明燈”般那種“悲欣交集”的特殊照度,都強力影響着人的認知感受及其心理根基,闆塊斑斓,必是行文浪漫。
總之,曆史陳迹和當下現實,都“荒誕又莊嚴”地接續着重複映現,無不席卷以飓風、滌蕩以豪雨,而衆聲喧嘩之際,形從影随,背景宏大,人事物象俱全,作家居間排程,似乎易如反掌。
不過,如前所述,盡管相關條件看起來有利,卻是“最難将息”。
劉小楓出過一本品讀古希臘詩歌的著作,書名《昭告幽微》。他在其中講了和那位著名盜火者有關的一段話:“普羅米修斯為什麼被囚禁在這兒的荒涼岩石上——這次普羅米修斯的回答很簡潔:‘宙斯的意志、赫淮斯托斯出手’”。在《天曉》的語境下,徐劍當然不能被視為盜火者,但自他眼前排山倒海而來的,卻是海量資訊,不僅是“天地轉,光陰迫”,更是“多少事,從來急”,而且内裡摻雜無涯人迹,甚至還牽扯到精神信仰、價值導向等因素,情境甚為相若。
屏除意識警悟,單論寫作取舍,則徐劍處于這種局面之下,那些巨大繁蕪的一切,無一不是“宙斯的意志”和“赫淮斯托斯出手”,他要背負的,是剪截裁量的真正重壓,他獨對這樣的情形,就很難不讓人聯想起“被囚禁在荒涼岩石上”的普羅米修斯了。
由是觀之,重大題材和善加引導,決非如大家所想象的那樣、或如人們所習慣的那樣,隻要用大詞、用高聲,便一切安好。
真正的麻煩,在于易被所有可以或便宜收攏或辛勞獲得的材料湮沒。徐劍到底有沒有跌進這種海淵呢?值得鄭重告知于衆的是,面對相關問題,作家成功地找到了解決之道,展示了高超技巧。
徐劍的處理,給曆史題材書寫,提供了一個優質案例。
先是突破了慣常的全域實錄模式,并且輕靈地選擇了即景言事。采訪者立足目下,史筆卻集中到了早期的數天之内(例分八日),将當年風雲,濃縮在了非常微觀、非常具象的篇幅裡邊。這種着眼于前代舊物、過往遺痕又能兼顧政經紀元、吐故納新的叙事,對同類題材如何能寫得獨出機杼,實可稱為有益啟示。
它繞過了過于龐雜這類亂石堆和布雷區,抵達了自由曠放的境界。
關鍵是,徐劍在和莊嚴叙述相交纏的時、事坐标系中,悄悄地把多重隐性參數置入其内,不管是回眸,還是緬懷,是通過今人留言,還是借由史事冊頁,作家在并不是相當醒目的場合、也不是特别明亮的時段,把事功脈絡,片言居要地就說清了——為什麼發生,緣何會開頭細弱,後來猛烈,而且發生得那麼無法抗拒。徐劍講南陳北李,還帶出了其他的重要角色和事件,且形象鮮活、細節典型,還原真實,開啟了自淨程式。這種近乎超現實的寫作,或許注定要承擔某種切近凝視,但惟其如此,惟其不以嘩衆取寵樣貌,去塑造消逝風物、遠遁行者,并将之納入大衆視野,才是更值得肯定的。
《天曉》開篇的“路标”部分,有幾句話必須照錄:“我從南至北,追尋十三位中共一大參加者的生命遺痕,拜谒故居,走訪黨史專家,請教對敏感人物的臧否。”徐劍這裡所作交代,道出了他人物處理的密碼。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組織,任何寫作者都無法厘清所有時期的人事糾葛,哪怕這種糾葛僅及總量的萬分之一。但徐劍富有智慧地找準了突破口——“一大”的十三位參加者。找到了這些人物,也就意味着本書真正做到了舉重若輕。創始人,典型;日之未出,等天空放亮——“破曉”,和書名意象,合拍。
標明了人物,作家順帶的收獲,是類型區隔、角色結局、品格錨定——既有可對應的人性對照,還有信仰比較,并以之昭告後人:壯士勒石記功,烈士流芳千古,下士身敗名裂。
按拉裡·布魯克斯所言,“這就是人物”。
除此之外,《天曉》叙事,情感至深:“掩卷已是五更寒。我朝天一歎。”
這樣盡顯才情的語言表達,全書比比皆是:“我在浩瀚的史書中發現了光亮”、“一船明月一帆風”……。
輕輕放下《天曉》,心頭油然湧出:還原曆史,寫好真人,與文學同路,也一樣是“萬裡輝光向人間!”
作者系深圳大學當代創作與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