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個年輕女人和以菲利普·羅斯為原型的作家處于不對等的關系。在男作家建構的故事裡,女人機靈、乖巧、遵循于兼具父親與導師身份的作家的引導。女人想寫一個和自己經曆完全無關的故事,但老作家自信地說,你應該從自己的經曆入手,否則很可能會失敗。
而在女作家的小說中,她虛構出了一個和自己毫不相關的人。一個年輕的美國白人女性助理編輯,寫下一個關于美籍伊拉克裔男性經濟學家的故事。
在第一個故事裡,權威男作家與年輕女助理,是男性與女性、導師與學生、權力場域的強者與弱者之間的不對稱。
在第二個故事裡,伊拉克裔男性因出生在國際航班上,擁有美國國籍,他随父母在美國生活,言行舉止與一個“新美國人”别無二緻,但在伊拉克戰争的陰影下,他在英國海關被反複盤問,最終被拒絕入境。這是西方與中東、全球化秩序的中心與邊緣、不同膚色和族群人類之間的不對稱。
想象這兩個故事,被放在一本書裡,這本書不僅是作家之書,也是作家對于書寫話語權、寫作中心本位的微妙質問——這就是莉莎·哈利迪的處女作《不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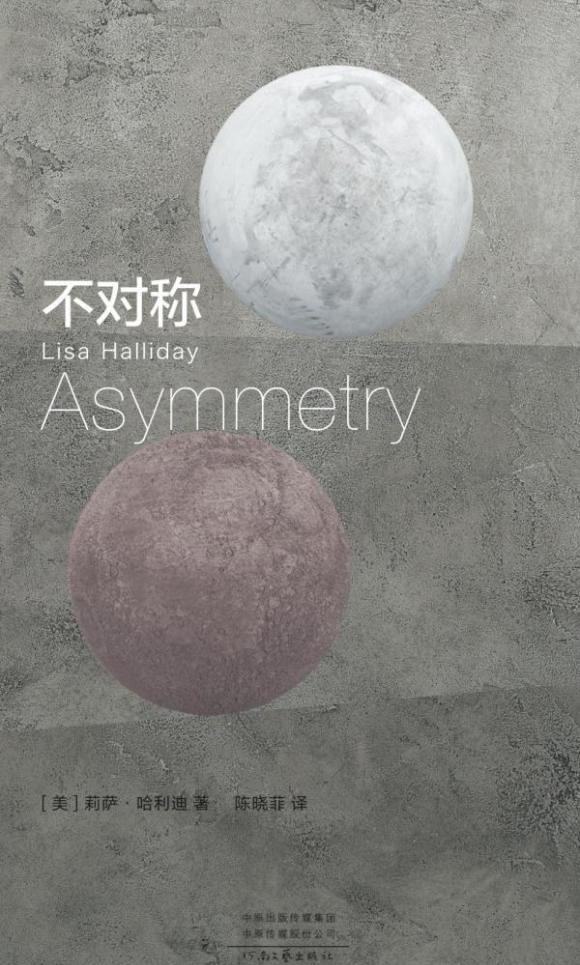
《不對稱》
2018年,這本書英文版的出版被美國人譽為一場“文學事件”。在第一部分故事裡,25歲的白人女助理編輯瑪麗·愛麗絲,在街頭被70歲的普利策獎得主、男作家埃茲拉·布雷澤搭讪,随後展開一段地下戀情。整個故事以冷靜的手法處理,我們對瑪麗的心理活動知之甚少,但處處可見埃茲拉的風趣、幽默、好色、自戀、衰老與對衰老的恐懼。這一部分故事,部分取材于哈利迪與羅斯的真實經曆,進行了大量藝術加工。《紐約時報》報道,哈利迪20多歲時曾在文學代理社擔任助理經紀人,與菲利普·羅斯相逢,并展開浪漫關系。有趣的是,哈利迪還給羅斯看過這本小說,羅斯回複:“這是一個不小的成功。”而哈利迪回應小說與現實的關系:“當然,愛麗絲生活的一些細節和我本人的有所重合,不過很多情節是小說虛構。菲利普最清楚,寫作就是這樣。”
時值Metoo運動,又是老作家與女文青的韻事,而羅斯當時承受着“厭女”的指控,羅斯自己寫過一部《垂死的肉身》,就曾以老少忘年戀為引子,闡述自己對于愛情、死亡、衰老、政治、宗教等問題的了解。讨厭羅斯的人斥責其為男作家自戀之書,贊美者則認為羅斯不僅在冷峻地剖析别人,也在解剖自己,他在一步步凝視一具衰老的肉身如何死去,對于性愛的渴望最終歸于生命的平靜。正如羅斯自己評論馬拉默德時的話語:“悲傷地記錄人類需求的互相沖突,需求遭到無情抗拒——也可以說是間接地減低——被封鎖的生命痛苦掙紮着,渴望所需要的光明、鼓舞和一點希望……”
《垂死的肉身》
《不對稱》可謂是對《垂死的肉身》的呼應和颠覆。此書一經出版就引發軒然大波,《紐約時報》将它列為年度十大圖書,《華盛頓郵報》稱其為“一場墜入兔子洞的未知之旅”,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将此書列入年度閱讀清單。
但這部小說也不乏争議。許多人認為它名不副實,社會意義大于文學意義,豆瓣也有短評認為,這部小說“也就比一般美國暢銷小說好一點”。
這本書到底成色如何?為什麼同樣一本書,會引起截然不同的閱讀感受?帶着這樣的好奇,我細讀了這一本《不對稱》。而當我讀到小說最後一部分時,耳邊萦繞着書中這一段對白:
“你在寫這個嗎?我們的事?”
“沒有。”
“那你在寫什麼?”
“其他的人。”
我們究竟能夠跨越出身、性别、族群、政治、國界的藩籬互相了解?這是《不對稱》真正想要探讨的問題,為了探讨這一問題,作者設計了一篇匿名紀實小說、一篇思想小說,以及一篇需要結合作者經曆和第三部分訪談來共同了解的元小說,三個文本互相串聯,構築了一個結構精巧的解謎遊戲。
這部小說分為三部分:愚蠢、瘋狂、埃茲拉·布萊澤的《荒島唱片》訪談。第一部分是老作家和年輕女助理的故事,作家的原型是菲利普·羅斯,女助理是第二部分小說的創作者。第一部分是用全知視角結合女助理愛麗絲的内傾視角講述的。叙事者不拖泥帶水,她在講述二人關系時主要用動作和對話,具有鏡頭切換感的場景處理,有些部分會讓人想起尤多拉·韋爾蒂、約翰·契弗或者雷蒙德·卡佛的處理手法。
莉莎·哈利迪的小說,最開始吸引我的是語感。知識分子忘年戀,很容易寫得油膩。文人那點陳皮爛谷子事,說多了膩味,尤其是男性知識分子寫的文人故事,如果變成“全世界女人都愛我”,或者“整個世界都虧欠我”,就容易落入落魄秀才小說的俗套。
莉莎·哈利迪
而哈利迪的文人故事不具有陳腐氣,她淡化了文人自戀的描述,取而代之的是冷靜、手術刀般的叙事口吻,如同清涼的夏夜附着在小說的肌膚上。
我很喜歡第一部分一些很有生活味的場景:
“星期六那天,下着雨。愛麗絲坐在衛生間的馬賽克瓷磚上,正努力地用黃油刀旋緊壞掉的馬桶座圈,這時電話響了:未知号碼。”
“她拿出自己的錢包:一隻磨損嚴重的棕色皮質男式錢包。一張刮刮卡,花一塊錢買的,面值也是一塊。一支潤唇膏。一把梳子一個鑰匙環。一個發夾。一支自動鉛筆。幾枚硬币。最後是三枚衛生棉條,被她攥在手心裡,像是三顆子彈。”
寫性愛很見一個作家的刀法,看一個作家寫性的部分,也是甄别優秀作家和平庸作家(此處村上春樹和賈平凹不服)的讨巧辦法。性愛可以有很多種寫法,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癫痫症、熱病發作的眩暈流寫法(從男女性事能引申出十頁哲學與宗教學思考),也有像普魯斯特這樣細水長流、宛如病中貴族在春夢中回憶舊事的粉色牡蛎流寫法,還有像喬伊斯寫日記那樣的泥石流寫法,但最要命的,是用一堆陳詞濫調來描寫一場自戀的性愛。而《不對稱》堪稱“事後流”,它寫性,但主要寫的是“性事以後”或者“性的中場休息”。
又一次,他們該做的都做了,并且沒把床弄亂。
隔着毛衣,他把手分别放在了兩隻乳房上,就像是在按她的靜音鍵。
“這隻大一點。”
“哦。”愛麗絲不太開心地低頭看了看。
“不不,這并不是什麼缺陷。世上不存在完美對稱物。”
“就像雪花?”愛麗絲試着舉例。
“就像雪花。”他很認同。
一道粉色的傷疤沿着他的胃往上一直延伸到胸骨,像一條拉鍊。另一道傷疤把他的腿從鼠蹊到腳踝等分成了兩截。還有兩個傷疤在他的屁股上方擺成了一個淡淡的抑揚符。這些還隻是正面的。
老作家和年輕白人女性的故事,很容易寫得輕浮、自戀,但《不對稱》處理得既不輕浮,也不淺薄,有一種剛剛好的分寸感,這種分寸感的基礎,在于作者莉莎·哈利迪嚴肅地對待筆下的人物,無論是老作家還是女編輯,她都沒有美化或醜化,而是給他們比對了适合的腔調。這部小說,意義是其次的,最迷人的是它的口吻,一種若即若離沉浸其中有一個抽身觀看自己的腔調。這一點其實讓我想到去年閱讀的《海邊的房間》。
在第一個故事裡,愛麗絲被埃茲拉發現自己在偷偷寫作,并敷衍說自己筆下的主人公隻是街上賣熱狗的穆斯林小販時,着急的讀者很容易忽略這樣的細節,可是記住的讀者,隻要讀到第二部分主人公的身份,就會恍然大悟,作家寫的根本不是陳詞濫調的老作家與小女生戀愛故事,而是借由嵌套小說的方式,來探讨兩個仿佛沒有答案,又始終困擾着我們的問題——
1、不對稱的人與人是否有可能真正做到互相了解?
2、當我們意識到世界上無處不在的不對稱,我們又該如何與不對稱共處,如何面對因意志力薄弱而産生的自我譴責傾向?
寫作是愛麗絲對埃茲拉的隐秘反抗。第二個故事是打在老作家觀念上的一記耳光,也是愛麗絲試圖證明——一個人有可能了解另一個人,哪怕是她完全陌生的人的處境。
然而,第二個故事的結尾,又讓這種了解走向一種更深的懸置——當形象宛如美國二代公民的伊拉克裔依然因為出身問題、膚色問題而被英國海關扣留,當巨大的不對稱,依然隐藏在全球化、普世價值溫情脈脈的話語裡,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倡導的包容、了解,又藏匿了多少無法消弭的血色暗痕?
這是一個暗流洶湧的文本。第一個文本有門羅的感覺,不緊不慢,隐藏機鋒,看似使女性形象單薄,其實藏了一個個小切口,留給敏感的人觀測那洶湧的暗河。第二個故事,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筆觸,是可見的好、謀篇布局的精巧,從角色設計到叙事推進,都透露出叙事者的野心。這是一個争奪叙事權的過程,是權威與挑戰者的暗中較勁。
埃茲拉與愛麗絲,他們這段關系的張力在于,他們不僅是權力關系、情感關系裡的對位者,也是老年與青年的互相對望。在接受采訪時,埃茲拉提到,自己和每一任對象相處,都像“養女兒”一樣,他的控制欲,隐藏在紳士的情話與甜蜜的教導裡。有趣的是,埃茲拉越告誡愛麗絲不要寫什麼,愛麗絲筆下的故事就越寫到。比如,他告誡愛麗絲不要讨論政治,不要寫自己不熟悉的人物,但第二個故事恰恰關于政治,恰恰是一個看起來愛麗絲不會感同身受的題材。
埃茲拉越是彰顯他的控制力、就越反襯他在年紀上的衰老、身體上的朽敗。他們的做愛很憂傷,哪怕是再有情調、再默契的吻合,都流淌着一種若即若離和憂傷的感覺。哪怕是再默契的兩個人,都有對方無法觀測的溝壑。
埃茲拉與愛麗絲的關系并不隻是占有與被占有,實際上,他們都在觀看彼此,都在凝視彼此的脆弱性。他們其實都愛自己勝過愛他人,承認自己的自私、敏感、僞裝、雙重标準,害怕被打擾,又盼望他人能把目光對準自己。他們是鏡子,是标本,是導師,也是觀測彼此不對稱的一個微縮膠囊。
他們都具有自我探索的特點,也都敏感于日常中看似普通又尖銳的細節。
比如愛麗絲:
有天晚上參加了一個派對,某個編輯的退休送别會,結束後她和一個版權部的助理睡了。他們确實用了安全套,但是它在該出來的時候卻留在了愛麗絲裡面沒能出來。……“它去哪兒了?”愛麗絲問,低頭看向兩人中間的幽暗峽谷。她的聲音聽起來稚氣又天真,仿佛這隻是一場魔術,而他随時會從她的耳朵裡變出一隻新鮮的套子。
然而,完成魔術的人是她自己——獨自在衛生間裡,一隻腳踩在新歡的馬桶座圈上,屏住呼吸。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勾起手指在濕滑腫脹的深處摸索。之後,盡管知道這樣并不能消除所有可怕的可能性,她還是躺進浴缸裡,用她能夠忍受的最燙的水灌洗自己。
而令我反複回味的,除了愛麗絲對自我的觀測,還有作者借由愛麗絲看的資訊,對于女性身體、女性生命曆程的觀測。那是一種被宏大曆史叙事所忽略,卻具體存在于每一個女性生命裡的——日常的磨損與暴力。
恰如書中提到諾貝爾獎對于凱爾泰斯·伊姆雷的授獎詞,說他“堅持書寫作為個體的脆弱經驗,以對抗曆史的野蠻與專橫。”
于是,小說特意花了一頁半篇幅,事無巨細描繪了女性移除胚胎的過程。而這是男性常會忽略的事情之一,男性與女性日常經驗的不對稱——對于痛苦感覺的不對稱、對于宏大與渺小界定的不對稱,乃至基于不同身份,所産生的文學書寫和曆史叙事的不對稱,加重了個體認知世界的偏見、撕裂,乃至自說自話的氛圍,但對于這種氛圍的破除,不是在于建立統一的觀念,而恰恰是回到對于“不同”的看見,對于“不對稱”的包容。
在其中,文學乃至整個人文領域所強調的“感受”“共情”,乃至“邏輯”“獨立思考”“批判和自省的能力”(很多人以為文學是感性,但藝術常常是感性和理性的結合),都是非常重要,但在公共讨論中日漸缺少的品質。
《不對稱》處處透露着小機巧,如果我們把封面設計也作為創作的一部分,那麼從《不對稱》的封面,到目錄,再到人物的叙事和角色轉換,其實都暗含着機巧的不對稱。例如在書的第三部分,埃茲拉接受采訪,認為把小說角色硬生生“楔進彼此的生活”太過刻意,不如讓他們道路平行,我們經由想象潛入他人的生活,超越“出身、特權、天真”,而在埃茲拉與愛麗絲實際相處時,他并未真正超越特權,也沒有真正了解愛麗絲對于書寫的渴望,而是渴望控制并塑造一個自己心目中的愛麗絲。
而在第一部分中擅離職守的阿馬爾·賈邁利,實際上也和第二部分的叙事者“阿馬爾”有着微妙的聯系。第二部分的一些自我解剖式的句子,未嘗不是指向第一部分的愛麗絲,甚至作者自己:
即便是那些靠想象維生的人也将永遠受困于一個終極的限制:她可以把鏡子照向任何一個標明的對象,以任意一個她喜歡的角度——她甚至可以把鏡子舉起來,不讓它照到自己,以便更好地去自戀化——但還是繞不開這樣一個事實:她總歸是舉着鏡子的那個人。而且你看不到鏡中的自己,可不代表别人也看不到你。
是以,這是一部充滿了小機巧的小說,作者運用了草蛇灰線的筆法,來描繪了我們周遭無處不在的不對稱,但最終,這本書更像一面鏡子,照見我們可能也不能完全确信的自己。
愛麗絲與埃茲拉的博弈,既是一個在文學上弑父與解放的過程,也是她在壓抑境地裡,摩擦出創造之火的證明。這種隐秘、禁忌、隐忍的關系不隻有壓抑,對她而言,其實還有一種暗暗較勁的滋味。是以,這是一本七繞八繞又始終陷于迷霧的小說,它對這一類人有一種擊中的誘惑,但是對于不喜歡這種風格,覺得作者的設計過于直白和野心畢露的讀者,他們從《不對稱》裡讀到的可能隻是厭倦和不适。
到頭來,這本書引起的回報也是不對稱的一部分。而我們所能做的,不是要對方接受自己,而是了解但不屈從于這差異而不對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