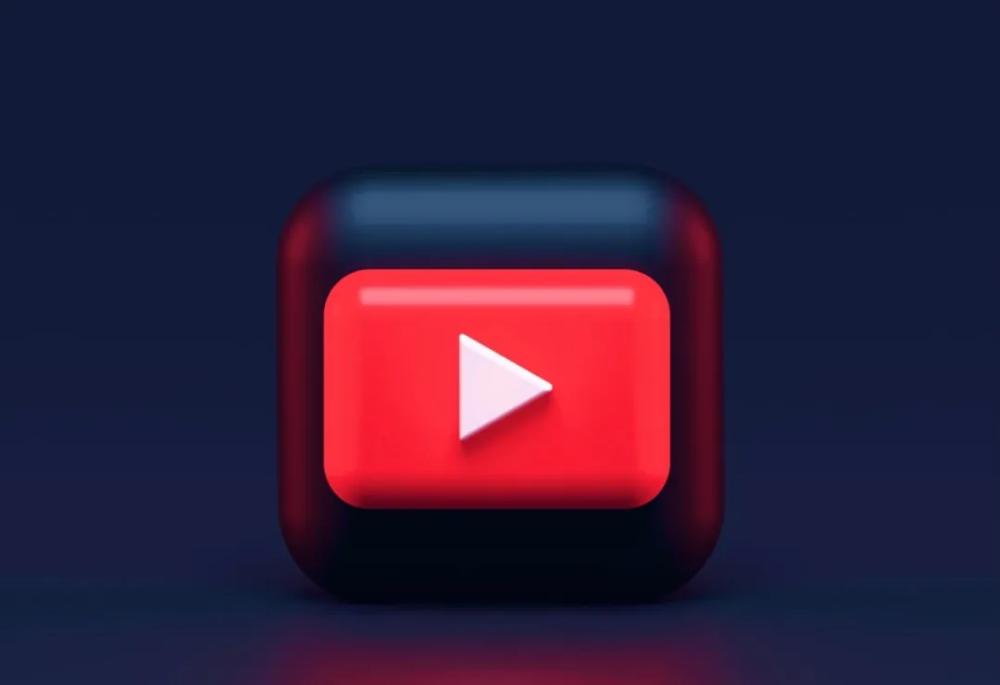
作者|呂玥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短視訊是典型的“網際網路流量”玩法,聚合短視訊内容,推薦比對給使用者,使用者無需付費,平台通過廣告的方式變現;而長視訊在經曆了免費燒錢時代的慘痛戰役後,目前歸于一種動态平衡,平台的會員付費、電影的單片付費都在試圖彌合内容與觀衆的距離,讓觀衆的錢直接給到内容,迫使内容從過去的“toB”賣給平台,轉變成更“科學” 的賣給使用者(D2C)。
如今,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商業模式有了又一次的交叉,「短視訊付費」來了。
一月底,微信視訊号上線了首個付費直播NBA正常賽,支付9元即可觀看全場。而這隻是一個開端,在2022年微信公開課上,微信官方也表示未來不排除會有中長視訊或短視訊的收費内容提供。快手、抖音也都推出了付費短劇内容,愛奇藝旗下的短視訊平台随刻去年還曾推出付費訂閱創作者“超級粉絲”的模式。
在海外,「短視訊付費」并不什麼新鮮事。YouTube早就有了“頻道會員”服務,使用者付費後便可以看到他們最喜歡的創作者的定制内容。而在近幾年,從Facebook(現為Meta)、Instagram到Twitter以及TikTok,也都開啟了這種付費訂閱功能。
不論國内國外、不論是短視訊平台還是包含短視訊内容的社交媒體,大家紛紛向使用者收費,但在「短視訊付費」為行業帶來新故事之前,仍有諸多尚未了解清楚的問題:
長視訊的付費模式都步履維艱,短視訊付費能跑通嗎?短視訊的付費設定點是怎樣的?又有怎樣内在的觸發付費的邏輯?短視訊付費和我們熟悉的知識付費、打賞投币一樣嗎?賽道的寬度是怎樣的?是大家作為補充,還是可以獨當一面?
怎麼付費?誰在付費?
和使用者給B站上的短視訊up主投币不同,投币、打賞均是“事後行為”,也就是使用者看完視訊之後,可選擇性的付費,是否付費、付費金額多少都是使用者決定的。而這裡所開啟的短視訊付費是“前置行為”。使用者需要先付費,才能看到完整的内容。
從内容上分類,目前主流短視訊平台以及社交平台上的短視訊付費,主要是知識内容和娛樂内容兩大塊。
2019年時,UGC創作的小成本電影和微短劇開始在短視訊平台上流行,同年快手便最先推出了付費觀看短劇的模式。抖音則是從去年年末才開始嘗試做短劇付費,與快手相似,抖音使用者可以按集數付費,也可以選擇一次性解鎖全劇。
左:快手付費短劇 右:抖音付費短劇《超級保安》
除了短劇,快手内其他付費視訊内容大多屬于泛知識類。與過去大衆熟悉的知識付費不同,這些需要付費的泛知識短視訊不一定是成套系統的課程,但卻類型相當多,包括職業技能、才藝、食譜、舞蹈教學,甚至是遊戲直播錄屏教程等等。在抖音同樣也有泛知識類付費視訊内容,但都是由創作者直接上架自己的小店進行銷售,直接走了電商路線。
愛奇藝旗下的短視訊平台随刻則是在去年推出了一個創新的付費模式“超級粉絲”。該模式和YouTube的“頻道會員”相似,是讓創作者建立起一個粉絲付費頻道,定制化地為粉絲提供更精緻的内容與互動增值服務。粉絲通過包月付費的方式觀看專屬内容和享受更多權益,創作者也由此獲得更多收益。
這種付費訂閱模式确是國内首次出現,在被推出後初期隻是對部分創作者開放。
總結以上各平台的付費機制來看:
目前平台上主要設計付費模式的内容是泛知識、影視娛樂類内容以及像是NBA比賽這樣的版權内容。
使用者可能會為能夠讓自己有所收獲的專業知識付費,同時也會為喜歡某個人而付費,為某類娛樂性極強内容而沖動買單。比如願意付費訂閱創作者的使用者必然是追随多年的忠實粉絲,付費後的“特殊粉絲待遇”就能夠使其獲得滿足感。而願意付費觀看短劇的使用者,也幾乎都會評論稱是因為劇情上頭、有“中毒性”,是以才會不自覺地連續觀看。
但不得不承認的是,不論是為愛還是為沖動,使用者的付費水準都不算太高。
短劇内容方面,雖然如今有更多正規影視公司參與制作,但其價格一直以來都是1元1集、2元3集、3元5集、10元打包的水準,與長視訊平台上的網絡電影和超前點播的網劇相比單價都更低。像是《危險的姐姐》這類短劇,其免費播放的部分單集點贊量都在10萬左右,釋出劇集的主賬号粉絲量也在700萬以上,但最終大結局也僅吸引到5萬人付費。
知識付費方面,平台上銷量過萬的付費課程并不多,一些付費課程其實也已經跳出了“為短視訊内容付費”的範圍,創作者往往還需要有錄播内容回放、一對一指導、作業點評等其他服務相配套才能夠吸引使用者。
更常見的操作是,知識付費的“專業戶”們,在平台上投放資訊流廣告,将使用者拉入“私域”,再進行課程銷售、轉化,而非直接在平台上開課。
跳出平台思維,站在創作者角度,短視訊付費目前的角色也仍在“補充”的位置上。
即使最有付費希望的短劇,品牌植入、流量分賬仍然是主流變現方式。放到更大的視角下,用免費短劇捧人,再讓人進行帶貨直播,也是一條有人探索的路徑。例如在快手上收獲超9億播放量的短劇《這個男主不太冷》,其主角一隻璐在因為短劇漲粉之後很快就成為了直播帶貨達人。
海外平台如何做短視訊付費
短視訊付費在國内難做,那麼在使用者付費習慣已經養成、付費意願也更高的海外,情況又如何?
YouTube是首先可以參考的平台,在探索付費模式方面YouTube多年來從未停止腳步。
早在2014年,YouTube就推出了YouTube Premium這一付費服務,這相當于國内各大長視訊平台的會員,使用者在訂閱後可以享有免廣告、離線緩存、背景播放等權益,此外它也包含着YouTube Music以及Play Music的會員。
2017年,YouTube推出“超級聊天”服務,使用者可以通過付費來讓自己評論的内容在不斷更新滾動的直播評論區中停留更長時間,同時也變得更醒目。2018年,YouTube又推出了“頻道會員”,這也就是前文提到愛奇藝随刻所對标的模式——使用者為創作者付費後,可以專享更多獨家内容。2020年時,YouTube官方稱頻道會員的收入已經增長至2019年的4倍。
來源:YouTube Official Blog
今年,YouTube又宣布将拓展其功能及服務,其中有不少是以使用者付費項目來幫助創作者提升其變現能力。例如将“超級聊天”功能從直播擴充到短視訊,“頻道會員”功能也為直播主播們開通,“禮物會員”功能可以讓觀看直播的使用者為其他人購買頻道會員,以及計劃将NFT引入平台,讓創作者可以直接向自己的粉絲們出售。
除了YouTube,更多包含短視訊内容形式的社交媒體平台也都有使用者付費訂閱服務。Facebook于2020年推出訂閱服務,緊接着就是Twitter在2021年推出相似的“超級關注”服務,Instagram也在今年開始做測試。
Instagram 付費訂閱功能
這些平台的付費訂閱其實在模式上幾乎相同,細小的差異隻在于平台内可選擇付費的内容形式以及附贈的相關權益。例如在Twitter上,付費訂閱的使用者是可以看到獨家推文;在Instagram上,付費使用者則可以看到獨家Instagram故事(24小時後消失的照片或視訊)以及實時直播的通路權限。
今年,TikTok也開始測試付費訂閱模式。可以說在海外,這種使用者付費已經是和廣告流量分成一樣基礎和正常的模式,平台内隻要有原創内容便可運用。
短視訊付費是雞肋嗎?
在國内,短視訊付費顯然還處于早期、輔助補充的角色,并略顯雞肋。但如果換個角度思考,或許這種模式的目的從一開始就不是變現。
海外平台持續豐富付費模式,基本上都是在強調要為創造者帶來什麼。YouTube首席産品官Neal Mohan在自己釋出的文章中就反複提到“創作者”這個詞,表示 YouTube始終大力投資于創作者。并且他也強調更多元化的收入組合可以幫助創作者應對諸多意外環境。不難看出,平台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通過提供更多變現模式,來獲得更多創作者的青睐。
而将更多創作者更穩定長期的留在平台上,這背後更終極的目的其實還是為應對行業競争。
自從TikTok等國内短視訊平台打入海外市場後,短視訊賽道始終是你追我趕,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幾個巨頭玩家幾乎全都在平台内嵌入短視訊内容。這種競争首先就展現在對創作者的扶持上:其一是直接砸錢給予創作者激勵獎金,其二就是讓創作者直覺看到平台上有更多變現機會。
是以在新功能和商業模式上,各個平台都在彼此“借鑒”,其重疊度也越來越高。比如YouTube會增加電商業務,讓創作者開店帶貨,以及植入更多來源于直播平台的功能為主播們創收。以往和抖音一樣的TikTok,如今也在廣告流量分成之外,補足了讓使用者直接為創作者和其創作的内容付費的模式。
雖然海内外的環境不同,但對比來看這對國内平台來說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如今短視訊知識内容付費已經跑通成熟,娛樂内容的付費最終還是在為“部落客”那個人買單。使用者與創作者之間形成的追随感、專屬感以及互動需求,足以支援付費訂閱。而且這也是YouTube等海外諸多平台已經驗證過的可行模式。
雖然就目前使用者付費水準來看,增加一種短視訊付費模式為創作者帶來的實際效果可能和直接平台砸錢給分成相比意義不大,但直覺上這是平台給内容創作者提供了更多變現通道,對創作者來說是一個變現的突破口。不斷探索之下,平台也會逐漸形成更加完善的内容創作者成長體系,這可以直接激勵創作者對其入駐的平台做出有側重性的選擇,也能夠激勵其優化内容。
盡管對平台而言,付費和廣告收入相比帶來的收入仍是太杯水車薪,但這必然也是種商業化補充和探索,特别是在如今廣告業務承壓的大背景下就顯得更有意義。
曾經長視訊的付費會員模式剛出現時,使用者排斥心理也很強,但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發展後使用者也已然接受。從使用者習慣上看,短視訊付費的“包袱”不重,較低的單價還增加了使用者沖動付費、為愛付費的可能性。短視訊付費,未必會比長視訊付費走更艱難的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