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心瞳瞳
有醫生告訴過丁香園,「誤診的機率不會超過 10%」。
但作為一個小機率事件,誤診卻有專為它創辦的期刊。1985 年,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主辦《臨床誤診誤治》期刊,近 40 年過去,這本期刊仍在更新;2001 年,中華預防醫學會創辦《中國誤診學雜志》;幾十年來,更多探究誤診的論文也紛至沓來。
「小機率」,卻比對了更新近 40 年的期刊。或許正是因為,誤診背後有更多值得深究的問題。
誤診,存在臨床每一個角落
誤診真的小機率嗎?
據悉,《臨床誤診誤治》以每月二十餘篇論文的速度,數十年來已經有約一萬篇「誤診」論文發表。這些論文的基石,便是數以萬計實實在在的誤診病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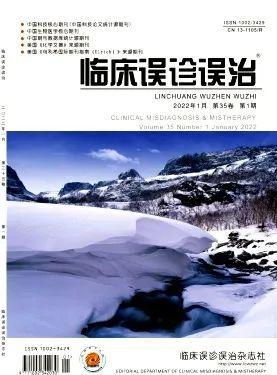
《臨床誤診誤治》期刊
同樣,在知網上搜尋「誤診」二字,會出現近 8 萬篇文獻,幾乎都是對于某種疾病的誤診研究,其中有一些是誤診率超過 60%的疑難雜症,但也不乏心肌炎、胰腺炎等非罕見病。
知網搜尋「誤診」截圖
來自四川某三甲醫院内分泌科的醫生陳蕾(化名)向丁香園表示,「幹臨床,誤診永遠會存在。」「誤診」對于臨床醫生來說,避無可避。
北京某三甲醫院胸外科張倫(化名)醫生給出更确切的感受,「幾乎每天都可能遇到誤診。」例如,同樣症狀的患者,去兩家不同醫院就診,就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答案。
比起認真糾錯的「小機率」,其實「偏差診斷」出現在醫療的每個角落。
華東某醫院婦産科醫生劉鎮華(化名)就曾遇到過這樣的一個病人:65 歲女性,在既往檢查中發現卵巢上長了一個 5 公分大小的囊腫,于是為她安排了切除手術。
但在手術前夕,這位女性卻突然出現劇烈腹痛,很可能是囊腫破裂了,這讓劉鎮華醫生如臨大敵——破裂的囊腫高度懷疑是惡性,病人的五年生存率極低。
劉醫生加急為病人做了手術,手術過程中才發現,病人并不是卵巢囊腫,隻是輸卵管膿腫,伴有盆腔炎。
由于病人已經 65 歲,劉鎮華醫生預設了對方沒有性生活。事實上這個病人的性生活還很頻繁,一周有 2 次左右,且因為已絕經,她和老伴的性生活并未使用避孕套,進而導緻盆腔炎,引起腹痛。
之後,無論遇到了多大年紀的女病人,劉醫生都會和對方确認「是否有性生活」。
處理誤診,應該把眼光往前看
所幸,老年女病人被「誤診」,但她沒有被「誤治」。
陳蕾醫生告訴丁香園,即使發生了誤診,在多數情況下也不會發生誤治。例如患者因為某症狀最初被确診為 A 疾病,但在治療過程中,由于 B 疾病産生的症狀慢慢顯現,醫生會馬上調整,從對抗 A 疾病的方案更改成對抗 B。
雖然最初的診斷屬于誤診,但對患者的治療沒有太大影響。
但這不是所有誤診的結果。如果遇到患者迅速惡化的情況,醫生便來不及調整。
2012 年,湖南發生一起醫療糾紛:患者是一位中年男性,因頸椎病在某醫院做了頸椎前路減壓植骨内固定術,術後出現急性腎衰竭、呼吸驟停,醫院給予對症治療,但患者還是很快去世了。
醫院認為患者死于「脊髓水腫或喉頭水腫緻呼吸循環衰竭,多系統器官功能衰竭」,但患者家屬并不認可,他們找到司法中心,由法醫最終鑒定患者死于「術後腦出血及多器官功能衰竭」。
後來死者将醫院告上法庭,指責醫院因誤診延誤治療,一審判定醫患雙方過錯比例為 6:4。
該案的裁判文書網截圖
這樣的醫療糾紛并不罕見。
五年來,光是告到司法機關的就有近一萬起,院内投訴事件更是數不勝數。投訴發生後,調節、賠償、給予手術友善往往是醫院層面最多的處理方式。
海量的投訴也讓醫院疲累,劉鎮華醫生說,部分醫院甚至将責任完全推到醫生本人身上,要醫生和患者對峙。
很顯然,在大部分情況下,處理誤診的手段變成了「處理誤診引起的投訴」。
圖檔來源:視覺中國
可實際上,處理好了這次投訴,可能還會有下次投訴,這不是減少誤診發生的根本方法,更需要解決的是發生在「誤診之前」的事。
來自西安某專科醫院的王偉甯(化名)醫生告訴丁香園,他曾在教育訓練時遇到一個新生兒誤診病例:出生四天後,這個嬰兒才被發現是先天性的肛門閉鎖,四天内這個孩子經過了多個助産士、醫生、護士的手,卻沒有一個人發現。
先天性的肛門閉鎖并不是完全平整,還是會有一點凹陷的,而年輕的助産士并沒有親眼見過真正的肛門閉鎖,加上用棉簽檢查肛門時,棉簽上粘了一點胎脂,助産士誤以為沒問題。新生兒的家人沉浸在得子的喜悅中,也沒有發現。
這一天是星期五,接着周末兩天都是值班醫生,醫生人手本就不多,也沒有人發現。直到周一,家人發現孩子一直沒有解大便,叫來醫生檢查,醫生才發現孩子肛門閉鎖。
這個孩子後來轉入兒保科進行治療,助産士統一被重新教育訓練,保證人人都能識别常見的新生兒畸形。
這個醫療糾紛就暴露了醫院内部系統的問題:助産士的教育訓練不足,他在能力不到位的情況下,便通過了考核,上崗工作了。其次,交班醫生在周六孩子一整天未解大便的情況下,周日時依然沒有發現孩子的問題。
王醫生表示,在後來的從業過程中,針對常見的誤診情況,科室會組織交叉學科的教育訓練,邀請其他諸如外科、新生兒科的主任來科室做分享。
但這些教育訓練,全由科室主任點對點邀請——院方并沒有系統性的前置教育訓練。
醫院可以做什麼?
在沒有院方的系統指導下,一些資曆較淺的醫生就有可能誤診。
年輕醫生對「誤診」等問題的教育訓練需求很強烈,但真正落實下來卻并不容易。其中,組織醫生們定期複盤疑難病例,便是有力的一環。
張倫醫生所在的醫院,是以胸外科著名的北京某三甲。每當有病人死亡時,全科室便要坐下來一起讨論這個病人的病情,複盤病情變化的每個節點。其中,就包含了不少最初誤診的案例。張倫醫生說,之後他再遇到類似的案例,都會格外注意。
在内分泌醫生陳蕾所在的醫院,「疑難病例讨論會」、「三級查房制度」也幫助降低了誤診。當面對特殊病例時,一位醫生的判斷有誤,屬于人之常情。若讓更多醫生參與進來,綜合判斷才能更加精準。
根據 Mayo Clinic 的調查發現,在該診所尋求第二診療的患者裡,有 21% 的患者第一次診療時被誤診了,66% 的患者得到了更精準的診斷。
Mayo Clinic 診所網站截圖
這些疑難病例中,還有不少屬于二進制論,并非單一疾病可以解釋,而這也極有可能造成誤診。
海南省某醫院内分泌醫生林惠謹(化名)告訴丁香園,她曾收入院的一個年輕男病人,入院時是典型的上睑下垂,而且在外院已确診為糖尿病神經病變,于是她就給予了營養神經的治療,但效果一直不好。
一籌莫展時,她請來同院的神經内科專家會診,專家一眼就看出,這個男孩患上了重症肌無力。後來病人轉入神經内科住院治療,恢複地很好。
林惠謹醫生介紹,這樣的會診制度,在她們醫院已經超過 10 年。「這是個非常好的減少誤診的方法。」
但是,這些制度雖然側面降低了誤診率,卻并沒有一個制度是專為誤診而建立的。陳蕾醫生在遇到誤診案例時,還曾去期刊查找,發現《臨床誤診誤治》中早就收錄過類似的案例。如果能對易誤診的疾病有針對性的教育訓練,相信會有不同的結果。
婦産科醫生劉鎮華說,「歐洲一些醫院的專科教育訓練中,貫穿着一個 clinical governance 的概念,每個科室内都會采取一系列的舉措,減少包括誤診在内的不良事件發生。」這些舉措包括教育訓練、增加人手等等。這些醫院架構問題,在劉醫生看來,國内醫院還有提高的空間。
劉醫生提到的「增加人手」,也有不少醫生提出同樣的訴求。
内分泌科陳蕾醫生表示,「一上午門診,有時能看七八十個病人,每個病人的時間确實也必須壓縮、再壓縮。」這時,可能醫生的查體就會有疏漏。
曾有一個不明原因發燒的病人來到醫生所在醫院就診,許多醫生沒有查清他的病因,最後才發現是病人會陰部被蟲子咬了,引起了感染。
如果最開始醫生有充足的時間查體,或許這起誤診就不會發生。
陳蕾醫生也提到,有時下級醫院的檢查裝置不周全也會導緻誤診。例如有的病人在下級醫院做了 CT 懷疑胰島素瘤,但不能确認位置,在她的醫院做了 PET/CT 後才确診。
也有時,醫院過度的處罰會讓醫生對誤診産生恐懼心理,不敢面對的醫生甚至會增加誤治的可能。
對于誤診的研究,可能永遠不會結束。正如陳蕾醫生說,「醫學博大精深,醫生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臨床疾病面前,我們永遠都是國小生。」
再把視角放大一點,解決誤診不僅是醫生的事。作為醫院、政策制定者,更不應該置身事外。
畢竟,降低誤診率,和行業内的每個人、每一位就診的患者,都息息相關。
策劃:carollero
監制:gyouza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