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成書時間,大略有宋代說、元中後期說、元末說、明初說、明中葉說等等。這些說法中,筆者比較傾向于元中後期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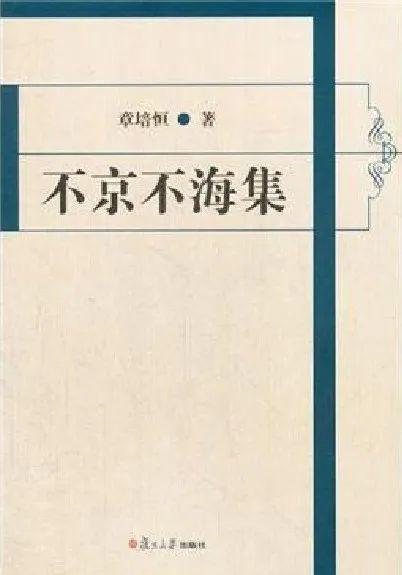
《不京不海集》
持這一意見的章培恒先生從《三國志通俗演義》小字注中“今地名”的考證認為“似當寫于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之前”,而沒有明确上限;袁世碩先生則斷定“約為十四世紀的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 [1]。
筆者據所見資料,認為兩先生的結論除了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證明外,還可有更具體的說明。試為考論如下。
首先,《三國演義》成書的上限可以從“說三分”話本的流傳得到說明。
今見宋元以來“說三分”的話本有刊于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的《三分事略》,和它的另一版本刊于元至治(1321—1323)年間的《三國志平話》[[2]]。古代小說刊刻流傳的基本規律是優勝劣汰,元至治三年(1323)《三國志平話》還在被人翻刻的情況表明,這時還沒有更好于它的三國小說問世。
而此後《三國志平話》等“說三分”的話本未見新版的事實,應當可以看作《三國志通俗演義》已經産生的迹象。是以,以元至治三年(1323)為《三國演義》成書的上限是較為可信的。
其次,《三國演義》成書的下限當以可推測的能見到此書的時間為準。
這個問題要複雜得多,容細為尋繹。瞿佑《歸田詩話》卷下《吊白門》:
清乾隆知不足齋刻本《歸田詩話》
陳剛中《白門詩》雲:“布死城南未足悲,老瞞可是算無遺。不知别有三分者,隻在當時大耳兒。”詠曹操殺呂布事。布被縛,曰:“縛太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意欲生之。劉備在坐,曰:“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布罵曰:“此大耳兒叵奈不記轅門射戟時也?”
張思廉作《縛虎行》雲:“白門樓下兵合圍,白門樓上虎伏威。戟尖不掉丈二尾,袍花已脫斑斓衣。捽虎腦,截虎爪。眼視虎,如貓小。猛跳不越當塗高,血吻空腥千裡草。養虎肉不飽,虎饑能齧人。縛虎繩不急,繩寬虎無親。坐中叵奈劉将軍,不從猛虎食漢賊,反殺猛虎生賊臣,食原食卓何足嗔!”記當時事調笑可誦。思廉有《詠史樂府》一編,皆用此體。
按陳剛中字彥柔,閩清人。宋高宗建炎二年進士,官至太府丞;張思廉名憲,号玉笥生。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少負才不羁,晚為張士誠所招署太尉府參謀,稍遷樞密院都事。元亡後變姓名,寄食僧寺以沒。有《玉笥集》十卷,卷一、二即瞿佑所稱《詠史樂府》,有詠三國時事詩十餘篇。
[補說:據《楊維桢詩集》卷三《赤兔兒》題注,《縛虎行》詩又見青照堂叢書本《鐵崖詠史》,“題下有‘呂布’兩字。錄兩首,又一首為:‘白門樓下兵合圍’”雲雲,即此詩。唯詩中“不掉”作“下掉”,“眼視虎,如貓小”作“眼中看虎如貓小”,“坐中叵奈”作“平生叵信”,“不從”作“不縱”。[[3]]《元詩選》張都事憲小傳雲:“思廉師事楊廉夫,尤多懷古感時之作。廉夫曰:‘吾用三體詠史、古樂府不易到,吾門唯張憲能之。’”(《初集》下庚集《玉笥集》)雖然此詩畢竟誰作,還當存疑待考,但與以下論述沒有邏輯關系。]
明汲古閣刻本《三國志》
今考《三國志》《後漢書》等,上引陳、張二詩及瞿佑釋義所述曹操白門樓殺呂布事基本依據史書。隻有呂布臨刑罵劉備一語,《三國志·呂布傳》作“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後漢書·呂布傳》作“大耳兒最叵信!”與瞿舉“布罵曰”雲雲相去甚遠。
但是,《後漢書·呂布傳》既已有“大耳兒”之說,陳詩“大耳兒”一語,與《三國志通俗演義》卷四《白門曹操斬呂布》引宋賢詩“枉罵無恩‘大耳兒’”句的情況一樣,還應被認為出自《後漢書》,瞿佑舉“布罵曰”雲雲的解釋是不妥的,可以不論。
又,張詩“坐中叵奈劉将軍”一句中“叵奈”一詞,《玉笥集》本詩作“叵信”,于史有據。《玉笥集》詠史諸作述事大緻密合史書,本詩作“叵信”既有版本的依據,當然可以視為原作如此。
瞿佑引作“叵奈”如非記憶有誤,則可能是因了他前舉“布罵曰‘此大耳兒叵奈不記轅門射戟時也’”的話而緻筆誤。
但是,《縛虎行》述事還是有溢出于史書的地方。如,《三國志》《後漢書》呂布本傳皆載呂布曾“拔戟斫幾”,未言方戟之短長;而本詩卻說“戟尖不掉丈二尾”,謂呂布之戟“丈二”,于史無征。
又,《玉笥集》詠三國事另有《南飛鳥》一首,題下注“曹操”,中有“白門東樓追赤兔”句,下注“擒呂布也”,謂呂布于“白門東樓”被擒;但是《三國志》本傳但言“白門樓”而未言樓之方位,《後漢書》本傳“布與麾下登白門樓”下注引宋武《北征記》謂“魏武擒布于白門”,又引郦道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擒陳宮于此。”明确說白門樓為下邳之南門,則“白門東樓”也于史無征。
清刻本《玉笥集》
當然,更重要的是上引瞿佑釋陳詩所舉“布罵曰”一語也不見于史書,作為說詩用語,又顯然不會是瞿佑的杜撰。從《玉笥集》有詠三國史事詩達十餘首之多,可知張思廉對三國史籍的熟谙;瞿佑也是熟悉《三國志》的,這有他所著《樂府遺音》中《沁園春·觀〈三國志〉有感》為證。
是以,出現于他們筆下的這些關于三國的于史無征的文字表述不大可能是對史實的誤記,而是必有另外的根據。其根據何在,對于我們所要讨論的問題帶有關鍵意義。
一般說來,它們既不見于正史,就應當出自野史小說或戲曲。今查《三國志平話》卷上謂呂布“使丈二方天戟”,則張詩“丈二”有了着落。但是《平話》隻有“白門斬呂布”的題目,正文根本沒說到“白門樓”。至于呂布臨刑的罵語,則作“呂布罵:‘大耳賊,逼吾速矣!’”除提到“大耳賊”外,語詞、語意也皆與瞿佑所舉“布罵曰”雲雲相去甚遠。
當然,宋元“說三分”的話本應不僅這一種書,但《三國志平話》獨能傳世應表明它是各本中最好的。此類具體的描繪以及瞿舉“布罵曰”這等極精彩的話既不見于此本,則也就大緻可以斷定不見于其他“說三分”話本。
連環畫《白門樓》
金、元三國戲演白門樓事的,今知隻有于伯淵《白門斬呂布》。此劇已佚。“白門東樓”“布罵曰”等的描繪,不絕對排除為此劇遺文的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并且瞿佑也不會根據于它。理由有二:
一、于伯淵生卒年不詳,鐘嗣成《錄鬼簿》列于“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于世者”之列。
《錄鬼簿》自序于至順元年(1330),則于伯淵當卒于至順元年以前。《白門斬呂布》作年更要早一些,但是,一般說不會比《三分事略》和《三國志平話》的刊刻流行更早,進而它的創編根據于史書,也幾乎一定要參考這一“說三分”的平話。“說三分”的平話中既然還沒有這些内容,一般說也就不會出現于《白門斬呂布》雜劇。
二、戲曲後起于小說,詩人用事,用戲曲的遠不如用野史小說者多;瞿佑又是詩人而兼小說家,年輕時就編過《剪燈錄》,後來作《剪燈新話》著名于世,很難想像他是用戲曲的文本而不是用野史小說說詩。是以,退一步說,即使《白門斬呂布》有“白門東樓”“布罵曰”的文字,瞿佑所引也可能另有根據。
這兩點原因又可以使我們斷定這幾處用語不會出自《三國志平話》大約同時或以前的戲曲。
上述宋、金、元有關三國的話本、戲曲之後可望為張、瞿所根據的三國小說就是《三國志通俗演義》。
今查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各處寫呂布持“方天畫戟”而未言“丈二”;但是,《白門曹操斬呂布》一則雖未明言白門樓為下邳東門樓,而其叙事謂“東門無水”,侯成“盜赤兔馬走東門,魏續放出”,呂布“各門點視,來責罵魏續,走透侯成”,“布少憩樓中,坐于椅上睡着”,遂被擒……,正在城東門樓上。與下述“高順、張遼都在西門……被生擒。陳宮就南門邊,被許晃捉了”也相吻合。
《三國志通俗演義》
是以張詩“白門東樓”的說法很可能是從《三國志通俗演義》得到的印象。而呂布臨刑罵劉備語,《三國志通俗演義》此處正作“布回首曰:‘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雖然句中并無“叵奈”一詞,但是,認為就是瞿佑釋陳詩所舉“布罵曰”的出處,也是确當無疑的。
至于今存嘉靖本寫“方天畫戟”不言“丈二”,大約因為小說寫了張飛“身長八尺”用“丈八點鋼矛”(《祭天地桃園結義》),再寫呂布“身長一丈”(《呂布刺殺丁建陽》),若說他的戟長“丈二”,就不合理了。
是以,如上所述張詩作“丈二”可能本自《三國志平話》。而溯源可能自唐李白《送外甥鄭灌從軍三首》之二:“丈八蛇矛出隴西,金盤一擲萬人開。”
又,《三國志通俗演義》呂布罵語沒有“叵奈”一詞,則應當是流傳中抄漏或刊落所緻。“奈”通“耐”,“叵奈”又作“叵耐”,是宋、元小說習用語。
連環畫《跨江擊劉表》
事實上羅貫中小說常用這一詞彙,如《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二《孫堅跨江擊劉表》:“叵耐劉表昔日斷我歸路,今不乘時報恨,更待何年?”又據傳為羅著《三遂平妖傳》第十二回:“叵奈你出家為僧,不守本分,辄敢惑騙人錢财!”
總之,在沒有堅強反證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認為張詩用“白門東樓”、瞿佑舉“布罵曰”均出《三國志通俗演義》。而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經明人修改過的,張、瞿見到的應當是它的祖本或更接近于原著的本子。那些本子均早于張思廉《縛虎行》《南飛烏》諸詠史樂府詩。
據錢仲聯等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版《中國文學大辭典》,張思廉約生于元仁宗七年(1320),卒于約明洪武六年(1373)。則即使其詠史樂府作于入明以後,他所根據之《三國志通俗演義》也當産生于元末。
而考慮到一部書流傳到它的如“布罵曰”一類話語播于衆口,成為詩料,需要較長的時間,《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下限還應有較大提前。若作具體的說明,則袁世碩先生從嘉靖本小字注中“今地名”考證得出“約為十四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判斷是大緻合理的。
但是,又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小字注包括“今地名”之注不大可能出自作者之手[[4]],這就還可以從成書“四十年代”的下限進一步提前,而與章培恒先生從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小字注“今地名”的考證所得出“《三國志通俗演義》似當寫于文宗天曆二年(1329)之前”的結論若合符契。
是以,從本文考證并參酌章、袁二先生的意見,我們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的時間在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之間,即元泰定三年(1326)前後。
這裡順便提出,正如許多學者所考今存嘉靖本是經明人修訂過的,筆者頗疑書中若幹文字獄的描寫乃是後人的增補。
《三國志通俗演義》有四處關于文字獄的描寫:一是第四回董卓誅少帝的《雙燕詩》之獄,二是第三十四回蔡瑁誣劉備作反詩之事,三是第七十二回楊修釋“雞肋”為曹操所殺,四是第一百十四回司馬昭殺曹髦《潛龍詩》之獄。這些情節除楊修事有蛛絲螞迹見于史書,其他都于史無征,也不見于《三國志平話》,完全是虛構的。
《三國志通俗演義》作者羅貫中同時是《水浒傳》作者之一。很巧的是《水浒傳》寫草澤英雄之事,竟也有兩處關于文字獄的描寫,即第三十九回的“浔陽樓宋江吟反詩”,第六十一回的“吳用智賺玉麒麟”造作盧俊義的反詩,這兩個情節也不見于《水浒傳》成書的重要基礎《宣和遺事》和其他文獻,顯然也是虛構的。
士禮居藏本《新刊宣和遺事》
筆者認為,這些虛構的文字獄的故事都不大可能是羅貫中、施耐庵所為。理由有二:一是如上所述并無史實、傳說或早期話本的根據;二是宋、元時代雖然也有文字獄,但是以殺人的事很少。從生活決定創作的角度說,羅貫中、施耐庵生當文禍并不甚嚴重的元代,不大可能對文字獄有如此特别的注意和動情深入的描寫。
這些描寫應是後人加入的。魯迅《中國小說的曆史的變遷》一文論《水浒傳》結局說:
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層,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統一天下之後,疑忌功臣,橫行殺戮,善終的很不多,人民為對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見,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這也就是事實上的缺陷者,小說使他團圓的老例。
同樣,由于朱元璋的疑忌和橫行殺戮,明初著名文人也是“善終的很不多”(參見趙翼《二十二史劄記·明初文學之禍》)。以魯迅之見觀之,《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文字獄的描寫除了未至于“成神”,不合“使他團圓的老例”之外,正可以看作是對于被害之文人“表同情起見”。是以,也很可能是明初人加進去的。
明初文人通過小說對文字獄表示抗議的不乏其人。例如看來對三國故事非常熟悉的瞿佑,在他寫成于明洪武十一年的《剪燈新話》中就不止一處寫到文字獄,抨擊了這種野蠻的文化專制政策。
如《令狐生冥夢錄》寫令狐生因寫詩被冥府拘系,在“供狀”中稱“偶以不平之鳴,遽獲多言之咎”,對冥王以詩罪人深緻不滿;《綠衣人傳》寫賈似道搞“官倒”販私鹽,有太學生以詩諷之,“遂以士人付獄,論以诽謗罪”。又寫賈似道于浙西行公田法,民受其苦,有人作詩諷刺,亦“捕得,遭遠竄”。
《剪燈新話》,向志柱點校,中華書局2020年11月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洪武七年高啟因替蘇州知府魏觀撰《上梁文》而被殺,《水宮慶會錄》卻寫餘善文為龍王撰《上梁文》被待為上賓,這作為一部書的首篇,簡直就是與明太祖方興未艾的文字獄唱對台戲。
可是,永樂中瞿佑卻因詩禍被谪戍保安十年。遇赦後他去世前幾年所寫的《歸田詩話》中,又詳細記載了他所見聞許多遭受文字獄迫害的友人的情況,凄楚哀怨,終生為之耿耿于懷。
由瞿佑以小說影射抨擊朱元璋的文字獄和終生懷恨,推想有人通過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浒傳》中加入關于文字獄的描寫以寄慨,豈非大有可能和順理成章?是以,今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浒傳》有關文字獄的描寫都極有可能是明初人增入的。
這種因有所寄托而進行的情節增補(包括相應的文字改動),對作品思想傾向往往有較大影響。但是,就全書而言,并不一定造成文字上太大的差異。是以,章培恒等幾位學者先後所作考證中關于“小字注”有(或多數)元人所作的共同認識仍然是可信的。
綜上所述,重複說明我們的結論是: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之間,即元泰定三年(1326)前後,而今存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正如許多學者已從别種角度有過說明,是經明初人改動過的,這個改動包括了有關文字獄描寫的插增。
《沈伯俊評點三國演義》
附 記
本文已五易其稿,其間沈伯俊先生多次來信和通過電話給予匡正和指教,最後改定之前沈先生緻作者信中附說:
“又,我查了一下手邊的幾種《三國》版本,其中雙峰堂本《三國志傳》、喬山堂本《三國志傳》均有‘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耶’一語,也許比嘉靖本更接近瞿佑所引的語氣(‘耶’與‘也’相通),謹供兄參考。”
這是很重要的意見。筆者除了表示衷心的感謝外,得到兩點啟示:(一)不同系統版本的《三國演義》共有此語的現象表明,此語有最大的可能出自羅貫中原本《三國演義》。本文由此深入考察得出的結論應是可靠的;(二)也許可以加強許多學者認為《志傳》本所據之本早于嘉靖本,因而更接近羅貫中原本的觀點。如果這兩點認識有合理之處,則應歸功于沈先生來信的無私的貢獻。
上下滑動檢視注釋
注釋:
[1] 參見沈伯俊《八十年代以來研究綜述》,載《稗海新航——第三屆大連明清小說國際會議論文集》,春風文藝出版社1996年7月版。
[2] 兩書刊刻年代的認定據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該詞目陳翔華先生文。
[3][元]楊維桢《楊維桢詩集》, 鄒志方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頁。
[4] 參見沈伯俊《八十年代以來研究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