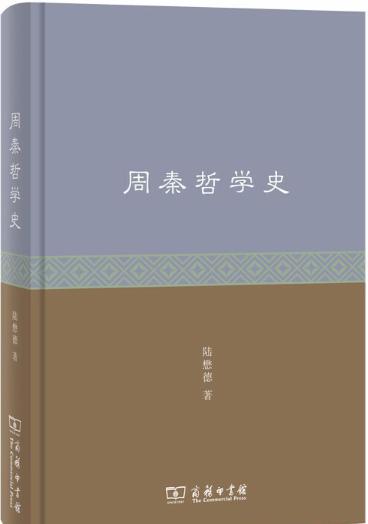
中國哲學史作為獨立學科,始于“五四”時期。胡适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是這個學科的奠基性著作。在對20世紀中國哲學史學科發展曆程的梳理過程中,有些非主流的著作往往被人們忽視。其實這些非主流著作也有其學術史的意義,例如分别在1923年和1929年出版的《周秦哲學史》(陸懋德著)和《中國哲學史》(鐘泰著)
胡适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建構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第一塊奠基石。胡适以“疑古”反對崇拜儒家經典的“信古”,區分哲學與經學的”疆界”,賦予中國哲學史以從經學中獨立岀來的現代性品格。這是他不同于此前的陳黻宸《中國哲學史》講義和謝無量《中國哲學史》的最顯著的特征。此後胡适說:《中國哲學史大綱》“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所謂“變色”,就是改變了此前類似陳黻宸、謝無量那樣蒙在中國哲學史身上的經學之色。然而,這樣的“變色”,實質是由經學範型轉向了西學範型。由于哲學來自西方學科體系,因而中國哲學史在與經學分離的同時,又必然産生對西方哲學的“依傍”。但是,中國哲學是有其民族特點的,如果對此不注意,那麼中國哲學史隻會成為西方哲學在中國的翻版。事實上,胡适和馮友蘭的著作都出現了這樣的問題。比如,金嶽霖在關于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中指出”我們看那本書的時候,難免一種奇怪的印象,有的時候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人。”就是說,馮友蘭以中國哲學的現代性诠釋消解了中國傳統哲學的民族特色。
陸懋德和鐘泰的著作正是有鑒于此,對胡适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提出了挑戰。前者認為胡适以西方式的知識論(邏輯方法)眼光整理先秦哲學,完全是抹殺了中國哲學的特點,因而其取材結構仍依傳統的六家之分;後者強調中西哲學是各自自成系統的,用西方哲學術語來叙述中國哲學,就會扭曲後者的真實面目,是極不合理的,于是沿用傳統術語而擯棄西方哲學用語。總之,他們試圖淨化中國哲學史研究中西方哲學的一切印迹,以拒絕西方哲學範型來維護中國傳統哲學的民族性。雖然這并沒有在後來被中國哲學史學界普遍接受和認同,但是陸懋德、鐘泰的著作依然是有學術史價值的,即他們對于胡适的挑戰,把内在于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現代性和民族性的沖突凸現出來,成了胡适之後研究中國哲學史者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事實上,馮友蘭正是思考了陸懋德、鐘泰揭示的沖突,提出了從“形式系統”和實質系統兩個方面建構中國哲學史學科。他認為,在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構上,一方面需要對中國傳統哲學予以形式系統的邏輯重建,使其具有現代性,另一方面需要在實質系統上展現中國傳統哲學不同于西方哲學的特點,使其具有民族性。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出版後,很快取胡适《中國哲學史大綱》而代之。這并非僅僅是由于它具有了後者欠缺的通史的完整性,更重要的是它展現了思考如何解決現代性和民族性沖突的自覺,并力圖使兩者得以統一。由此可以看到,陸懋德和鐘泰的著作在學術史上構成了從胡适到馮友蘭的中間環節。這提示我們,非主流的學術著作也是研究學術史時應當認真分析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1月/22日/第002版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