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武漢會戰之後,華北抗戰也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在黃河以北的中條山防區,第一戰區仍然保留着兩個集團軍近20萬兵力,直接牽制着日軍三個師團的主力。并且在其後三年時間裡,在敵後八路軍的配合下,中條山守軍連續擊退了日軍七次大規模進攻,日寇華北方面軍對此如芒在背,稱其為“華北的盲腸”,但苦于兵力不足,一時無可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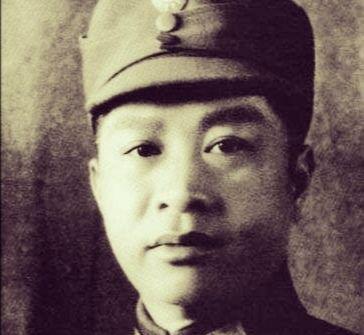
新四軍軍長葉挺
然而到了1941年5月間,日寇卻能夠集中了六個師團、兩個半混成旅團超過10萬人的兵力,對中條山防區發動空前規模的進攻,在日寇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中将、第1軍司令官筱冢義男中将的統一指揮下,敵人采取“中間穿透、四面合圍”的戰法實施猛烈進攻。僅僅幾天時間,中條山守軍防線迅速土崩瓦解,其中陣亡42000餘人、被俘35000餘人,其他大部潰散,衛立煌第一戰區黃河以北的前進陣地不複存在。
中條山會戰于是被蔣某人稱為“抗日最恥辱一戰”,而這次戰役日軍能夠在華北調集重兵,完全是當年初“皖南事變”帶來的惡果。原來,自1940年7月起,鑒于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不斷發展壯大,重慶政府舊病複發,以參謀總長何應欽的名義,向延安方面提出關于“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作戰區域”問題,同時附帶一個近乎指令式的要求:“八路軍和新四軍之各部隊,限時全部開到河北、察哈爾兩省以及山西北部地區,并将新四軍納入第18集團軍作戰序列”。
新四軍政委項英
何應欽的指令還包括:無論八路軍還是新四軍的部隊,今後非奉軍事委員會指令不得擅自越出“規定之地區”,同時“第18集團軍除編為三個軍六個師(兩旅四團制的整理師)和三個補充團外,可再加兩個補充團,不準再有支隊建制,新四軍編為兩個整理師”。這就意味着,要求已經在敵後形成有利态勢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放棄通過艱苦奮戰和浴血犧牲換來的大片抗日根據地,全線後撤并自我縮編。
從戰略層面上講,這等于極大解除了侵華日軍在後方戰場上所面臨的兵力空虛局面和軍事壓力,與助敵為虐無異。甚至連日軍情報部門都對這一指令大感意外,南京的“中國派遣軍”、北平的“華北方面軍”各級參謀部門,晝夜研究重慶方面的真實意圖,卻仍然沒有判斷出來:重慶政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真會下令中國抗日軍隊自相殘殺。
新四軍參謀長周子昆
然而重慶方面的軍事部署卻是緊鑼密鼓,不僅調動第八戰區胡宗南部封鎖陝甘甯邊區、還密令第三戰區顧祝同部從抗日前線抽調部隊包圍皖南地區,同時再令湯恩伯第31集團軍和李品仙第21集團軍(原屬第五戰區)向東移動,準備配合蘇北的韓德勤向華中地區的八路軍、新四軍發起進攻,同室操戈的罪惡企圖顯露無疑。
1940年12月9日,重慶軍事委員會下達最後通牒式的指令: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限于本年12月31日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明年1月30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現在黃河以南的第18集團軍所有部隊,限本年12月31日止,開到黃河以北地區。同時還給新四軍北移專門規定了路線,那既是一條陌生的路線,也是一條危險的路線。
何應欽
為了顧全抗日大局,我新四軍軍部率領一個教導團、一個特務團和第一、第二、第三縱隊的各兩個團共9000餘人,于1941年1月4日起在葉挺和項英的上司下開始北移。兩天後的1月6日,當新四軍部隊到達皖南泾縣茂林地區時,遭到第三戰區顧祝同所部的八個師(第32集團軍上官雲相為總指揮)70000餘人的突然襲擊,新四軍除2000餘人突圍成功和少數被俘外,大部壯烈犧牲,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重慶方面和蔣某人想當然地認為,他們這種無恥的行徑必然得到侵華日軍的“默契配合”,短時間内日軍不會在正面戰場對重慶政府軍發動攻勢。而事實卻是嚴重打臉,由于華中敵後戰場的新四軍元氣大傷,暫時無力繼續牽制敵人,日軍迅速抓住這個機會從華中向華北大舉增兵,目标則對準了黃河以北的中條山防區。
顧祝同
日寇原本在中條山附近隻有第35(豫北)、第36(晉城)、第37(運城)三個警備師團,以及臨汾方向上的第41師團,這四個師團還要分出相當兵力對付八路軍部隊,是以是無力大規模進攻中條山防區的。然而“皖南事變”的發生,使日軍得以從南昌抽出第33師團、從蘇北抽出第21師團以及大量特種兵部隊,集結在中條山一線的日軍頓時增至10萬人以上,以中日軍隊當時的戰力比計算,日軍遂形成了絕對優勢。
日軍在擊破第一戰區中條山防區主力後,又得以集中力量“掃蕩”八路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中國的抗戰形勢由此進入最艱難的時期。重慶政府和蔣某人的所做作為,屬于徹頭徹尾的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此“害人害己”的行徑,也在抗日戰争史上留下極不光彩的一頁。
衛立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