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什麼:是過去傳到将來的回聲,是将來對過去的反映。——雨果
晚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使得近代中國飽受外族入侵,一度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作為中國曆史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朝代,清朝似乎飽受苛責,被人們定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幾乎是風評最差的朝代,對許多人而言,清朝本身似乎就是一種過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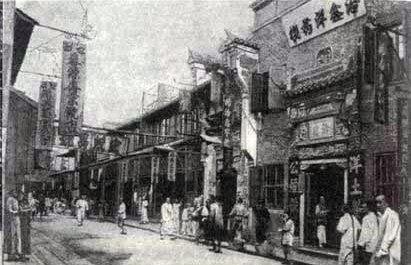
其實不然,國祚267年的清朝其實是對近代中國版圖貢獻最大的朝代(入主中原自帶的東北嫁妝,康乾雍連續三代對新疆的用兵,清準戰争消滅準格爾汗國,兩次對西藏的大規模用兵),盡管在與沙俄的《瑷珲條約》中,清朝先後割讓了近一百萬平方公裡的土地。
但是清朝即使在列強環伺,内部沖突迸發的環境下仍然牢牢控制着現代中國的版圖,内憂外患之下,晚清政府留給現代中國的最後一筆财富就是清末在西南邊疆大力推行的“改土歸流”所保護下來的川西和青藏高原地區。
一.軍政并施,清廷為鞏固西南西北邊疆所做的努力
1.連續三代帝王用兵西南西北,穩固青藏疆統治
從曆史角度來看,青藏疆三省大部分時間都脫離了中原王朝的掌控,新疆地區也僅是在空前強大的漢唐兩個朝代設立過都護府,把地區主權歸入中原王朝,而政治軍事主權依然屬于當地政權,這種治理方式埋藏着極大的隐患,一旦中原王朝統治力下降,軍政自治的邊疆地區極易爆發反叛。
清軍進關,入主中原之後,一直着手解決西南西北邊境的問題,此時北疆地區強敵環伺,大部分領土被準格爾汗國和葉爾羌汗國占領,康乾雍祖孫三代帝王,面對鼎盛時國土面積高達700多萬平方公裡的準格爾汗國,連續用兵讨伐100多年才成功消滅了準格爾汗國,将新疆劃入版圖,乾隆大喜過望,認為是“故土歸新”新疆故是以得名。
而西藏地區,由于中原王朝長期缺乏有效管理,面對王朝更疊,更是暗流湧動,各方勢力犬牙交錯,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達賴五世圓寂,西藏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内亂,康熙在得悉拉藏汗遇害、準噶爾部占領并洗劫西藏後,直接從西甯出兵,前往西藏平亂,在此之後的近半個世紀裡,西藏地區暴亂紛發,康乾兩帝反複出兵穩定西藏局勢,維護統治。
2.設立駐藏大臣,改土歸流初推行
面對西藏地區反複出現叛亂的情況,康熙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解決辦法,早期冊封汗王和宗教領袖;後廢止汗王制,又廢除達賴管家管政務的第巴制,而設諸噶倫集體上司,繼而在頗羅鼐父子時期實行首席噶倫帶郡王爵位制,最後設噶廈配套強化型駐藏大臣,且通過乾隆頒布的《欽定藏内善後章程》等章程,不斷加強提升駐藏大臣的實際管轄能力,削弱領主關系。
在明清朝代,由于各地區生産力水準差異較大,加之少數民族地區交通不便,文化差異巨大,雲貴川地區土司制度十分盛行,加之明朝對于西南邊陲的無力管轄,使得軍政自治的土司政權發展到巅峰。土司之間時常爆發械鬥甚至戰争,對清廷的管理也是叛服無常。
順治年間,面對土司之間攻伐不斷,雲貴地區大片耕地無人開墾的情況,順治帝企圖通過移民的方式同化當地的文化風俗以削弱土司實力,這一政策受到了部分土司的強勢阻礙。
雍正四年(1726年),雲南巡撫鄂爾泰對此言之甚明,其建言改流疏雲:“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至此,改土歸流已是勢在必行。改土歸流,不僅僅是要廢除掉落後的土司制度,更重要的是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進行和中原地區相同的統治制度。改土歸流自康熙年間開始,貫穿了整個清朝的統治時代。
清廷在吸取了元明兩朝治理西部邊疆的經驗,軍政并施,極大地加強了對西北西南地區的掌控,先是連續一百多年的用兵解決了西北大患準格爾汗國,面對西南雲貴川地區的複雜情況,不斷改革推行改土歸流,不僅大大加強了中央集權和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還使得原本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得到極大的開發,提高了社會生産力,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二.内憂外患,西部統治岌岌可危,改土歸流再固社稷
1.列強環伺,清末統治者新政救亡圖存
十九世紀中葉,在西方列強完成工業革命,叩開清政府閉關鎖門之後,清政府陷入了列強環伺的局面,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更是使得清政府陷入了内憂外患的尴尬局面,與此同時,新疆邊境告急,清廷意識到了自己逐漸喪失了對西部地區的控制。
1900年,逃亡至先的光緒帝深感“國勢至此,斷非苟且所能挽回厄運” 于是痛下決心,上谕“各就現在情弊,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主、學校科舉、軍制财政,當因當革”,由此便拉開清末新政的序幕。清未新政在邊疆地區主要圍繞籌邊改制與開發圖強兩方面進行的。籌邊改制的主要措施是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遍設州縣,改建行省;開發圖強則以招墾邊地。
興辦工礦、郵電、交通、文化教育為主,發展邊疆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實施實邊政策。面對英國東印度公司先後完成對印度,不丹尼泊爾等國的侵略,對西藏地區虎視眈眈的局面,清廷意識到了西藏的重要性,作為西南門戶,西藏是川,滇二省的屏障,是穩固西部後方的關鍵,同時沙俄也多次以勘探為借口進入藏區,以期染指西藏,西藏地區的局勢可以說關乎中國的半壁江山。
1903年,英軍直接出兵西藏,迫使西藏上層簽訂《英藏拉薩條約》,這一條約幾乎否定了清廷對西藏的實際統治和領土主權,加之英帝國在西藏培養親英勢力,西藏政權和清王朝的關系日益緊張,而達拉喇嘛的出走,更是給清廷釋放了一個危險的信号:西藏地區對中央政府的離心力正在急速變大。川督鹿傳霖奏稱,“若英俄争藏,則兵連禍結,将無已時。”改土歸流,加強統治迫在眉睫。
2.改土歸流的内因和導火索
土司制度,其前身是唐宋推行的羁奴政策,我國西南地區向來是少數民族雜居地,各民族之間風俗文化差異巨大,管理十分不便,在元明時期,土司制度在羁縻政策的基礎上應運而生,土司制度本着“以夷制夷”的方針在開創前期,确實大大提高了西南民族地區的穩定,間接加強了中原王朝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控制。
但是由于本質上與内地的行省制度相比,弊端較多,随着“分而治之”的時間推移,土司割據政權開始出現,抗拒朝命,嚴重影響了多民族國家的完全同意和成為了行政區域劃分的障礙,土司之間攻伐不斷,生産力無法發展使得土司制度成為了相當落後的管理措施,不僅為封建朝廷所不容,也嚴重阻礙了各民族交流和生産力提高,改土歸流已經成為客觀需求。
二十世紀初,清政府開始在川藏地區推行“固川保藏”的政策,在康巴地區推行新政。1905年,新任駐藏大臣鳳全及其随從共五十餘人在巴塘因為強推新政被全部殺害,引起朝野震動。
清政府在此次事件之後将“固川保藏”的戰略放在了第一優先級,開始大力推動新政在康巴地區的實行,以達到通過新政和改土歸流“經營川邊,以為西藏後援”的目的。這一政策有效的控制了親英藏族與中央政府的沖突,安撫了原本岌岌可危的西藏地區,間接保護了國家主權。
清政府确實算不上一個值得稱贊的朝代,晚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給近代中國帶來的苦難和屈辱是無法抹除的,但是它在對西南西北邊陲的控制和管理卻是最大程度的保全了中國的版圖完整,與元明末年不同,清政府并沒有因為無暇顧及邊疆而放棄雲貴青疆地區。
無論是左宗棠力排衆議收複新疆,還是清末新政,大力推動康巴川藏地區的改土歸流,都為鞏固中國西部地區的統治做出了巨大貢獻,使中國西南地區免受英帝國入侵,對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意義重大,倘若沒有這次新政和改土歸流,那麼中國的現代版圖恐怕不再完整。
從曆史軌迹上看,改土歸流不僅消滅了大部分土司頑固勢力,維護了民族穩定國家統一,也為後續對西藏土地改革政策和處理少數民族事務問題提供了經驗,是清政府給現代中國完整穩定所做的最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