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美國非虛構文學對于美國社會生态和自然生态的關注由來已久。對于社會生态進行反思的非虛構文本,主要展現為從批判現實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視角,貫穿對于美國社會變遷的真實記錄和深切反思。而對自然生态進行反思的文本,則主要展現為生态主義和理想主義視角,它們表達對于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生存生态的憂思。作家身份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着這兩種生态反思類型文本的文化與審美訴求。而這種追求最終通過文本結構、叙事話語和非叙事性話語等方面反映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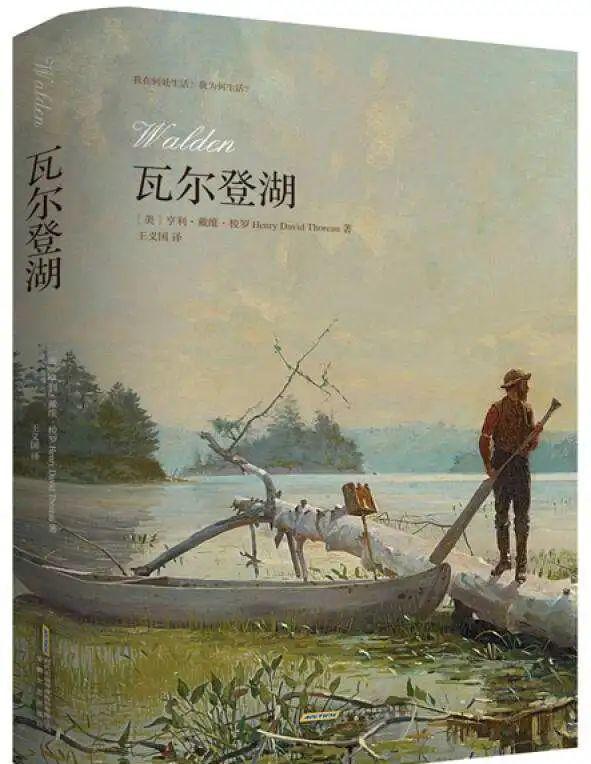
馬克·吐溫的《密西西比河上》、辛克萊的《屠場》,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新新聞報道、非虛構小說和口述實錄文學的代表人物諾曼·梅勒、杜魯門·卡波特、湯姆·沃爾夫、斯特克爾的諸多作品,都是比較典型的對于社會生态的反思類型的非虛構文本,它們從批判現實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視角,貫穿着對于美國社會變遷的真實記錄和深切反思,通過對美國社會激變的描述,來探尋社會生态中那些比虛構更激動人心的現實震蕩,以此表達作家們反傳統和反權威的獨立文明批判理念,表達對人的精神生态危機的深切關注。
而梭羅的《瓦爾登湖》(1854)、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1949)、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1962),以及戴維斯的《濃煙似水》(2002)、韋斯曼的《沒有我們的世界》(2007)等作品,作為對自然生态的反思類型的非虛構文本,主要從生态主義和理想主義視角出發,表達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憂思。1962年,當環境問題還沒有進入到美國政府的決策視野之時,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發表了她的作品《寂靜的春天》。這部作品沒有一如既往地書寫人與自然的詩意關聯,而是對“DDT”化學農藥這樣一個象征科技進步事物的批判,因為它在殺死危害農作物的昆蟲的時候,也扼殺了人類的生存環境,将一個喧鬧生機的春天變成為一個寂靜的春天。這部作品應該算作當代生态文學的“覺醒之作”。後來的所謂環保文學、生态文學等說法實際都與它分不開。可以說,《寂靜的春天》以來的美國非虛構文學,是在高速運轉、高度發達的工業化社會來臨之際對于生态危機的強烈反應,這種反應在某種意義上與對社會生态反思類型的非虛構文本的理念不謀而合,那就是以對于自然生态的人為破壞、人類再生系統面臨無法預知的厄運,來警醒政府和人民,來表達反傳統(人類中心主義)觀念和反叛人類愚蠢的盲目自大。這無疑是一種獨立的文明批判理念。在生态反思上,對社會生态反思類型的非虛構文本與對自然生态反思類型的非虛構文本有所不同。前者的關注局限在人的“自我”本身的危機(包括個人與國家、民族與文明、正義與非正義等),而後者則主要表現人與“他者”(包括除人之外的其他自然生态系統)的關系危機。而正是有了前者所表現的危機,才導緻了後者所揭示的危機,即自然生态的危機直接來源于人的精神生态的危機。因為在我們這個星球上,人是獨一無二的具有改變自然力量的物種,這使得他放大了自己的地球主宰意識,在欲望的驅使下,人對于環境平衡的無極限的打破,使得“土地倫理”扭曲,人成為“土地共同體”的巨無霸。對此,一些作家試圖将“和諧”作為某種解決之道,譬如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中對于“土地倫理”的闡釋,即是希望人與自然在這個土地共同體之中和諧相處;蕾切爾·卡遜在《寂靜的春天》裡所表達的“生物共享”地球觀念,也指向人與自然的“和諧”。
中國的生态文學大緻起于上世紀80年代的台灣,之後大陸的作家也陸續開始了這方面的寫作。徐剛一開始是以詩人的形象蜚聲文壇的,但恰恰是這樣一個詩意書寫人生的人,成為大陸比較早、也比較集中地以紀實的方式反映生态受損現實的作家。他的《伐木者,醒來》《沉淪的國土》《長江傳》以及他以詩的筆觸描繪青藏高原的《大山水》,讓我們深切感受到一個詩人對工業化程序中人的“詩意的栖居”環境淪喪的痛斥與反思。
上世紀80年代以降,一些有責任感的報告文學作家,密切關注現代化程序中中國生态所頻現的危機現實,寫出了許多震撼人心的警醒之作。單就描述江河生态和水危機而言,就有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嶽非丘的《隻有一條長江》、徐剛的《江河并非萬古流》和《長江傳》、哲夫的“江河生态報告”系列、馬役軍的《中國水危機》、盧躍剛的《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21世紀以來,陳啟文的《大河上下——黃河的命運》和《命脈——中國水利調查》等“江河系列”,既不是有關中國水系和水利的面面俱到的教科書,也并非《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的文學版,而是有其獨特叙述視角的紀實報告。作品将中國主要水系的水利建設曆史及其現實狀況的調查作為貫穿全文的主線,緻力于真相的揭示。必須超越人類中心主義,保持、修複,最終實作包括水在内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生态。保住了水的健康生态,就是保住了人之生存和發展的“命脈”。以現代人類的終極關懷即實作其主體自由為目的,思考和反思現代化程序中人與自然的關系,特别關注和警醒人類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種種與此目的相悖離的缺失,反思和批判工業化的負面效應以及人性中急劇膨脹的私欲,警惕和預防人類非理性的思維與行為方式。他的《中華水塔》寫青海三江源生态,不是有關三江源的旅遊指南,而是對三江源生态現狀及其危機作極富針對性的深入的考察,将觸目驚心的現實客觀再現出來,将人的修複與保護意識的覺醒以及實際的行動再現出來,以此警醒國人和世人。
任林舉是生态非虛構書寫的後起之秀。他的《糧道》不僅創設了一個“新概念”的紀實文體,而且關注“糧食”這一涉及國計民生的大事,類似于上世紀80年代産生的問題報告文學。但這部作品的叙述卻更為從容——由糧食說開去,運用多學科的視角,以生動的話語闡述“民以食為天”的“大道”,以及糧道與人道、糧道與國家、糧道與世界的複雜關系。這些叙述确證了知識分子寫作的基本旨歸。
還有一些作家則是從“林”的角度表現生态及其與人的關系,譬如,李青松的“山林”系列——《共和國:退耕還林》《告别伐木時代》《烏梁素海》《油茶時代》《粒粒飽滿》《萬物筆記》等,這是一位林業工作者長期“身臨其境”的所思所感。作為記者和編輯的王國平,近幾年寫出了《美麗鄉村在說話》《一片葉子的重量》《好一個大“林子”》等作品,從浙江的美麗鄉村建設、安吉白茶産業的生态扶貧、河北塞罕壩林場等視角再現“林與人”的關系。
應該說,與美國的生态文學相比,中國的生态文學屬于後來者居上。在虛構和非虛構領域,中國的優秀作家都創作了極具中國情懷和世界眼光的生态文學作品。生态文學并不是科學報告,而是浸潤着人文關懷、終極關懷的形象書寫,充溢着濃郁的“人”之憂思。賈平凹的小說《懷念狼》與借“狼”發揮、主講民族精神的姜戎小說《狼圖騰》不同,它緊扣生态問題不放,着力點在诠釋人與生态的關系。在《懷念狼》裡,狼與人的關系是沖突的。一方面,二者互相敵對,互相威脅着對方的安全與生存;另一方面,人與狼又互相依存,前者離不開後者。這正是大自然“生物鍊”的平衡規律所在。一旦狼被消滅,“獵人”便身心衰竭直至死亡。這就告訴我們,人作為地球生物的組成部分,一定是生物多樣性的受益者,人不可能消滅一切物種而自己卻孤獨地活着。正像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狼與人相輔相成、相依為命,狼的悲劇性命運的結束其實就是人的悲劇性命運的開始。”是以,《懷念狼》思考的正是當代生态文學共同關注的東西,它的結論剛好印證了“和而不同”的生态人文主義的理念。這種理念是對農業文明時代強調人與自然混沌不分、絕對同一的“自然人文主義”,以及工業文明時代人與自然相對抗、相毀滅的“科技人文主義”的反撥與超越,它确認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離不開與他物的聯系和對整個系統的依賴,沒有物種能夠單獨生存和發展,它們必須在大和諧的境界之中互相利用、互相牽制、互相競争,最終實作各自的存在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