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派君有话说
倡导阅读生活,致敬名家大师。为此,甬派文艺频道推出“编辑看名家”栏目,特邀原《中国文学》执行主编、资深文学编辑钟振奋女士主持,讲述她多年来与中外名作家们合作带来的精彩故事,再现名作背后大师们的风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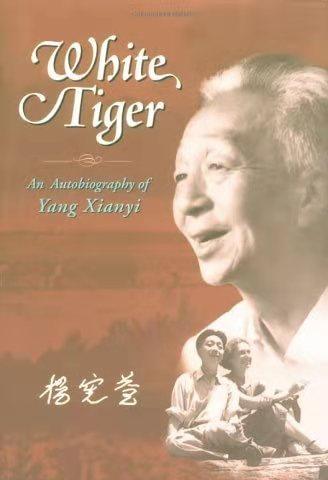
由诗人来做译者,无疑是作者与读者的双重幸运。尤其是由诗人来译诗,更是堪称珠联璧合,妙笔生花。享誉海内外的杨宪益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非常难得的诗人翻译家。无论是中译外还是外译中,诗人笔下那灵动的珠玑般的文字,令人沉吟深味的意境,都能通过另一位诗人的妙笔完美传达,如同作者直接用母语书写,这是一般的译者难以企及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开始参加工作时,有幸与杨先生在《中国文学》杂志社共事过几年。那时候的《中国文学》英、法文部一直都有外籍专家定稿把关,并且重要的稿件会约请国外的汉学家担纲主译,像美国的葛浩文、英国的詹纳尔、新西兰的路易·艾黎以及后来加入中国籍的美裔翻译家沙博理都是我们非常倚重的译者。而担任选稿、写稿任务的中文编辑部也不乏诗人、作家。
杨先生是我们杂志的主编,除了确定每期的选题,还要做大量的翻译以及定稿工作,有时候还会亲自写文章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作家的创作状况。他的工作相当的忙碌。好在杨先生所住的专家楼就在我们单位的大院里,上下班比较方便。在工作之余,我们这帮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也常到杨先生家观看一些外国电影录像,每次去都会受到好客的杨先生的热情欢迎,还拿出好吃的零食招待我们。杨先生和他的英籍夫人戴乃迭也和我们一起观看,有时候遇到难懂的英文句子,杨先生还会亲自为我们做“同传”,他的言行就像一个让人很感亲切的长者,全然没有大翻译家的架子。
虽然对于杨先生来说,由于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了翻译事业中,他的翻译家的盛名多少遮掩了作为诗人的光芒,但他的诗歌才华也会在工作之余时不时地“横溢”,令读者们惊喜。如果说杨先生称他的翻译是工作,“因为乃迭喜欢,我也就做了”,那么写诗则是真正体现他才气与性情的雅事了。
杨先生对于写诗的热情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期。1915年1月,杨宪益先生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富贵之家。祖父和几位叔祖都曾通过殿试当上翰林,是少见的“五子登科”之家。他的父亲杨毓璋精通诗词格律,酷爱京剧,曾经留学日本,回国后担任过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他的三位叔叔也曾有留学法国、德国和美国的经历。杨先生在上私塾时跟着一位优秀的塾师学写旧体诗,悟性极高的他很快就能写出“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断绿杨烟”这样令老师激赏的诗句了。
当然,出于少年顽皮心性,他也曾跟教自己英文的家庭教师开玩笑,拿她的名字“徐剑生”作上联,很得意地对了个“快枪毙”的下联。1928年,杨先生进入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天津新学书院学习,接受了正规的西式教育。杨先生在博览群书之余,对中外诗歌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那个阶段他大量阅读了西方诗人的作品,喜欢上了浪漫主义诗人济慈、雪莱等人的诗,并开始用英文写诗作文。他曾把自己喜爱的一些诗歌翻译成旧体诗。最初的翻译尝试是朗费罗、弥尔顿等人的诗,以及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诗,兴之所至,甚至还根据英译本转译过古希腊诗人萨福的诗。对于他来说,在中西文化之间自由地穿梭,是一件令他非常开心的事。当然,这样自觉的训练也为他后来写诗、译诗的文学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当他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就读时“出于好玩”,用英雄诗体翻译《离骚》,让英国人大大地吃了一惊,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1940年杨先生获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同时还“携带”了一位漂亮的英国姑娘回来,那便是后来成为他夫人的戴乃迭。值得一提的是,戴乃迭出生在北京,7岁后才回英国,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曾经在燕京大学教过书,这也促成了戴乃迭与中国的一生情缘。她在牛津求学时是杨宪益先生上法国文学课时的同学,因为热爱中国文化,后来干脆改学中国文学,成了牛津大学获得中国文学学位的第一人。从喜爱古老而神秘的中国——对中国文化着迷——爱上年轻潇洒、出口成章,还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杨先生,这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于是Gladys(戴女士的英文名字)变成了 Gladys Yang(随丈夫姓杨),杨先生为她起的中文名字——戴乃迭也随之“诞生”了,尽管常有读者来信将她的名字误写成戴乃选。
自古以来,诗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杨先生也不例外,他的好酒是出了名的。据说他在“文革”中蒙冤入狱时,因刚在家喝过闷酒身上尚余酒气,还被同狱的犯人误以为是喝酒闹事才被抓的呢,说他的酒气“好闻极了,一定是高档货”,还问他“多少钱一两”。有人因此戏称他为“酒气最香的犯人”。身陷囹圄,不能与酒相伴,杨先生便“以诗解忧”,教犯人们背诵唐诗,向他们讲解《长恨歌》,他自己独处时则默念莎士比亚的诗句。这样的修为与境界自非常人所能比拟。
每年元旦,我们杂志社聚餐时杨先生都会带上几瓶白酒与同事们共享。杨先生喝酒常会脸红,但从不醉倒,大概他所追求的是一种“仙”的境界吧。杨先生为人处世颇有魏晋之风,黄苗子就称他为“现代刘伶”,还为他画过一幅题为“酒仙”的漫画,图中的杨先生抱着一个酒坛子自乐,活脱一个酒翁形象,真正应了他诗中的一句话“有烟有酒吾愿足”。习惯以酒待客的他当然还会以诗唱和:“我家有大曲,待君日已久。何当过敝庐,喝它三两斗。”这是写给他天津新学书院的同学、翻译家王以铸的。当别人问到他的长寿秘诀时,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抽烟,喝酒,不运动。”
杨先生曾经谈及他抗战时期在贵阳师范学院教书时的经历。那时候他与同在贵阳的学者、诗人尹石公先生等人常常聚会,时有唱和,集中写了不少旧体诗,也许可以算是杨先生的一个高产期吧。常常是10分钟便可依原韵和一首七律,他笑称自己因此“吃了不少白酒白饭”。像这样敏捷的诗思,完全称得上是“倚马可待”啊!
1995年,杨先生在香港出版了一本诗集《银翘集》,里面收录了多年来创作的130多首旧体诗,既有针砭时弊、金刚怒目式的愤世之作,也有酣畅淋漓、直抒胸臆的快意文字,更有不少诙谐幽默的打油诗,从中可见他旷达、洒脱的处世风格。这些诗作大多是靠朋友们收集才留存下来的,因为杨先生对自己写的诗经常是“闲抛闲掷”,毫不在意。有的诗还是他当年细心的同学抄写留存,后来再寄还给他的。
对于自己的一生,他在《题丁聪为我漫画肖像》中是这样总结的:“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恃欲言无忌,贪杯孰与俦。蹉跎惭白发,辛苦作黄牛。”
香港大学曾因杨宪益先生“对于开拓学问知识和人类福祉有重大贡献”以及“在文学和历史学上的杰出成就”而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93),一向诙谐的杨先生在参加完隆重的“加冕”仪式后还不忘写诗自嘲:“相鼠有皮真闹剧,沐猴而冠好威风。”
杨宪益先生晚年时居住的小金丝胡同。
杨宪益先生才华天纵、著译等身,但他一向淡泊名利、虚怀若谷。有人说过,如果杨先生把他的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他完全可能成为像钱钟书那样的大学者。当年他在北碚国立编译馆时写的文章已达很高的学术造诣,但他在编成集子时却自称为“零墨新笺”“译余偶拾”。他曾从希腊文译荷马的《奥德修记》、从拉丁文译维吉尔的《牧歌》,还从中古法文译法国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但对这些堪称卓越的成就,杨先生看得十分淡然,他谦称:“我也没做什么太多的事,也就是翻了点德文,翻了点法文,翻了点希腊文,翻了点意大利文,要不就翻点英文什么的;数量也不太多,也就是把《红楼梦》《老残游记》和《儒林外史》给译成了洋文, 介绍到欧美去了……”把多少译者穷其一生都望尘莫及的成就用这样几句话平平道出,这是怎样的气度与胸怀!
杨先生是个诗人,自然常会流露出真性情。“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遇得失莫关心。”这两句诗恰好表明了杨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就像他用一生的行为所证明的那样,在重要的历史时刻,杨先生会一改平日的温和,他的言行举止中充满了诗人的激情。言人所不敢言,有所为、有所不为,既是一种大勇,更是直抵人心的高义。
作者简介
钟振奋,浙江鄞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文学》(双语版)执行主编。新世界出版社编审。所编辑的图书曾获鲁迅文学奖、优秀外宣图书奖等。曾获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优秀论文奖等奖项,部分作品被《散文选刊》《读者》《青年文摘》等刊物转载并在北京文艺台播出。译著有长篇小说《星游人》(杰克·伦敦著)等。
一审:陈青 二审:龚红雅 三审:汤丹文 终审:王存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