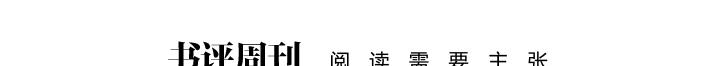
說到最着名的曆史作品,将引用月曆的十五年。在黃仁宇之前,我們不知道曆史可以這樣書寫,似乎隻是在象牙塔裡,但黃仁宇,不僅将曆史融入了大衆的閱讀視野,整個曆史也引起了公衆的關注。與此同時,圍繞黃仁宇的曆史觀和研究方法的各種争議也随之而來。
今天是這位著名曆史學家逝世的周年紀念日。十八年前的今天,2000年1月8日,黃仁宇因心髒病發作去世。這一天我們來跟大家聊聊黃仁宇,不僅是成功的黃仁宇,還給黃仁宇留下了不少争議。
文章最後,我們還準備了一個特别的"蛋",請學術界的幾位老師談談他們對黃仁宇和《十五年曆》的看法和思考。您如何看待這本流行而暢銷的曆史書?你是不是也是通過黃仁宇先生愛上了曆史?歡迎您留言與我們分享您的想法。
編寫|宗城
黃仁宇把自己活成一種現象,或者說是一個傳說。他原本是個單純的學者,生活在象牙塔裡,但六十歲以後,因為太久沒讀新書,評價達不到标準,他被紐約州立大學的紐普斯開除,學術之路敲響了警鐘。然而,人生起起伏伏,讓紐普斯大學沒想到,第二年,黃仁宇就新書,書名《曆法十五年》,曾經洛陽紙價不菲。此後,他的每一本書都成為暢銷書,有人崇拜他,還組織了"黃色研究研究會",并申請設立"黃色研究"學術系列。
在他的一生中,甚至通過生與死,都有許多巧合和轶事。黃仁宇于2000年1月8日去世,轶事:那天他去看電影,突發心髒病。在去電影院的路上,黃仁宇微笑着對妻子格爾說:"老人身上病得太重了,最好是抛棄軀殼,離開這個世界。"我不想說一句話。
在民間,黃仁宇是著名的曆史大師,但在曆史領域,黃仁宇更像是一個"側門左手",國内主流的明代史專家并不完全采納他的觀點,甚至有人專門分析黃仁宇的作品硬傷,批評他的學術态度。黃仁宇一生之後,曾是一個诽謗人物,而現在,當我們回頭看這位曆史學家,剝離詛咒和求愛,理性看待他的作品和争議,或許對未來的生活更有啟發性。
偉大的曆史
現代性是不合時宜的
黃仁宇本人是個有趣的人,他被曆史上每一個被譽為"神奇俠"風格的學者。在他的一生中,他留在學校,參軍,成為一名教師,完成學業,一本名為《月曆中的十五年》的書使他成為最具曆史意義的作家。
他成為曆史學家的雄心壯志與他父親的遭遇有關。他的父親來自湖南省的一個地主家庭,他加入了同盟,加入了革命,但十多年的動亂使他憎恨革命,為了在時代的縫隙中生存下來才得以生存。黃仁宇曾經說過:"他(父親)讓我意識到我是幸存者,而不是烈士。這種背景使我清楚地知道什麼是可能的,什麼是不可能的,我不需要面對已經發生的事情。"
黃仁宇,1918年生于湖南省長沙市,華裔美國人,1936年考入南開理學院機電工程系。抗日戰争爆發後,黃仁宇辍學參軍赴美留學,在密歇根大學(于英石)獲得曆史學博士學位,曆史學家、中國曆史專家、曆史大觀倡導者都知道。著有《曆十五年》、《中國大史》等暢銷書。
學習後,黃仁宇專注于明史。早在1974年,他就寫了《16世紀明朝中國的财政與稅收》,其中黃仁宇指出:明朝的财政注重形式,但官僚與人民缺乏法律和經濟聯系,是以不可能建立有效的稅收制度。這本書的想法影響了"月曆十五年"的寫作,沒有它就沒有"月曆十五年"。
除《曆十五年》外,黃仁宇較受歡迎的著作還有《中國大史》、《資本主義與21世紀》、《從大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黃仁禹回憶錄》等。在這些作品中,"偉大的曆史"是一個被多次提及的詞。黃仁宇認為,隻有大視野才能看到偉大的曆史,整個中國的曆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其内在的規律和聯系。一般來說,"大史"要求學者從宏觀的角度把握曆史,而不是拘泥于細節,在世界曆史的背景下講述特定朝代的變化和演變。
作為學者,黃仁宇倡導高度的理性計算精神。在治理方法上,他主張采用歸納法,在對比分析的基礎上,對現有曆史資料進行高度壓縮。這在《中國史》中尤為明顯。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大史"和"曆法十五年"的思想是一緻的,黃仁宇站在批判的角度看待農業社會和中國朝代的興衰,這實際上是西方人研究中國曆史的典型思想,在他們看來,不同的社會形态, 經濟制度确實是落後和先進的,後者往往被稱為"現代"或"現代",而前者是中國農業社會和封建政治制度的代表,"中國偉大的曆史"來談論"現代經濟制度與農業社會的沖突"。
《長沙白茉莉花》
作者: 黃仁宇
譯者:宋碧雲
版本:九州新聞 2009年8月
除了曆史著作,黃仁宇還有寫小說的愛好,曾以筆名"李偉昂"出版。《餘景餘夢》、《長沙白茉莉花》等都是他的小說。如果不學,黃仁宇有望成為一名勤奮的小說家,但他的小說不如曆史書,說教太多,語言上還有一個清晰的"曆史空腔",在人物的控制上也缺乏細節,不像寫小說,而像曆史解釋者。
在寫作中,黃仁宇模仿了明清兩句話和民國通俗小說的路号,披着剛硬的理性外殼,但有些骨頭是溫柔的蝴蝶。他認為自己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你可以毫不猶豫地追求一個女孩,在鬥争爆發時可以勇敢地參軍。他喜歡受歡迎,喜歡體驗戰士的感覺。在抗戰期間,作為總司令部的一員,他偶爾會冒險進入無人區,即使沒有多大幫助,當中國軍隊在山口附近損失了兩輛輕型坦克時,他冒險觀察被日軍燒毀的坦克。"用手指觸摸被四點或七點反坦克炮刺穿的洞。
1587
從"無意義"到"大轉彎"
比如說黃仁宇,或者說是圍繞着"十五年曆"的影響。
四十年過去了,這本書還是暢銷不少,分析這種現象并不是一種可以打消的"寫作新奇"。1587年表面上是平靜的,但發生了一些深遠的事情。這是萬曆登基十五年,是沈世航作為内閣第一輔工的當年,也是清官發晖、吳将齊繼光去世的那一年,黃仁宇認為——這是大明王朝的轉折年。1587年後,大明王朝走向滅亡。
月曆的十五年
版本:生活,閱讀,新知識三聯書店,1997年5月
與明朝前作相比,《曆法十五年》避免了複雜的曆史鈎子,而是用人物生活的幾個片段勾勒出作者的視角。在書中,萬立對自己的一切都被繁文缛節所束縛感到不滿;沈世航每天都在做着無聊的工作;齊繼光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李偉正面臨王朝絞刑。1587年,公務員制度陷入了瑣事之中,而統治機構則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僵化的道教。黃仁宇認為,明朝失去了國家管理的關鍵:技術。同時,該政權過于注重道德,在中後期放慢了法治的步伐。
這可以從沈世航的命運(編者注:明朝著名大臣)身上看出。這種公衆主張少和諧,相信儒家經典,強調用美德為人服務,用美德衡量人。他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調和各級官員的争論,随着時間的推移,他成了一名調解人,無法像張居正那樣提高官僚能力。
然而,沈世航想要平衡公務員群體與皇帝的關系,和諧而少戰的辛勤工作卻沒有得到同僚們的了解。最後,次級徐國開啟了他和萬曆皇帝的溝通,沈世航完全失去了公職組的信任,他隻能辭去第一個輔工職位。
強調道德和法治技術,最終因為需要美德和實踐的問題而離開,沈世航正是被自己維護的制度趕了出去。在這個體系中,判斷官員的最高标準是道德操守,而不是技術先進、程式是否合理。調解的标準不是任何人的論點更合理,而是理論家的道德是高尚的。官員為了保持自己的評價風格,一方面不敢任命技術人員,另一方面,巴綁名人,給自己一個好口碑。
萬曆十五年,英文
版本:耶魯大學出版社,1982年9月
與沈現在的陣容相反,海瑞和張居正。哈利不僅僅是一個道德榜樣,他有很好的經營能力和行政權力。在主要政治位置上,他鎮壓強者,清河,實行鞭刑法,以提高明朝人民的本源,實作中央官員。海瑞在自己心中燃燒着極大的激情,為了讓自己心中的清平生士艱苦奮鬥,他想用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來對抗現實生活中的自己看待一切。但海瑞的悲劇在于,世界隻把他當作道德的象征,而不是他的技術能力。直到他去世,情況仍然如此。十五年過去了,海麗去世了。"北方所有的官員都為他哀悼,甚至皇帝也給他寫了一封貢品。正如《1566年大明王朝》的作者劉平所說:"他們哀悼的不是一個人的死亡,而是一個精神象征的死亡。"
張居正比海瑞更政治化,他反對用道德代替技術,政府十年來,他重複使用技術人員,但為此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死後被悲慘地抄回家。
利益被削減,公務員小組決定把張居政的私人美德作為文章。張菊正試圖用自己的努力來提升官僚機構的技術,用一套世俗的行政效率來解決明朝的問題,卻忽視了道德在保守官僚心中的重擔,是以他們被群落包圍。
他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是用自己的努力推動自己的改革,他是在用大權,但在體制上,張菊缺乏變革,這使得他改革的成果難以挽留。而且,張菊正不僅面臨着保守派公務員的道德嚴厲批評,還面臨着皇權的反擊。是以,張居正死後,明朝政治又回到了老路上去。
明朝官廷将形成一種道德而不是技術,以及當時的文化。有政治學者指出,中國的政治文化一直是一種"文化中間的政治文化",不同于西方的"體制軸心政治文化"。文化決定政治生态,明朝也不例外。明朝是一個科學盛行的時代,表面上是儒家思想導向的,但有兩股主要勢力交織在一起,互相沖突,一是相信程竹立保守的官僚,一是弘揚魯王心中的新官僚。但不管怎樣,對個人道德的要求都很大,加上以神為主的中國時期,已經有強烈的人類治理氛圍,整個朝代都呼喚着世界的道德統治,世俗的孝順,是以明朝官僚們把德治法放在首位也就不足為奇了。
争議
黃仁宇的理性看法
伴随着暢銷書,也存在很大的争議,對黃仁宇作品的批評和他偉大的曆史觀早已存在。最大的争議是黃仁宇對"曆史分析"的文學化。黃仁宇在叙述一個曆史人物時,可以灑、噴湧,但描述多,基礎少。比如寫《曆十五年》,講到沈世航、海瑞、張居政這些人物,黃仁宇花了大量的筆墨寫下了他們的"心态"、"行為",但這種猜測的依據在哪裡呢?他沒有提供,這在曆史研究中是一個很大的禁忌。
隐藏在偉大曆史觀下的是黃仁宇"重新判斷,輕解"。黃仁宇是造詞大師,"大曆史觀"、"洪武型金融"、"數字化管理"是他最喜歡的詞語,但他經常引入新詞,但解釋不夠,讓人迷霧缭繞,讓主流學術界難以接受。學者們不允許有新的想法,比如邱芷明對三國曆史的研究,他提出"司馬瑜不是儒家家族的代言人"是對陳玉克觀點的"反對",這種"反對"是基于對最新曆史資料的詳細論證和把握,是以邱泷明的觀點很快被曆史學家所接受。
除了知識之外,豆瓣網友、學術界也不乏對黃仁宇文章的批評。例如,萬明的《16世紀明朝金融史回顧——黃仁宇<16世紀中國财稅>》,朱曉明和易成志的《曆法>15年的邏輯與<——以及其中的一些遺漏》,以及潘淑明和徐素敏的《<15年>誤讀李偉作品》。。他們主要批評黃仁宇引用曆史資料。其中,潘淑明和徐素敏有着非常敏銳的觀點,他們認為:黃仁宇的學術偏見是——像中國這樣的社會,不可能産生任何新經濟、新思想,隻能在外力的作用下"現代化"。
中國曆史
版本:生活,閱讀,新知識三聯書店,2007年2月
其實,黃仁宇的學術态度與他人生的流動息息相關。浪漫華麗的湖南長沙,早年在美國接受過學術訓練,也憑直覺感受到了那個時期不同社會生态的風格,這讓黃仁宇積極擁抱現代性,強調科技和法治的作用,對農業社會和父權制傳統要挑剔。
黃仁宇沒有回避争議,他重複并補充了他的《大曆史觀》、《偉大的曆史不會退縮》等作品和講義,在他的回應集裡。他首先反對将曆史人物從特定語境中剝離出來,反對輕率的道德判斷,是以他說:"中國人重新貶低,在書寫曆史的時候,他使書中的人得以向最好和最邪惡的人解釋。很容易将書寫曆史作為抒情工具。同時,他主張将地方曆史融入整個偉大曆史的生産演進中,而觀察者則介入曆史程序,把握曆史中的空間互動和叙事。《曆十五年》等作品是他系列觀點的實踐,齊繼光被脫掉了"抗日英雄"的語境,海瑞也不僅僅是一個道德象征。
當然,大多數人都肯定了黃仁宇的叙事魅力和他傳播明史的巨大動力。
"我讀過四遍《漫長曆史中的十五年》,"吳說。1986年初,讀書時,隻覺得寫得好,說了關鍵,而關鍵點是什麼不能說,反而覺得大海是肆意妄為,仿佛龍看到了結局。"這種汪洋肆意妄為是黃仁宇曆史的特征,他總是高高在上,努力去感受曆史的質感,讀着他的書,橫截面的氣息來了,即使觀點不一樣,閱讀還是會很享受的。黃仁宇對曆史叙事的貢獻可能比他自己的曆史觀點更大,他開辟了一種不同的寫作方式,市場回報被證明是有效的。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圖書局出版了中文版《曆法十五年》,第一卷印刷本25000冊售罄。直到今天,這項工作仍然很受歡迎。
《黃仁宇全集》
作者:黃仁宇 版本:九州出版社,2012年2月
今天,我們重溫這些争議,不是為了責怪死者,而是為了重新審視這部作品和所謂的"黃仁宇現象"。盡管有錯誤和遺漏,但黃仁宇的作品仍然為學術界提供了"走出去"的啟示。學術研究不是閉門造車,學術寫作不必局限于舊形式,如果黃仁宇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寫作考慮到了少數精英和非專業讀者,證明枯燥的曆史資料也可以轉化為引人入勝的生動叙事。
有趣的是,黃仁宇在他的書中對數字管理持高度積極态度,認為數字商業社會是比農業社會更先進的社會形式,但黃仁宇正是因為"複雜的數字管理"而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波特分校解雇。他的"績效點"(FTE)達不到标準,他的學術思想也不符合現代學術生産所倡導的"專業分工"。對于一個學者來說,被解雇是一個巨大的挫折,也是黃仁宇一生難以言喻的秘密。
當更"進步"的社會形态把自己趕出大門時,是他們自己的問題,還是這種"進步"會是一個巨大的問号?更重要的是,我們見證了計算理性的時代,這是黃仁宇在他的著作中高度欽佩的。電腦、手機、大資料、雲計算,沒有比現在的時代更"計算"的時代了,分工更高,知識分子被培養成專家,城市公民用工具理性地看遍每個人,我們甚至可以預測自己的未來,賽博朋克的智能世界不是幻想。但在這個時代,黃仁宇的擔憂得到了解決嗎?黃仁宇已經離開了,他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但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難題,也是當下人應該反思的困境。
圓桌會議
他們如何看待黃仁宇和十五年曆?
寫作|新京報實習記者 郭雪豔 丁振偉
争議和批評在公開場合顯得蒼白無力
易忠天,1947年2月出生于湖南省長沙市,1981年畢業于武漢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留學任教。著名曆史作家、學者,後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黃仁宇先生的《曆法十五年》對我們這一代人産生了巨大的影響,非常感恩,經常讀新書。
對我來說,黃仁宇先生和《十五年曆》對我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知道原本的曆史也可以這樣看,是以寫吧。對我來說,這種影響是革命性的和颠覆性的。
而一個學者選擇發表他的研究成果,究竟是什麼樣的表達方式,完全是他的自由,讀者的好惡看得見,似乎不選擇自己的,還有什麼可争辯的呢?我在武漢大學讀書時,一大批非曆史研究所學生争先恐後地傳授《曆十五年》。有多少人能如此有影響力?難道所有的争議和批評都不是蒼白無力的嗎?
《曆法十五年》的出版,開啟了曆史領域的新潮流
解釋,著名的評論家,學者,現代史研究者。著有《梁啟超傳記》、《一個人的讀史》、《響度與寂寞》、《優雅與蘇荷》等。
黃仁宇為我們這一代人提供了一種講述曆史的新方式,我們以前從未見過這種講述曆史的方式。當我第一次讀到《月曆的十五年》還是在1980年代初,我看到這本書有一種新奇感,在大學生都很興奮,沒有看過這樣的書。因為我們看過的教科書和國内學者寫的曆史書大多是穩定的,比較教條,但黃仁宇的《曆法十五年》既有宏觀曆史的架構,又從微觀人物開始,去分析和介紹曆史,新鮮感特别強。關于黃仁宇的争議,可能是由于國内曆史界總體上比較保守的一面,很難接受新事物,看到這本書會認為黃仁宇的曆史叙事不符合規範。但其實我們讀了很多西方曆史書,尤其是比較流行的曆史書,他們大多能和熱愛曆史的普通讀者有一定的交流。
國内曆史研究和曆史叙事手法也随着歲月而變得多樣化,近年來,中國逐漸出現了類似的書籍,但之前黃仁宇絕對不是。改革開放後,正如金庸和梁玉生對中國大衆文學圈的影響,以及鄧立軍對中國流行歌曲的影響一樣,《十五年的曆史》也是曆史硬碟的第一沖擊,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告訴人們曆史也可以書寫, 他在這方面的影響非常深遠。
當然,在對曆史的具體讨論中,對一些結論和描述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因為曆史很難達成一緻,而且看不同的曆史視角、手頭的不同材料、不同的立場、不同的出發點,都可能影響曆史叙事,這是正常的。但不管你接受與否,《月曆十五年》的出版都是一股新風,對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的影響是絕對的。
黃仁宇确實不錯,但不是那麼好
張明陽,曆史作家、《上海書評》主編
上大學的時候,黃仁宇拿出了他的《曆十五年》和《中國大史》,告訴我們這些"不太看見世界"的學生,原著的曆史可以這樣寫。即使對于很多曆史專業,黃仁宇也采取了一種非常颠覆性的做法,原來我們沒有讀過這樣的曆史,也從來沒有人寫過這樣的曆史。
黃仁宇先生在大陸幾十年來的名聲是漂流的,起初,黃仁宇在大陸是一個被埋沒和忽視的國家,而"曆法十五年"進入中國,黃仁宇被捧在祭壇上,曾經有一段時間,這種體書出來了很多,很多;2010年之前,黃仁宇的名氣太高了,很多人評價他為"幾十年來最厲害的學者"之一,但他的學術能力卻經不起這麼高的評價,我想這不一定是對黃仁宇先生的客觀評價。近幾年,閱讀界進入第三狀态,開始反思黃仁宇,我們開始認為黃仁宇真的很強,但并沒有那麼強。我覺得這種評價是好的,但是在重新評估黃仁宇的過程中,我們不能過分地稱他為一個非常差的、二三流的曆史學家,這對我來說是不能接受的,我認為他也是一個非常一流的曆史學家。
曆史寫作是學術寫作還是非學術寫作,即使在美國也存在争議,曾擔任美國曆史學會會長的史景正先生的曆史可能更具文學性,美國學術界對他有很多争論,但他的地位還是很高的。曆史圈對不同流派、不同性格、不同閱讀習慣的人有這樣的争論,是正常的。我認為曆史的寫作沒有固定的标準,沒有非此即彼,或者取決于作家的水準,寫不容易不好,寫學術不好。
▼
直接點選關鍵詞,看過去精彩
點選"閱讀原文"去我們的微店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