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軍壓境,糧食被搶,對于雄才大略的鄭莊公來說,這是奇恥大辱。但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睿智和理性讓他不急于與五國再次陷入混戰之中。然莊公生來就不是甘願白白挨打的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犯死你。仇還是要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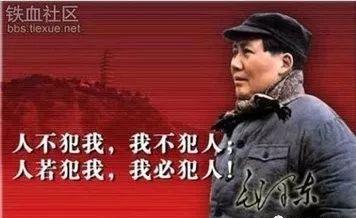
鄭國的反擊
當初氣勢洶洶的五國聯軍散了之後,衛國率先亂了,不勞莊公動手,幾年内都是軟柿子。其他四國也該收拾了。
緩過神來的鄭國開始了反擊。
還是老套路,拉盟友,盡可能增強己方實力。也怪宋國人貪心,搶了邾國的田。這邾國不大,子爵,但也不能讓你這麼欺負,土地可是命根子。可打不過宋國怎麼辦?
邾國人想到了鄭國:鄭伯你可是周王卿士,可得為我們主持公道啊,宋國,就是去年打你那個混蛋,又來欺負我了。大哥幫我揍丫的。
莊公一聽,正中下懷啊:本來就想打你,奈何你宋國好歹也是個大國,單挑太累,現在有了這麼好一個借口,老子正好籍此調動王室軍隊讨伐你,看你敢不敢對周天子的軍隊動手。
莊公就這樣再一次公權私用了一把,口号喊得震天響:宋人無道,欺淩邾子;天子震怒,命我下伐(這多少有點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感覺)。
可又有誰不知道你這是報去年東門被圍、糧食被搶那檔子仇呢。(也不知道這王師哪兒借來的,按理說周天子跟鄭莊公不來電啊,估計又是賄賂了哪個王畿内的親戚,挖了周王的牆角)。
宋國向來是欺軟怕硬,打仗也不拿手,面對以兇悍善戰著稱的鄭軍為主的周、鄭、邾三國聯軍毫無還手之力,這一打就直接打進了宋國國都的外城。
攻城為次,鄭鄭莊公可不想在宋國的國都之下消耗太多國力,滅了宋國也不現實,差不多得了。一番道義譴責後,眼看宋國龜縮不出,用行動表示自己慫了,鄭軍便打道回府了。
恩恩怨怨何時了。這邊宋國剛被打,沒過幾個月,忙完地裡的農活,收完成熟的莊稼(先收再打,免得打不過糧食也丢了),立馬又派兵往鄭國打,包圍了鄭國的長葛,一圍就是一年多,最終還打下了長葛。
古人不像今人這般講究聲東擊西、各個擊破這樣的謀略,他們認為那是無恥和缺乏勇氣的表現。隻有兩軍拉開架勢,兩陣對圓,堂堂正正地幹一架才是君子所為,如果己方有萬夫不當之勇的猛将,可以緻師挑戰,他們崇尚的這種打法稱為“偏戰”,而與之相對的“詐戰”,則不受推崇。
再不濟就是一方死守國都,一方圍城,但必須是在被讨伐的國家的國都幹架,打其他地方不算英雄好漢。
而宋國這回包圍長葛就顯得不厚道了,是以《春秋》拿長葛之圍作為典型罵了一回宋國無禮。
就這樣一來一回,宋國也跟鄭國結下了梁子,這兩國的恩怨剪不斷理還亂,一直持續到春秋末期,可以說禍害了好幾代人。
但總的來說,鄭國在軍事上是占優勢的,而宋國在外交上占據主動。
鄭國從春秋中期開始在晉、楚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搖擺不定,反而長期遭到晉楚兩國點名。宋國則是鐵了心做晉國的馬仔,反倒沒有鄭國那麼多外患。但鄭國即使被晉楚揍個半死,回過頭總能從宋國頭上占點便宜,十足的宋國克星。這留待日後對《左傳》的解讀中分享。
鄭國反擊的第二步是瓦解五國聯盟。五國之中,與鄭國利益沖突最少的當數魯國。魯國與鄭國不接壤,中間隔着宋、衛、曹等國,即使對外擴張也搶不到一塊兒去。
鄭國和魯國不接壤,利益沖突較少
可魯、鄭兩國有仇,魯隐公在戰場上被鄭國人俘虜過,這面子拉不下來啊。
其實這魯隐公是個老實人,沒啥野心,即使魯國國君之位他也是暫代而已,早打算還政于他弟弟(後來的魯桓公)。是以,即使五國聯合伐鄭時,魯隐公也是反對出兵的,架不住公子翚擅自行動。
莊公覺得魯隐公的為人可以,就主動示好,打完宋國的第二年開春就派了口才最好的謀臣去朝見魯隐公,要求棄怨修好(渝平、更成)。這魯隐公多半是同意了,反正魯、鄭兩國之後就沒再打起來,即使鄭國跟其他國家鬥得你死我活。
其實,早在上一年,鄭國就打算與陳國和好,但失敗了。陳桓公不知道哪根筋搭錯了(上回說了,陳桓公有精神病,這回舊病複發),明知沒好處,非要跟鄭國過不去。理由很可笑:衛國和宋國才是真正的禍患,鄭國沒什麼能耐。意思是老子防的是宋國、衛國,鄭國這樣的盟友不要也罷。
什麼邏輯,反正我是沒看懂。你怕宋、衛,還跟這倆坑貨結盟?(精神病的世界我們不懂)
敬酒不吃吃罰酒,和談不成那就打,前年你搶我的糧食今年給我吐出來。結果一打,陳國僞大國的原形就暴露了,跟鄭國單挑,還真不經打。鄭國大勝而還,連那幾百車糧食連本帶利都拿回去了。
有得也有失,這邊鄭國大勝陳國,那頭宋國趁着鄭國主力在外,把去年包圍的長葛又撸了一次,拿下了。
經過這一輪反擊,鄭國跟宋國等于打了個平手。看似沒啥收獲,但卻争取了魯國的中立甚至支援,順帶把陳國按地上摩擦了一通。總體上說,這輪反擊預期目的達到了。
閃轉騰挪,鄭莊公的一系列操作再一次為鄭國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和空間,鄭國接下來該走向何處呢?鄭莊公又會遇到哪些困境,取得哪些成就?
敬請關注下期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