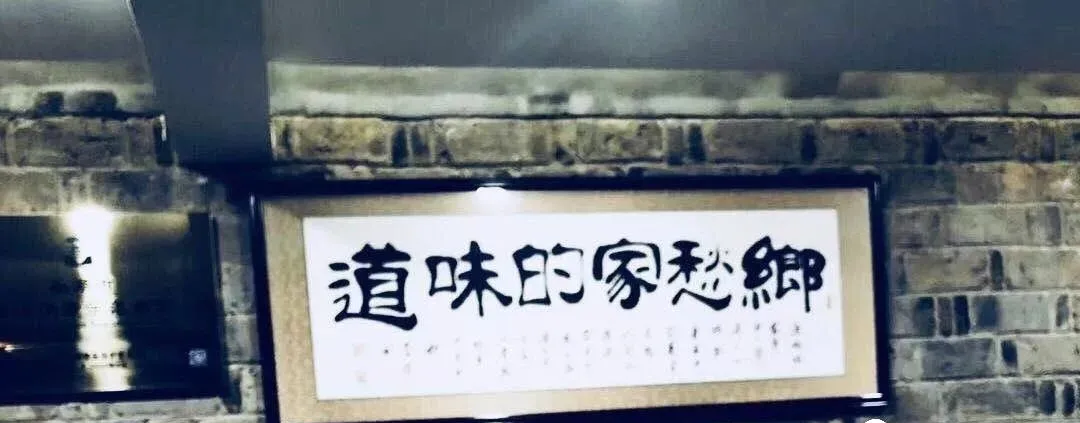
作者:吳钊
舍不得、放不下、不敢愛的老家“小菜”
合肥人喜歡吃小菜。飯店用餐,上主食時,習慣請飯店服務員上一份或幾份小菜。前幾年,在開發區分管招商,經常去外地出差,有一次在南方出差,吃飯時,同僚問服務員有沒有小菜,服務員不明白什麼叫“小菜”,解釋清楚後,服務員回答說“沒有”。
合肥話中的“小菜”,就是鹹菜。小徐村小菜有好多種,按制作的方法算,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腌制的小菜。蒜頭、蒜苗、蔥果、豆角、蘿蔔、刀豆、扁豆、冬芥菜、雪裡蕻、韭菜、辣椒、生姜、莴筍、菜瓜等葉類、根莖類蔬菜,都是做小菜的常用材料。
每家都有好幾個陶質的壇,大小不一,用于腌小菜。大壇腌冬芥菜、雪裡蕻,小壇腌豆角、韭菜等别的菜。香椿也腌,自己家香椿樹上産的香椿。有一種野生的小蒜,小徐村人稱為“小蒜”,長在田野,連根挖回來,洗淨後腌腌也好吃。太細、太小的小蒜,摘洗時有點麻煩。
第二類是醬和醬菜。醬有兩種,一種是蠶豆醬,另一種是水磨辣椒醬,沒有很多地方有的黃豆醬。蠶豆醬,在小徐村稱為“醬”,以前多自制。蠶豆是幹蠶豆,需要去皮,雖然用水泡了好長時間,殼還是難剝。在小徐村住時,每年都跟表姐們一起剝做醬用的蠶豆,剝得手生疼。1981年暑期,和爸爸去定遠張橋,聽說張橋人用黃豆做醬,覺得好奇怪,其實是少見多怪。
小徐村人稱辣椒為“大椒”,稱水磨辣椒醬為“大椒醬”。“大椒醬”多用自己家收的新鮮紅辣椒,到加工廠磨碎,做成糊狀,加鹽。也有少數人家用新鮮青椒做。“大椒醬”多直接吃,也作燒菜、炒菜、涼拌菜時的調味品,很少有人用水磨辣椒醬醬别的菜。
醬菜,用蠶豆醬,而且是專門用于醬菜的蠶豆醬。自己家直接吃的醬,和醬菜用的醬分開,各按各的用途。醬的菜有蘿蔔、洋蔥、生姜、莴筍、刀豆、扁豆、黃瓜等,都是非葉類菜,友善撈取,不拖泥帶水。現在有些人家不做醬,就用醬油醬菜,也好吃。
第三種是曬幹或曬得半幹後再加工的小菜。最具代表性的是蘿蔔幹,小徐村稱為“蘿蔔響”。“蘿蔔響”分為兩種,一種由稍大點的蘿蔔制成,洗淨後,需要切開曬;另一種是小蘿蔔品種,稱為“小蘿蔔頭”,直接洗淨曬幹。
曬半幹的有菜瓜、黃瓜、莴筍等水份比較大的根莖類和果實類的菜,還有一種類似于榨菜,被稱為“苔菜”的菜,也是曬成半幹,再用鹽腌或用醬醬,吃起來更脆。
小菜做好了,根據個人喜好和習慣,吃法自便。
醬菜和腌菜,有些适合直接吃,如蘿蔔幹、腌蒜頭、腌辣椒片、醬生姜等。有些适合炒着吃,如腌制的雪裡蕻,加肉絲炒更好吃,雪裡蕻炒肉絲是合肥地區的一道名菜,現在也稱“雪菜肉絲”。有些既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炒着吃,從口感角度看,直接吃可能感覺更好;從衛生角度看,加熱炒一炒,更好。
蠶豆醬作為小菜直接吃,可以加入切好的紅辣椒片或青辣椒片,頭一天晚上拌好,第二天早晨就能吃。炒着吃也好,加肉丁或巢湖産的白米蝦,做成肉醬或蝦醬,放玻璃瓶裡,能吃好長時間。加入黃豆、肉丁等許多配料的“炸醬”、“炒炸醬”、“肉丁炸醬”、“雞丁炸醬”、“毛豆炸醬”,在合肥地區是一道名菜。蠶豆醬還可以和豆腐一起放碗裡或盤裡,豆腐搗碎,加一點香蔥,在鍋上蒸着吃。
爸爸媽媽小菜做得好,家裡小菜不斷。爸爸最拿手的是腌冬芥菜,爸爸說他的手好,經他手腌的冬芥菜從來不會發臭。爸爸1978年至1980年在定遠縣年家崗公社工作時,媽媽帶着我們還住在肥東老家。春節期間,媽媽帶我們去年家崗玩,我和媽媽都喜歡吃爸爸自己在那腌的冬芥菜,不需要炒熟,洗洗切碎後,直接吃,清脆爽口,至少還有感覺。爸爸還喜歡将胡蘿蔔切成丁,放青蒜,用醬油泡着吃;喜歡将香椿切碎,也用醬油泡着吃。媽媽會做的小菜更多。
有好多年,家裡每年都要做蠶豆醬,醬下醬缸後放外面曬。1985年暑假,我們家住定遠張橋供電所北面曬場的社屋裡。爸爸媽媽做了兩大缸醬,特意在曬場放一張條桌,醬缸放桌上曬。我下午放豬,媽媽提醒我,不要讓豬将醬缸打倒了。我答應好好的,還是大意,豬真地将條桌掀翻。醬缸落地上,摔碎,醬流一地,不能要了。媽媽心疼醬,更心疼我。爸爸下班回來,媽媽主動說,将豬圈門一打開,豬就蹿出來,蹿到桌子下面将桌子撞倒。爸爸不相信,生氣地将豬圈門打開,火沖沖地說:“我就看看豬是怎樣蹿出來将桌子撞倒的!”
我喜歡吃小菜,喜歡吃爸爸媽媽做的小菜。參加工作以後,幾乎每頓飯都離不開小菜。現在因為健康方面的考慮,不敢多吃,卻舍不得不吃,有時遇到自己喜歡的小菜,仍然忍不住多吃,妻攔都攔不住。在外面吃飯,每次都忘不了請服務員上小菜,有時還主動問服務員,他們家飯店有什麼好吃的小菜。
論對小菜的喜好,在腌菜與醬菜之間,我更喜歡醬菜,喜歡濃濃的醬味。論品種,更喜歡腌蒜頭、腌大椒片、腌香椿、醬生姜、“蘿蔔響”、醬洋蔥、醬莴筍、醬刀豆等。有一種不是合肥地區出的臭豆子,也喜歡。對到處可以買到的榨菜、豆腐乳,一般。在吃法上,更喜歡直接吃,不炒。切好的小菜,無論是腌菜,還是醬菜,加一點麻油,感覺更好。
我最不感興趣的小菜,是雪裡蕻,因為小時候在小徐村時吃得太多,吃厭了,吃怕了。那時候,蔬菜少,小菜不隻是早、晚吃,中午也吃。可能是雪裡蕻産量高的緣故,我們家和村裡其他人家一樣,每年都要腌一大壇雪裡蕻,吃腌雪裡蕻的時間也最長,而且不是肉絲炒的那種,油放得少,有時候可能放一點千張絲進去一起炒。特别在冬天,經常吃雪裡蕻,缺少新鮮蔬菜,我和村裡好多孩子嘴角都長了瘡。
腌菜壇裡的水,腌菜時間長了,有點淡淡的臭的味道。這在一些人的眼裡,是好東西。國家5A級景區的肥西縣三河鎮,是太平天國時期“三河大捷”的發生地,有諾貝爾實體學獎獲得者楊振甯的舊居和抗戰名将孫立人的故居,也是合肥地區美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三河米餃”、“三河小炒”等菜肴在合肥家喻戶曉。三河街上有飯店,用腌菜壇裡的鹹菜水,蒸臭豆腐,起個很文雅的名字,“千裡漂香”,聞起來臭,吃起來香,很受歡迎。
我們在老家,菜少時,媽媽也經常将面粉調成糊狀,用腌菜水蒸,蒸成“面糟”,顔色略青,有微微的鹹菜水味,鹹。年輕的媽媽對我們說,她牙齒不好,喜歡吃鲊“面糟”,以後老了,我們隻要鲊“面糟”給她吃就可以了。現在生活條件不是那個時候可以想像出來的,媽媽現在哪裡還要吃“鲊面糟”。
媽媽身體好時,根據不同季節,每年都要做好多小菜,給我帶到合肥吃,現在身體不友善,仍然曬蘿蔔幹、做數量不多的小菜給我帶走。我自己也學,将青蒜切小,腌一腌就吃;将新鮮辣椒切成片或切碎,腌着吃;将洋蔥切成絲,腌着吃;将胡蘿蔔切成丁,腌着吃。我還學着做四川泡菜,用包菜做,加生姜片、胡蘿蔔片或絲、紅椒片或青椒片、蒜頭,感覺味道也還好。
除了以上所說的小菜,小徐村還有将什麼什麼東西“當小菜”吃的說法。這樣的東西,也是菜,不過不在通常所說的小菜範圍。小徐村人的心目中,這些可以當小菜吃的菜,比平常的小菜進階。比如鹹鴨蛋、燒黃豆、臭幹子、冬天的魚凍、春節期間做的賀菜等,都可以當小菜吃,卻不是平常所說的小菜。還有正餐吃的鹹魚、鹹鴨子等,正餐沒吃完,早餐、晚餐端出來,也能當小菜吃,隻是有點委屈它們了,它們是大菜。
“小菜”小,小得微不足道,不珍貴,不稀罕,家家都會做,家家都能做,因而,“小菜”這個詞也被引申為“小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等。如有事請熟人幫忙,熟人很有把握,答應得很幹脆:“小菜!”有時候,還會在“小菜”後面加上一句“一碟”,為“小菜一碟”。稱贊别人有本事,解決問題的辦法多,有時會說:“你做這個事,還不是‘小菜一碟’。”這樣的語境裡,“小菜”等同于“小事”、“小菜一碟”等同于“小事一樁”。
小菜鹹,比較下飯,又有“下飯小菜”的稱謂。誇獎人家小菜好吃,會說:“他家‘下飯小菜’好吃。”由于小菜“下飯”、并且不珍貴、太普通的特點,小徐村及合肥許多地區,将“下飯小菜”這個詞的意思也引申為不被人看重、不受人尊重的“受氣包”、“出氣筒”等。如,妻子指責丈夫不尊重自己:“他當我是‘下飯小菜’,天天給我臉色看”,“你以為我是‘下飯小菜’啊?天天給我臉色看”。
小菜好吃,不能多吃,多吃影響健康。對于我們這些從小生活條件不好、吃飯離不開小菜的人來說,吃小菜已經成了一種飲食習慣和愛好,明知道不對,卻難管住自己的嘴,欲罷不能。
小菜,俺的小菜,舍不得,放不下,不敢愛。
最憶是巢州